九岁登基,却沦为傀儡,生母惨死,杀机四伏,十四岁,他忍无可忍,密谋反击,一招制敌,翻盘外戚集团!
这位少年天子,不仅智斗太后,更挥师西域,拓土五十国,缔造“永元之隆”!他就是汉和帝刘肇,比康熙更传奇的少年帝王,却只活了27岁!
公元88年,九岁的刘肇坐上了龙椅。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本该是泼天的富贵,可对他,更像是一副甩不掉的枷锁。因为真正拍板说了算的,不是他这个小皇帝,而是帘子后面那位养母——窦太后。
这位窦太后,手腕可不一般。刘肇并非她亲生,他的生母梁贵人,早就死得不明不白,据说就是拜窦氏所赐。窦太后以皇帝年幼为名,临朝称制,名为辅佐,实则大权独揽。
她把自家人安插得满满当当,哥哥窦宪是大将军,军政一把抓。弟弟窦笃、窦景、窦环等人也都占据要津。窦家俨然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朝廷上下,几乎成了他们家的天下。甚至荒唐到什么地步?窦宪手底下的人,敢当着皇帝的面,冲着窦宪喊“万岁”,要不是有正直的尚书韩棱出来呵斥,这场闹剧还不知道怎么收场。窦家人的跋扈,可见一斑。
想想刘肇当时的日子,能好过吗?住在皇宫里,却跟住在透明的玻璃缸里没两样,干点啥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想说句心里话,得憋着。想做点自己的事,门儿都没有。换个普通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不吓傻也得磨平了棱角。
可刘肇偏偏不是。或许是宫廷的残酷(比如生母的悲惨下场)让他早熟,或许是天生骨子里就有股韧劲,他在这种让人喘不过气的环境里,没垮掉,反而像块被反复敲打的铁,炼出了超乎年龄的隐忍和盘算。
他面上装得乖巧顺从,对太后毕恭毕敬,好像对朝政一点兴趣没有,整天就跟几个小宦官厮混。这副人畜无害的样子,确实让窦家人放松了警惕,觉得这小皇帝不过是个摆设,翻不了天。
然而,谁知道呢?就在这平静的水面下,一股暗流正在悄悄涌动。他心里清楚,要想不当一辈子提线木偶,要想堂堂正正做个皇帝,窦家这座大山,非搬开不可。
到了公元92年,刘肇十三岁,他感觉不能再等了。窦家的气焰越来越嚣张,甚至有风声说他们动了废立的心思。时间不等人,必须动手。
可他手里有啥?几乎啥也没有。兵权在窦宪那儿,朝政是窦家人说了算,连宫里的侍卫有多少是靠得住的都难说。放眼望去,能信得过、又能帮上忙的,似乎只有身边那些平日里不起眼的宦官。
宦官里头,有个叫郑众的,为人比较谨慎,对皇帝也还算忠心。刘肇开始有意识地接近他,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自己的苦闷和不甘。郑众是个明白人,渐渐摸清了小皇帝的心思。
他还挺有学问,给刘肇讲了不少历史上君主斗权臣,特别是收拾外戚的故事,比如汉宣帝是怎么干掉霍光家族的。这些前朝旧事,无疑给了困境中的刘肇极大的启发和勇气。郑众,就成了他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地下战友”。
光靠宫里的人还不行,得有外援。刘肇又悄悄搭上了自己的堂兄,清河王刘庆。刘庆是刘氏宗亲,眼瞅着窦家这么胡来,心里也早就窝着火,身边也聚拢了一些同样对窦氏不满的正直官员。
两人目标一致,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为了方便密谋又不引人注意,据说刘庆常常找借口留在宫里,跟刘肇同吃同住,商量对策。
就这样,一个以十四岁皇帝为轴心,由心腹宦官和宗室王爷组成的秘密夺权小分队,悄然成立了。他们这步棋,走得是真悬,每一步都得算计到家,不能有半点闪失。一边要暗地里搜罗窦家的罪证,一边还得物色关键时刻能站出来顶事的官员,同时更要耐心等着那个能一锤定音的绝佳时机。
公元92年六月,常年在外领兵的大将军窦宪,回到了京城洛阳述职。这对刘肇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窦宪是窦氏集团的主心骨,只要把他拿下,窦家就垮了一半。更关键的是,窦宪离开了他的军队大本营,在京城里,他的力量相对就没那么可怕了。
行动就在窦宪回京后不久的一个晚上,突然发动。过程听着不复杂,但每一步都跟踩在刀尖上一样。刘肇以皇帝名义,骤然下令关闭所有京城城门,全城戒严。这在当时绝对是个不同寻常的信号。紧接着,他调动了自己能掌握的、忠于皇室的禁军部队,兵分几路:
主力直扑大将军窦宪的府邸。窦宪哪儿能想到,这个平日里温顺得像只小猫似的小皇帝,敢玩这么大?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禁军冲进府里,迅速控制了局面,当场收缴了窦宪的大将军印信和绶带,фактически等于是解除了他的兵权,并将其软禁。
与此同时,另外几路人马也没闲着,按照预定计划,闪电般地逮捕了窦笃、窦景、窦环等窦氏核心人物。那些平日里跟着窦家作威作福的党羽们,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里,也纷纷落网,直接送进了大牢。
整个行动快得像一阵风,干净利索,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窦家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网络,就这么在一夜之间,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接下来是最难的一步:怎么面对窦太后?毕竟她是名义上的“母亲”,也是曾经的最高统治者。刘肇亲自去见了窦太后。
他没选择硬碰硬,而是玩了一手软硬兼施。先是恭恭敬敬地行礼问安,口称“母亲”,把面子上的礼数做足。然后,才平静而又坚定地,一条条摆出窦氏兄弟揽权乱政、图谋不轨的证据,表明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大汉江山,为了刘家天下,是迫不得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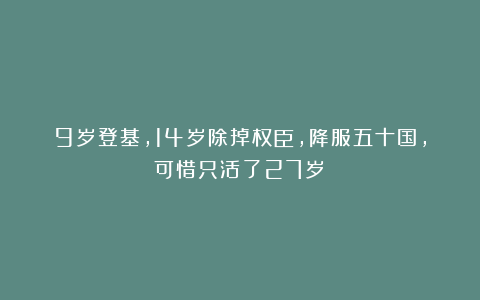
窦太后大概也是被自己这个养子突如其来的强硬和决绝给镇住了。或许是心虚,或许是被刘肇那不容置疑的帝王气势所慑,她最终选择了沉默,
有意思的是,刘肇并没有立刻处死窦宪等人,而是先把他们贬到各自的封国去,派了严厉的地方官看着,等到了地方,才最终下令让他们自尽。这手腕,既顾全了太后的面子,又彻底清除了后患,足见其心思缜密,手段老道。
就这样,年仅十四岁的汉和帝刘肇,靠着过人的胆识、周密的计划和盟友的配合,硬是从权倾朝野的窦氏集团手里,夺回了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这场干净利落的宫廷政变,在中国历史上,都算得上是少年天子逆袭的经典案例。
很多人可能会想,一个靠着这么激烈手段上位的少年皇帝,会不会从此变得多疑猜忌,或者沉迷于权力斗争?可刘肇接下来的表现,再一次让人刮目相看。
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没搞什么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而是立马把心思放到了治理国家上。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国家被窦家折腾了这么些年,到处都是窟窿,得赶紧补上。
他用起人来,眼光相当准。不管你出身高低,只要有真本事,他就敢用。比如,他重新起用了被窦家排挤多年的名将班超。班超也是个牛人,受命之后,在西域纵横捭阖三十多年,硬是凭着智勇双全,让西域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重新归附汉朝,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
刘肇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不惜千里迢迢下诏书,封他为定远侯,这就是“万里封侯”的典故。这不光是对班超个人的肯定,更是向天下人表明态度:只要你为国出力,皇帝绝不亏待你。他还多次下诏求贤,努力扭转窦氏当权时那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官场风气。
在内政方面,他大概是吸取了窦氏专权的教训,对权力保持着警惕。他着手整顿官吏队伍,严惩贪腐。推行宽缓的政策,要求司法官员断案时,在法律框架内尽量从轻发落,不搞严刑峻法。他还特别注意减轻百姓负担,多次下令减免赋税,让老百姓能喘口气,安生过日子。
据说,他常常亲自批阅奏章到深夜,对民生疾苦很是上心。比如永元八年(公元96年),京城洛阳闹蝗灾,他下的诏书里先反省自己:“蝗虫这玩意儿,大概不是凭空来的,天下的罪过,恐怕都在我一个人身上。”这话听着,透着一股真诚的自责和忧民之心。
他还做过一件挺实在的事,就是下令停止地方上费老鼻子劲,不远万里地往京城送新鲜荔枝、龙眼什么的,理由是这事儿劳民伤财,没必要。
在军事和边防上,除了搞定西域,他对付长期让汉朝头疼的匈奴和羌人,也很有一套。他派兵北上,打得匈奴残部一路向西逃窜。对付羌族叛乱,则是软硬兼施,有效地稳住了西部边境。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汉朝的边疆变得空前稳固,国威远扬。
正是在刘肇亲政的这十几年里,东汉王朝的国力确实达到了一个高峰。政治相对清明,经济繁荣发展,边疆安定拓展,文化也欣欣向荣。
后世史家把这段时期称为“永元之隆”,认为这是东汉历史上难得的好时光,国力之强盛,比如垦田面积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都是东汉的顶峰。
然而,就在这片繁荣景象之下,似乎也埋下了一些隐忧,刘肇当初夺权,出力最大、也最受信任的,就是宦官郑众。
事成之后,郑众被提拔为大长秋,这是一个可以经常出入宫廷、传递皇帝旨意、管理宫内事务的重要职位。刘肇可能觉得郑众忠心可靠,又熟悉宫廷运作,便常常同他商议国家大事。这就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要知道,东汉的制度设计里,本来就设有中常侍、黄门侍郎等一系列宦官职位,他们负责传达诏令、审阅文书,本身就离权力中心很近。刘肇倚重郑众,固然有报恩和信任的成分,但也无形中抬高了宦官群体的地位,让他们有机会更深地介入到朝政决策中来。
再加上,早期辅佐他的一些宗室老臣,比如帮他夺权的清河王刘庆等人,随着时间推移,或年老力衰,或不幸去世,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此消彼长之下,宦官的势力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后人评价这段历史,常说刘肇“赶走了窦氏外戚,却引来了宦官势力”。这话或许有点刻薄,但并非全无道理。他为了解决眼前的危机,选择了一条看似有效的捷径,却可能忽视了这条路长远的风险。
毕竟,东汉前几位皇帝,对于限制外戚和宦官干政,还是比较注意的。刘肇没能完全继承这一点,或许是因为他当时处境艰难,别无选择。或许是他过于自信,认为自己能驾驭住局面。
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位才华横溢、正准备大干一场的皇帝,身体却垮了。
也许是早年长期在压抑、恐惧的环境下生活,伤了根本。也许是亲政后太过勤勉,事必躬亲,透支了精力。史书上说,他二十出头,就已经是疾病缠身,汤药不离口了。可他好像总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依旧每天坚持上朝理政,批阅奏章到深夜,从不懈怠。
公元106年(也有说105年底),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皇帝,在首都洛阳病逝了。
他的死,对整个东汉王朝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朝野上下,一片哀鸣。老百姓感念他的好,官员们痛惜失去了一位难得的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