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的历史长河中,地雷作为一种隐蔽且极具威慑力的武器,始终占据着独特的地位。69 式反步兵跳雷,便是新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自主研制的一款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步兵武器。它不仅见证了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历程,更在实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尤其是在 1984 年的对越作战中,给越军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军事压力。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地雷作为一种有效的防御武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前,我国已经成功定型了58式、59式、66式反步兵地雷,但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以及对战场需求的深入研究,兵工行业意识到需要研制一款新型地雷以适应新的作战形势。
美国M16反步兵跳雷
彼时,跳雷作为一种在发达国家普遍装备的新型地雷。1942年,美国研发了M2跳雷,M2跳雷的抛射药是一枚60毫米迫击炮弹,一旦敌人踩中,它就会将一枚迫击炮弹直接弹飞到2米高度,杀伤半径为15米。
美军另一种制式跳雷是M16型,重量高达近4公斤,装药就有500多克。地雷被触发后,圆柱形抛射药会被弹到1.2米高度爆炸,产生至少600多个碎片,杀伤半径高达50米。
这种跳雷威力大、杀伤范围广的特点引起了我国军工部门的关注。跳雷不同于传统地雷,它设计为在地面以上爆破,通过将雷体抛射到空中爆炸,以破片杀伤行进中的敌人,几乎不存在杀伤破片覆盖不到的死角。于是,我国开始摸索自行设计此类新型地雷。
克服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及 “大跃进” 带来的负面影响后,我国兵工科研人员经过不懈努力,于1969年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种完全自主设计的现代地雷 ——69式反步兵跳雷。这款地雷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在武器设计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也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增添了新的力量。
69式反步兵跳雷主要由引信、抛射药、抛射筒、雷体、传火管、延期药、雷管和炸药等几个关键部分组成。
引信:采用压、绊两用引信,这一设计使得它既可以通过直接用绊线布置成绊发,也能够通过使用压板等装置设置成压发,极大地提高了布设的灵活性。
抛射药与抛射筒:当引信触发后,击发火帽产生的火焰通过传火管点燃抛射筒底部的抛射药包。抛射药包瞬间产生大量火药燃气,这些燃气产生的强大推力将整个弹体垂直向上弹起,使其脱离抛射筒。
雷体:雷体是跳雷的核心部分,69式跳雷使用的是铸铁弹体。在雷体内部,装有延期药、雷管和炸药等。当雷体被抛射到一定高度时,延期药点燃雷管,进而引发炸药爆炸,产生杀伤破片。
传火管与延期药:传火管负责将引信击发火帽产生的火焰传递到抛射药包处,确保抛射药包能够被顺利点燃。延期药则在雷体被抛射出去的过程中持续燃烧,当雷体到达距地面0.5-2米的高度时,延期药刚好点燃雷管,使地雷爆炸。
69式反步兵跳雷在威力设计上具有独特之处。当敌人不慎踩踏或者触及绊线触发引信后,雷体被抛射到空中,在距离地面 0.5-2米的高度爆炸。爆炸瞬间,所形成的杀伤破片会以雷体为中心,向四周呈扇形扩散,覆盖半径可达11米的区域。在这个范围内,所有暴露的人员都将面临破片的杀伤威胁。
相比传统的反步兵地雷,其腾空爆炸的方式大大增加了杀伤范围,减少了因地形等因素导致的杀伤死角。在开阔地带,69式跳雷能够有效地对行进中的步兵队伍造成重大打击,打乱敌方的进攻节奏,给敌方有生力量带来严重的伤亡。
但69式跳雷也因为当年中国工业技术能力还比较薄弱等原因,伴有不少问题。
引信安全性与操作复杂性:69式跳雷的引信安全性存在一定问题。在平时为了防止意外爆炸,必须将弹体、雷管、击发装置分开保存。在实际使用时,需要首先装击发装置,再装入雷管,最后撤除保险装置,整个操作过程较为繁琐,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这在紧张的战场环境下,可能会影响士兵的作战效率,甚至可能因操作不当而导致危险。
杀伤效果局限性:该雷使用的铸铁弹体没有采用杀伤钢珠或预制破片设计。这就导致爆炸后产生的杀伤破片数量相对较少,仅有200多片,而且破片分布不均匀。相比同时期美国和苏联跳雷20米以上的杀伤半径,69式跳雷11米的杀伤半径显得相对较小,在杀伤力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压发装置不完善:69式跳雷没有专门设计的压发装置,若要设置为压发爆炸,需要使用一个压板。具体操作方法较为复杂,要先将旋上击发机构的地雷放入雷坑中,并在保险销上系上细绳引出雷坑外,将压板轻轻盖上,覆土伪装后,再拉出保险销。这种繁琐的操作方式在实际战场中相当不实用,不符合一线作战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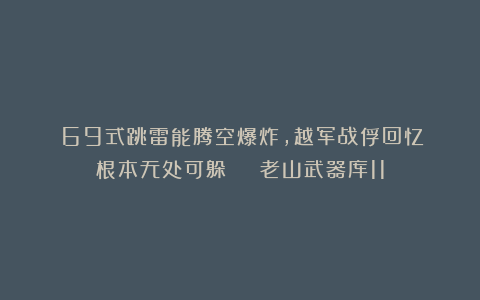
基于69式反步兵跳雷的这些缺陷,我国兵工部门此后经过3年的努力,于 1972年成功研制出了性能更为优良的72式反步兵跳雷。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越作战中,69式反步兵跳雷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在实战中仍然凭借其独特的杀伤方式和一定的威力,给越军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实际的人员伤亡,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保卫我国领土安全作出了贡献。它的存在也为我国后续地雷武器的研发和改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1979年3月的柯来西南侧无名高地的防御战中,我军某部8连为守住阵地,在阵地前埋设了132枚地雷,其中就包括75枚69式跳雷。3月8日,越军发动进攻,在突入雷场后,遭到我军埋设的地雷攻击伤亡惨重。之后越军一边排雷一边攻击,前后打了5次,均被8连击退,最终因兵力不足,越军撤离战场。
在1984年7月12日的松毛岭战斗中,我军在防御越军大规模反扑时,提前在阵地前沿布设了大量69式跳雷。战斗打响后,越军以密集队形向我军阵地发起冲锋,但在接近雷区时,多枚跳雷被触发,爆炸产生的破片覆盖了越军冲锋队伍,造成严重伤亡。据战后统计,仅在这一场战斗中,69式跳雷就造成越军数十人伤亡,有效迟滞了越军的进攻节奏,为我军组织反击争取了宝贵时间。
在1984年9月的者阴山战斗中,69式跳雷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军在者阴山地区实施防御作战时,利用地形特点,在越军可能渗透的路径上布设了跳雷。9月8日夜间,越军一支小分队试图从侧翼迂回,潜入我军阵地后方,但在行进过程中触发了跳雷。爆炸声引起我军警戒部队的注意,随即展开火力打击,成功击退了越军的渗透行动。战后清理战场时发现,跳雷的爆炸不仅直接击毙了数名越军士兵,还迫使其余人员暴露位置,为我军火力打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在1984年11月的八里河东山战斗中,69式跳雷也被用于封锁越军的撤退路线。11月20日,我军在一次夜间突袭中成功攻占了越军一处前沿阵地,越军在溃退时试图沿一条隐蔽小路撤离。然而,这条小路已被我军工兵布设了跳雷。越军士兵在慌乱中触雷,跳雷爆炸后产生的破片覆盖了狭窄的道路,造成越军多人伤亡,彻底切断了他们的撤退路线。战后,我军在清理战场时发现,跳雷的爆炸效果极为显著,越军尸体散布在雷区周围,显示出跳雷在实战中的高效杀伤力。
从参战老兵的回忆中也能看出69式跳雷在战场上的威慑力。一名我军工兵回忆道:“我们在布设跳雷时,特别注意选择越军可能经过的隐蔽路线。跳雷的触发机制非常灵敏,一旦越军踩中,几乎无法逃脱。爆炸后,弹片四散,覆盖范围广,往往能一次性杀伤多名敌人。”而一名越军俘虏在审讯中也提到:“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中国军队的跳雷,它们隐蔽性极强,爆炸后弹片像雨点一样飞来,根本无处可躲。”
综合这些战例可以看出,69式反步兵跳雷在1984年对越作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防御作战中的迟滞敌人进攻,还是进攻作战中的封锁敌人退路,跳雷都以其高效的杀伤力和战术灵活性,为我军赢得了宝贵的战场优势。
但也不能否认,玩地雷,越军也是老手,各种诡雷防不胜防,同样也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1984年7月12日的松毛岭战斗中,我军在防御越军反扑时,也遭遇了越军地雷的威胁。一名连长回忆:“我们在阵地前沿布设了跳雷,但越军也在夜间渗透时布下了大量地雷。第二天早上,我们的巡逻队在检查阵地时,一名士兵不慎踩中了越军埋设的压发雷,当场被炸断了腿。”这次触雷事件不仅造成一名士兵重伤,还暴露了我军巡逻路线,给后续防御带来了压力。
1984年9月的者阴山战斗中,我军在一次夜间侦察行动中,因不熟悉越军雷区分布,导致多名士兵触雷受伤。一名侦察兵回忆:“我们小组在夜间潜入越军阵地附近,试图摸清敌人的火力点。但在穿过一片草丛时,一名战友踩中了地雷,爆炸声惊动了越军,我们不得不紧急撤退。那名战友的腿被炸伤,血流不止,我们轮流背着他撤回了阵地。”这次触雷事件不仅导致侦察任务失败,还造成一名士兵重伤,影响了部队的士气。
1984年11月的八里河东山战斗中,我军在一次追击溃退越军的行动中,因急于推进而忽视了雷区的危险。一名排长回忆:“我们追击敌人时,看到越军仓皇逃窜,大家都想尽快追上他们。结果在通过一片树林时,一名战士踩中了越军布设的跳雷,爆炸后弹片四射,周围几名战士也被波及。”这次触雷事件导致三人受伤,其中一人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给部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从这些战例中可以看出,地雷在战场上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杀伤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触雷都可能造成严重的伤亡。我军在战斗中虽然采取了排雷措施,但由于越军雷区布设复杂,加之战场环境恶劣,触雷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些触雷事件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还对部队的士气和作战计划产生了影响。战后,我军加强了对地雷的防范和排雷训练,以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
作 者 | 大河弯弯
编 辑 | 春山
参 考 | 网络资料
图 片 | 网络图片
(若侵权请联系删除)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