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9-12q扩增标志一类具有奇异性肌上皮异型性的独特唾液腺肿瘤
摘要
背景:过去二十年间,分子改变的深入研究极大完善了唾液腺肿瘤的分类。许多既往难以分类的肿瘤,基于共同的组织学、免疫表型和分子特征,现已被识别为新型独立病种。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癌性肿瘤,而近期分子发现亦扩展至唾液腺腺瘤领域。本研究报道一组以显著奇异型肌上皮异型性为特征的双相性唾液腺肿瘤,其遗传学层面均存在12q扩增证据。
方法:筛选具有奇异但退变性异型性的唾液腺肿瘤。对病例进行免疫组化、MDM2和HMGA2荧光原位杂交(FISH)及靶向新一代测序(NGS)分析。
结果:共鉴定7例。肿瘤发生于腮腺(3/7)、口腔(3/7)及颌下腺(1/7)。患者包括5名女性和2名男性,年龄53-83岁(平均65.7岁)。组织学上,肿瘤边界清晰且部分包膜完整,呈高细胞密度实性生长,无软骨黏液样间质成分。肿瘤呈双相性结构:嗜酸性导管位于基底样细胞背景中,基底样细胞伴不同程度透明变及梭形化。所有病例最显著特征为散在分布具有奇异型核异型(染色质模糊)的细胞。该类奇异细胞核质比低,未见核分裂象。基底样细胞表达S100、p63和p40;导管细胞强阳性表达CD117和AE1/AE3,证实肿瘤双相性。奇异细胞显示肌上皮免疫表型。Ki67指数1-10%,且多数异型细胞不标记。4例NGS成功检测到12q拷贝数增加和5q拷贝数丢失;1例RNA测序显示MDM2和HMGA2表达升高;7例中6例FISH证实MDM2和/或HMGA2扩增。综上,所有病例至少通过一种技术显示12q扩增证据。
结论:具有奇异型肌上皮异型性的唾液腺肿瘤与12q扩增高度相关。尽管此类组织学改变可能令人警惕,但染色质模糊、核分裂活性低及Ki67标记稀疏提示其未必代表恶性。
深度分析
科学意义与创新性
1.新型病种的界定:
研究通过整合组织学、免疫表型和分子特征,首次将一种罕见双相性唾液腺肿瘤归类为独立实体。其核心标志是:
奇异型肌上皮异型性(核大深染但核质比低、染色质模糊)
12q扩增驱动(含癌基因MDM2和HMGA2)
2.分子分类范式强化:
补充了唾液腺肿瘤分子分型框架(如近年提出的纹状管腺瘤、闰管腺瘤等),凸显分子技术在疑难病例诊断中的核心价值。
3.恶性潜能的再审视:
传统观念中“奇异型异型性”易被误判为恶性,但本研究通过低Ki67指数(1-10%)和缺乏核分裂象,提出此类肿瘤可能属于良性或低度恶性潜能的交界性病变,挑战了既往形态学与恶性程度的直接关联。
研究方法亮点
1.多维度技术验证:
联合FISH、NGS和RNA测序,从DNA拷贝数、基因表达层面交叉验证12q扩增(尤其是MDM2/HMGA2),确保结果的可靠性。
2.精准免疫表型定位:
通过基底样细胞(S100/p63/p40+)与导管细胞(CD117/AE1/AE3+)的差异化标记,明确肿瘤双相分化本质;奇异细胞的肌上皮表型则提示其可能源自基底细胞层的异常增殖。
临床启示
1.诊断标志物的确立:
12q扩增联合MDM2/HMGA2过表达可作为此类肿瘤的分子诊断标准,避免将其误诊为多形性腺瘤恶变或其他高级别癌。
2.治疗策略优化:
若进一步随访证实其惰性生物学行为,或可避免过度治疗(如根治性手术或辅助放化疗)。
局限性及未来方向
1.样本量局限:仅7例需扩大验证。
2.随访数据缺失:需补充长期预后数据以明确其复发/转移风险。
3.机制待解析:12q扩增如何驱动肌上皮异型性?是否与其他通路(如TP53/5q缺失)协同作用?
总结
本研究通过多组学方法揭示了一类新型唾液腺肿瘤的分子本质,为精准诊疗提供了关键依据,同时也启示:分子时代的病理诊断需突破“以形态定恶性”的传统思维,整合遗传学特征方能实现更科学的分类。
引言
唾液腺肿瘤病理学是外科病理学中极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这既源于其显著的多样性,也与过去二十年间新型肿瘤变体及独立病种的爆发式增长密切相关。迄今为止,多数研究聚焦于唾液腺癌,但唾液腺腺瘤的分子特征也逐渐被揭示。例如,纹状管腺瘤、闰管腺瘤和角化囊腺瘤等新兴病种最近被发现具有重复性、且常具有肿瘤定义性的遗传学改变。
我们在临床中遇到一类难以归类的唾液腺肿瘤,其显著特征为散在分布的奇异型非典型肌上皮细胞。本研究旨在从分子层面对此类肿瘤进行表征,以探索其定义性的遗传学改变。
图1.肿瘤呈实性、高细胞密度、边界清晰且至少部分包膜完整。图示病例3(A)和病例1(B)。
图1分析:肿瘤大体与边界特征
关键信息:
实性高细胞密度:提示肿瘤增殖活跃,但缺乏囊性变或黏液样基质(区别于多形性腺瘤的软骨黏液区域)。
边界清晰与包膜:支持其可能为良性或低度恶性潜能,与侵袭性癌的浸润性生长模式不同。
科学意义:形态学初步提示非典型性肿瘤,需分子检测进一步分类。
图2.所有肿瘤主要由基底样细胞构成,伴胞质透明化及轻微梭形化,其间散在导管结构(A-C)。1例可见显著鳞状上皮化生(D)。图示病例3(A)、病例1(B)、病例5(C)和病例4(D)。
图2分析:组织学结构与细胞分化
基底样细胞特征:
胞质透明化:可能与糖原沉积或线粒体异常相关(需PAS或电镜验证)。
梭形化:反映肌上皮分化倾向(后续免疫组化证实)。
鳞状化生(D):罕见于经典多形性腺瘤,提示肿瘤可能具有独特分化路径。
对比意义:与基底细胞腺瘤(单一基底细胞群)不同,双相性结构(基底细胞+导管)更接近多形性腺瘤谱系。
图3.所有病例均以散在分布的奇异型非典型细胞为特征,细胞核巨大且形态不规则。这些细胞核质比低,染色质模糊,类似退变性或内分泌型异型性。图示病例6(A)、病例5(B)、病例4(C)、病例3(D)、病例2(E)及病例1(F)。
图3分析:奇异型核异型性的形态细节
核心特征:
核大、不规则但核质比低:区别于高级别癌(核质比高、染色质粗糙)。
染色质模糊(smudgy):与退变性/内分泌型异型性相似,可能反映DNA损伤修复缺陷或代谢压力,而非恶性增殖。
诊断挑战:此类细胞易被误判为恶性,但低Ki67指数(图4D)支持其惰性本质。
图4.免疫组化证实肿瘤的双相性结构:导管细胞强表达AE1/AE3(A),肌上皮细胞弱表达;
肌上皮成分强表达p40(B)
肌上皮强表达S100(C)(插图示奇异细胞呈肌上皮表型)。
Ki67指数为5%,且异型核基本不标记(D及插图)。图示病例4(A)和病例3(B-D)。
图4分析:免疫表型与增殖活性
双相性标记:
导管标志(AE1/AE3+):证实腺上皮成分。
肌上皮标志(S100/p40+):确认基底样细胞为肌上皮来源,符合多形性腺瘤的双相分化模式。
奇异细胞的肌上皮表型:提示异型性可能源于肌上皮克隆性增生伴随12q扩增驱动的遗传不稳定性。
Ki67低增殖:进一步支持肿瘤生物学行为偏向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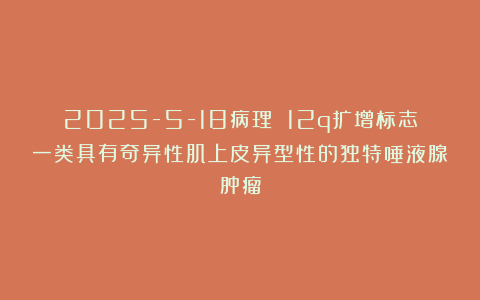
图5.荧光原位杂交(FISH)显示病例6存在MDM2扩增(红色信号,绿色为12号染色体着丝粒对照)(A)。
病例4中HMGA2断裂探针显示扩增与重排(5’端红色,3’端绿色)(B)。
图5分析:分子遗传学证据
MDM2扩增(A):
红色信号聚集:明确12q15区域扩增,与脂肪肉瘤分子特征重叠,但需结合组织学排除转移。
HMGA2扩增与重排(B):
分离信号(红绿分离):提示HMGA2基因断裂,可能为融合或复杂重排(如与WIF1),驱动肿瘤发生。
技术互补性:FISH与NGS联合使用可克服单一技术的局限性(如内含子融合或拷贝数变异的检测)。
总结
1.形态-分子关联:
双相性结构+12q扩增:提示此类肿瘤可能是多形性腺瘤的分子亚型(HMGA2驱动),但伴随独特退变性异型性。
奇异细胞本质:可能是HMGA2/MDM2过表达导致的异常终末分化,而非恶性转化。
2.诊断陷阱与启示:
避免过度诊断:奇异型核异型未必等同恶性,需结合Ki67、分子特征及临床行为综合判断。
分子检测必要性:对难以分类的唾液腺肿瘤,推荐12q FISH检测以识别此类独特实体。
3.未来研究方向:
HMGA2功能研究:其在肌上皮分化与退变性异型性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5q缺失的生物学意义:是否与12q扩增协同驱动肿瘤发生?
讨论
唾液腺病理学正经历一场变革,遗传学改变的认知已深刻重塑其分类体系。在许多情况下,当特征性基因融合在意外形态学背景下被识别时(例如Warthin样肿瘤中的MAML2融合现被视为Warthin样黏液表皮样癌),某些肿瘤的谱系得以极大扩展。另一些情况下,全新病种因新型基因融合的发现而诞生,如分泌性癌、微分泌性腺癌及微筛状腺癌。近期研究转向良性唾液腺肿瘤,基于遗传学的方法彻底改变了对纹状管腺瘤、闰管腺瘤及角化囊腺瘤等腺瘤的认知。这些肿瘤中特征性分子改变的发现,增强了对其相关腺瘤的诊断信心——尽管其生长模式常易与癌混淆。
本研究报道了一组以显著奇异型多形性肌上皮细胞为特征的双相性唾液腺肿瘤。此前少量小型研究曾描述过类似形态学特征,但病例被诊断为含奇异肿瘤细胞或退变性异型性的多形性腺瘤、含奇异肌上皮细胞的基底细胞腺瘤,以及伴古老性改变的腺上皮-肌上皮癌。本系列病例的分子分析表明,此类形态学特征与12q14.3-q21.2区域扩增(包含MDM2(12q15)和HMGA2(12q14.3))密切相关。此区域的扩增是已知的致癌驱动因素,以非典型脂肪瘤样肿瘤/高分化脂肪肉瘤及其偶发的去分化脂肪肉瘤最为典型。有趣的是,这些唾液腺肿瘤中的异型性形态与脂肪肉瘤中散在肿瘤细胞的异型性极为相似,提示两者具有相似的分子发病机制。HMGA2在唾液腺病理学中亦广为人知,因其融合是(起源于多形性腺瘤的)多形性腺瘤(及其癌变)中第二常见的驱动性改变。本系列中有2例通过FISH检测到HMGA2重排,其中1例RNA测序未发现融合,可能因复杂重排或涉及内含子的非经典融合导致。这些肿瘤的主要遗传学驱动因素可能是HMGA2融合,而通过“染色体外双微体”机制发生的12q扩增可能导致了额外的异常形态学改变。双微体缺乏着丝粒及其在细胞分裂时的不均等分配,可能解释了观察到的散在退变性异型性。
其他研究者在唾液腺肿瘤中也发现12q扩增。Grunewald等报道51例唾液腺导管癌中3例存在MDM2、CDK4和/或HMGA2扩增。Persson等发现16例中10例存在HMGA2扩增(包括6例多形性腺瘤和4例癌在多形性腺瘤中),但未提供组织病理学图像。值得注意的是,4例伴HMGA2扩增的癌在多形性腺瘤随访中均无恶性行为。Roijer等报道1例诊断为癌在多形性腺瘤的肿瘤存在12q扩增,其诊断基于显著多形性且镜下呈现与本系列相似的奇异型异型性。该病例被认为存在微浸润(但难以通过显微图像确认),且患者3年后无复发或转移。Mariano等报道2例癌在多形性腺瘤(1例微浸润,1例广泛浸润)伴12q扩增及其他拷贝数改变,但缺乏随访且未显示奇异型异型性。Katabi等报道1例伴HMGA2::WIF1融合及12q扩增的肿瘤后续发生转移。Alsugair等近期研究描述4例伴12q扩增的癌在多形性腺瘤,其中2例携带HMGA2融合,仅1例报告浸润性且未转移或复发(随访有限)。该系列显微图像未显示奇异型肌上皮异型性,但强调了一种“齿轮样”核特征(与本系列不同)。
尽管这些文献假设12q扩增与恶性转化相关,但许多情况下恶性诊断至少部分基于与本系列相同的奇异型异型性。此类异型性的显著形态令人警惕,本系列中6例有2例最初被诊断为恶性。然而,有理由认为其本质为良性。尽管随访有限,但无恶性行为报告。虽然存在明确伴12q扩增的癌在多形性腺瘤病例,但多数报道的此类肿瘤未转移或复发。此外,异型性虽引人警觉,但其染色质模糊特征常与退变性异型性(如内分泌器官的“内分泌异型性”及神经鞘瘤的“古老性改变”)相关,且异型核无核分裂活性且Ki67阴性。最终,这些肿瘤的生物学潜能需通过临床行为确定,目前尚未明确。
本系列中4例拷贝数分析病例均显示5q11.1-35.3区域缺失。尽管5q缺失在肿瘤中的研究不如12q扩增深入,但已在多种肿瘤类型中被记录[21-24]。Persson等在3例癌在多形性腺瘤中发现此区域缺失。缺乏明确候选基因使此发现的生物学意义难以推测,但其在本系列中的重复出现提示其可能参与细胞表型的形成。
病例4中检测到的ARID2::TNNI1和PPP1R12B::PLCO融合(同时伴12q扩增)意义不明。TNNI1和PPP1R12B位于1q32.1,而ARID2、HMGA2和MDM2均位于12q,提示涉及这些位点的复杂结构重排。ARID2属ARID家族DNA结合蛋白,参与细胞周期调控、转录调控及染色质重塑;TNNI1编码成人骨骼肌慢肌钙蛋白I。因两基因保留所有外显子,重排可能导致启动子互换(后果未知)。PPP1R12B(MYPT2)主要在骨骼肌和心肌表达,而PLCO编码中枢神经系统谷氨酸能及GABA能突触前细胞骨架蛋白(非胆碱能神经肌肉接头),此融合后果亦未知。
病例6中的APC无义突变提示其可能属于基底细胞腺瘤谱系(因基底细胞腺瘤以Wnt通路异常为特征,多涉及CTNNB1或CYLD,偶见AXIN1或APC突变)。但该病例同时存在STAG2和WRN无义突变(参与DNA复制/修复)及PIK3R1剪接位点突变。病例3携带ATM突变(参与DNA损伤应答)。本队列中Wnt通路突变无重复性,提示病例6的APC突变可能为继发性改变。
综上,我们报道了7例以肌上皮成分显著奇异型核异型为特征的双相性唾液腺肿瘤,均存在12q扩增。其双相性及扩增区含HMGA2提示其可能属于多形性腺瘤家族。尽管显著细胞异型易被归为恶性,但奇异型肌上皮细胞的临床意义尚不明确。
深度分析
1. 分子病理学范式转变
分类体系的动态演变: 讨论强调唾液腺肿瘤分类正从纯形态学驱动转向分子遗传学主导。例如:
MAML2融合的发现使Warthin样肿瘤被重新归类为低度恶性潜能的黏液表皮样癌。
ETV6-NTRK3融合定义的分泌性癌,彻底改变了传统基于形态学的诊断框架。
良性肿瘤的分子解析: 既往“良性”腺瘤(如纹状管腺瘤)因特定基因变异(如PLAG1重排)被确立为独立实体,提示分子特征可超越形态学异质性定义疾病本质。
2. 12q扩增的生物学启示
驱动基因的双重作用:
HMGA2:在多形性腺瘤中常见重排(如与WIF1融合),可能通过染色质重塑促进肿瘤发生;其在12q扩增中的过表达可能增强致瘤性。
MDM2:通过抑制p53通路促进细胞增殖,但在唾液腺肿瘤中可能与其他通路(如PI3K/AKT)协同作用。
分子-形态学关联性: 12q扩增导致的**染色体外双微体(DM)**机制可能解释肿瘤细胞的异质性分布:DM缺乏着丝粒导致分裂时随机分配,形成散在分布的奇异细胞(类似脂肪肉瘤中的“奇异细胞”)。
3. 恶性潜能争议的核心矛盾
形态学警示 vs 分子惰性:
支持良性的证据:
低增殖活性(Ki67<10%,无核分裂象)。
多数病例无转移/复发(即使最初误诊为恶性)。
异型性特征与退变性改变(如内分泌肿瘤中的“古老性改变”)相似。
潜在恶性风险的线索:
个别病例(如Katabi报道的HMGA2::WIF1融合合并12q扩增)发生转移。
分子复杂性(如合并5q缺失、ATM/PIK3R1突变)可能预示亚克隆进化。
分类困境的解决方案: 提出将此类肿瘤暂归类为**“具有不确定恶性潜能的肿瘤”**,需长期随访明确其生物学行为。
4. 与其他研究的对话与分歧
12q扩增的异质性意义:
脂肪肉瘤 vs 唾液腺肿瘤: 虽共享12q扩增,但脂肪肉瘤中的MDM2扩增伴随CDK4扩增,而唾液腺肿瘤中更常见HMGA2异常(融合或扩增),提示组织依赖性致癌机制。
癌在多形性腺瘤中的矛盾发现: Persson等研究显示伴HMGA2扩增的癌在多形性腺瘤无恶性行为,挑战了传统“癌变”定义,提示需结合分子特征重新评估恶性标准。
5. 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样本量与随访限制:
仅7例且随访时间短,需扩大队列验证12q扩增的预后意义。
分子机制的黑箱:
5q缺失的功能意义:该区域含APC、TRIO等基因,但其在唾液腺肿瘤中的作用未被阐明。
融合基因的未知效应(如ARID2::TNNI1):需功能实验验证其是否驱动肿瘤发生或仅为“乘客突变”。
临床诊断的挑战: 需建立分子-形态学整合诊断标准,例如:当形态学显示奇异型肌上皮异型性时,建议常规检测12q扩增/HMGA2状态以辅助分类。
6. 多学科协作的必要性
病理-分子-临床的三维整合: 此类肿瘤的诊断需综合:
形态学警惕性(识别奇异型细胞及双相结构)。
分子验证(FISH/NGS检测12q扩增及HMGA2状态)。
临床谨慎管理(完整切除+密切随访,避免过度治疗)。
总结
本讨论通过多维证据链,揭示了12q扩增在唾液腺肿瘤中的独特地位,并挑战了传统以形态学判定恶性的范式。其核心启示在于:分子时代需以“基因-形态-临床行为”三位一体框架重新定义肿瘤本质,尤其对形态学警示但分子惰性的病例,应避免过度诊断与治疗。未来需通过大样本前瞻性研究,建立基于分子分层的精准诊疗路径。
Bishop JA, Nakaguro M, Palsgrove D, Gagan J, Koduru P, Rooper L, Smith MH, Shows J, Tada Y, Nishimura H, Matsuno M, Utsumi Y, Nagao T. 12q Amplification Characterizes a Distinctive Salivary Gland Tumor with Bizarre Myoepithelial Atypia. Head Neck Pathol. 2025 Mar 15;19(1):31. doi: 10.1007/s12105-025-01770-6. PMID: 40088390; PMCID: PMC11910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