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的一纸公告震动了中国文坛——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个曾经在山东高密农村放牛的少年,用他独特的笔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评委会的授奖词精准地捕捉到了莫言创作的灵魂:他将魔幻与现实熔于一炉,在福克纳式的叙事结构与马尔克斯式的魔幻色彩中,又深深扎根于中国民间说唱艺术与传统文学的沃土。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在莫言构建的文学王国里,’高密东北乡’是最醒目的地标。这片虚构的乡土既是他真实故乡的投影,又是一个充满寓言色彩的文学空间。电影《红高粱》中那片炽热的红高粱地,那些在黄土坡上肆意生长的生命,都是这个文学世界的生动写照。从《透明的红萝卜》到《丰乳肥臀》,莫言笔下的人物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他们的悲欢离合折射出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
获得诺奖后,莫言依然保持着农民般的朴实。他常说自己是’讲故事的人’,这个称谓背后,是一个作家对民间叙事传统的坚守与创新。从胶东平原的田间地头到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莫言用他的文字证明:最地道的中国故事,同样能够打动世界。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文学种子
在山东高密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少年莫言的文学梦始于最朴素的渴望。每当夕阳西下,放牛归来的他总爱坐在村头的石碾上发呆,脑海里盘旋着从《封神演义》里看来的神奇故事。为了借到一本书,这个倔强的少年可以帮人推一整天的石磨,汗水浸透粗布衣衫也浑然不觉。村里人都说,管家的二小子看书看魔怔了,连放牛时都揣着本破旧的字典。
那些年的夜晚,莫言家的土屋里总亮着豆大的灯火。他和二哥挤在门槛边,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贪婪地阅读。门槛上的凹痕一年比一年深,就像少年心中疯长的文学梦。没有纸笔,他就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写画画;没有新书,连糊墙的旧报纸都能让他反复研读。村里老秀才家的《三国演义》缺了十几页,他硬是靠想象补全了缺失的情节。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关于当作家的梦想,源于邻居一句无心之言。那年冬至,莫言听见大人们说,城里的作家顿顿都能吃白面饺子。这个为半块霉红薯干和姐姐抢哭的孩子,第一次把’作家’和’吃饱饭’画上了等号。许多年后,当他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总会想起那个为吃饺子想当作家的少年。
在后来《丰乳肥臀》等作品中,那些对食物近乎神圣的描写,都带着童年的烙印。莫言总说,挨过饿的人才能懂得粮食的金贵。就像他笔下那些在高粱地里挣扎求生的人物,那种对生存最原始的渴望,成就了他作品中最打动人心的力量。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从军营到文坛
那个背着行囊离开高密东北乡的年轻人,在军营里找到了新的天地。白天,他是认真负责的保密员;夜晚,他伏在集体宿舍的床头,就着昏黄的台灯写下一行行文字。投稿信像候鸟一样飞向全国各地,又像退潮般带着退稿信回来。有些信封边角已经磨破,里面的稿纸皱皱巴巴,编辑部的铅印退条千篇一律。但莫言从不在意战友们的调侃,依旧坚持把每个月的津贴省下来买稿纸和邮票。
转折发生在那个普通的早晨。收发室的老班长举着一封信喊道:’管谟业,有你的信!’这次不是退稿,而是保定《莲池》杂志的用稿通知。莫言捧着那本刊登着《春夜雨霏霏》的杂志,闻着油墨的清香,在训练场上走了好几个来回。那年他当上了父亲,女儿的笑声让他笔下的文字愈发温暖。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命运的齿轮继续转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徐怀中先生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学生。莫言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文学养分,图书馆里总能看到他埋头苦读的身影。同学们记得,他总爱蹲在走廊尽头的暖气片旁写作,说这样能让思维更活跃。《透明的红萝卜》就是在这里诞生的,那个能看见萝卜芯里流动汁液的黑孩,让整个文坛记住了莫言的名字。
此后的创作生涯如同开闸的洪水。《红高粱家族》里那片血色的高粱地,《丰乳肥臀》中母亲坚韧的脊梁,《檀香刑》里残酷而诗意的刑罚描写,《生死疲劳》里六道轮回的荒诞视角,每一部作品都在突破前作。莫言常说,写作就像种地,要舍得下力气,也要懂得节气。他保持着惊人的创作节奏,有时一天能写上万字,有时又会为一个人物的命运辗转反侧好几天。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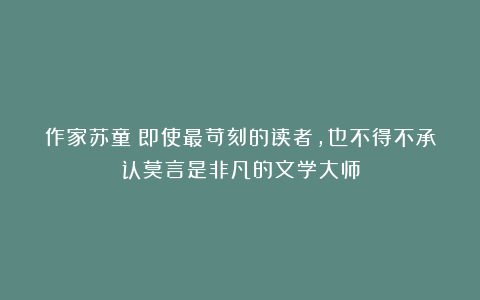
当《蛙》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已经完成了从乡土作家到文学大家的蜕变。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在世界各地流传。但莫言始终记得军艺教室里徐怀中先生的教诲:写作不是追名逐利,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高粱地里
那部改变莫言命运的电影,始于军艺宿舍里一个奋笔疾书的夜晚。当同学们都已入睡,莫言还在就着台灯写《红高粱》的最后几页。稿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里,跃动着高密东北乡那片野性十足的高粱地,还有他祖父辈那些敢爱敢恨的故事。小说发表后,在文学圈激起不小水花,但真正让它家喻户晓的,是那个刚从摄影转行做导演的年轻人——张艺谋。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800元的电影版权费,在当年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莫言签合同时没想过,这笔交易会成就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段佳话。张艺谋带着剧组驻扎高密三个月,为了拍出最真实的高粱地,他们特意种了几十亩红高粱。电影里巩俐饰演的九儿穿着红袄站在高粱丛中的画面,后来成为影史经典。当样片在试映室播放时,莫言看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自己笔下的文字能变成如此震撼的视觉冲击。
电影上映后的盛况超出所有人预料。街头巷尾都在传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连卖冰棍的老太太都能哼上两句。原本几毛钱的电影票被黄牛炒到十块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天的工资。在柏林电影节上,当金熊奖的奖杯被举起时,西方观众第一次通过银幕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功夫片的中国——粗犷、原始、充满生命力。也难怪作家苏童感叹:“即使最苛刻的读者,也不得不承认莫言是非凡的文学大师!”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饺子里的人生
在北京那套91平米的部队宿舍里,莫言的生活简单得令人意外。清晨,他总爱泡一壶高密老家带来的茉莉花茶,坐在阳台上看会儿书。厨房里,妻子杜勤兰正在和面,准备包饺子。这是他们最常吃的改善伙食,也是莫言几十年来最爱的味道。邻居们常纳闷,这么大的作家家里怎么很少见大鱼大肉,倒是阳台上总晾着各种野菜——那是老家人捎来的,莫言说这些带着泥土味的野菜最养人。
杜勤兰至今记得刚来北京时的日子。那时女儿笑笑还在上学,全家就靠莫言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有次女儿要交补习费,夫妻俩翻遍抽屉才凑齐。即便如此,当老家修路需要捐款时,莫言二话不说拿出3万元,名字刻在功德碑第一位。村里人都说莫言出息了不忘本,却不知道这笔钱是他攒了好几年的稿费。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这个在文坛叱咤风云的作家,在家里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丈夫和父亲。他给外孙女取名’一诺’,说是要让孩子记住’一诺千金’的道理。每天不管多忙,他都要陪孩子玩会儿,有时蹲在地上当大马,任孩子骑在背上咯咯笑。夜深人静时,他常戴着老花镜给老家的父亲写信,一笔一划写得认真,就像当年在棉花厂给杜勤兰写情书那样。
获得诺奖后,有人问750万奖金怎么花。莫言盘算着在北京买套大房子,可算来算去也只够买120平。他笑着对记者说,看来作家再有名也赶不上房价涨得快。这笔钱最后大部分都用来设立了’莫言文学基金’,资助那些和他当年一样怀揣文学梦的年轻人。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在文学圈里,莫言的朴素是出了名的。作协开会时,别人都穿名牌,他就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这种质朴来自他早年的经历,就像他总说的:’饿过肚子的人,知道粮食的金贵;受过苦的人,懂得平淡的滋味。’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莫言,创作速度越来越慢。不是写不动,而是对每个字都格外较真。他常说,写作就像种地,不能光图快,得等庄稼自然熟。有时为了一个细节,他会专门跑回高密,蹲在田间地头观察好几天。这种近乎固执的认真,让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土地般的厚重质感。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在名利场中打滚多年,莫言最珍视的还是家庭。每当有人夸他作品好,他总说最大的成就是娶了个好媳妇。杜勤兰只有小学文化,可莫言说她是自己最好的读者,能一眼看出哪些情节是编的,哪些是真事。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比任何奖项都让他感到满足。
夜深了,莫言的书房还亮着灯。桌上摊着写了一半的手稿,旁边是女儿刚送来的饺子。他咬了口饺子,突然想起几十年前那个放牛娃的梦想——当作家就能天天吃饺子。如今梦想成真,可他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和杜勤兰在棉花厂食堂分吃一个饺子的时光。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