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文教师的角度看《藏在罐子里的爱》,我觉得唯有“真情”此外并无特别。即便被普遍叫绝的“只是一层薄薄的土,人与人就再难相见了”这句话,我们也不难在历来的悼亡诗中找到类似的句子。但在“真情”成为稀缺资源的当下,它就有了制胜法宝。网络世界的逻辑看似无逻辑其实自有其真逻辑,在群体情感饥渴与情感遗忘的时候,在看了太多的装腔作势的“假文章”后,大家突遇“甘泉”,于是寻常文章就“看哭全网”了。山泉本寻常物,幸遇长途奔袭的征夫或负重的樵夫,它就成了“甘泉”。某种程度上,《藏在罐子里的爱》叫拼命奔跑的我们停下来或跑慢点回头看看,因为我们好久没有回头了。
我有奶奶的日子是30年,失去奶奶的日子已32年,今天重读拙文,情不自禁地想:“被啃老”何尝不是件幸福的事!
奶奶教会我从“爱”中找到快乐
早晨洗漱时随机点了个视频看,看的是《我是演说家》中刘轩的演讲。刘轩说,他今天的演讲不讲父亲刘墉,要讲他的奶奶。演讲十分钟左右。听到一半,我脑子里蹦出一个念头:有奶奶的日子并不长。其实,每个人都有奶奶,但不是每个人都和奶奶在一起生活过,甚至不是每个人都见过自己的奶奶。我有奶奶的日子是30年,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约20年;我儿子有奶奶的日子是26年,累计一起生活的时间可能不到2年……想到这里,我放下洗脸的毛巾,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愣了半天。
我奶奶生于1905年农历10月26日,属蛇,我出生时她58岁。我15岁上高中开始住校,此后和奶奶长住在一起的日子就很少。奶奶公历1994年元月去世,具体哪天我已记不清。去世前偶染小疾,没几天就过世了。基本可算无疾而终,享年90虚岁。我在外地工作,没能给他送终,但我儿子恰好被我小妹带回老家,算是代我给老太太送了终。奇怪的是,当时只有两岁八个月的儿子一直记得我抱着他在老太太坟头“兜土”的事。
(1990年春节全家摄于祖屋门前)
我关于睡觉的最初记忆是发生在爷爷奶奶的床上。我很小的时候和爷爷奶奶睡一床。我和奶奶睡一头,爷爷睡另一头。我小时候是被当作女孩儿养的,辫子扎到快上学的时候。我也不肯剪指甲,手指甲脚趾甲都很长。我喜欢侧身蜷缩着睡觉,常常半夜突然翻身伸腿,每逢此时,爷爷都要长长地“哎哟”一声,因为他大腿上的肉被我的脚指甲狠狠地划了一道血痕。我睡觉前总要摸摸奶奶干瘪的乳房,也常在朦胧中掐奶奶的乳头,奶奶“哎哟”一下我便缩手,然后又睡去。家中那只比我资历老的老猫,总是在半夜我不知晓的时候钻进被窝依偎在我的臀边,我一翻身它往往也是“喵”的一声逃出被窝。我自小睡觉就动静大,至今如此。大约在弟弟也可以独睡时,我离开了爷爷奶奶的被窝,和弟弟睡一张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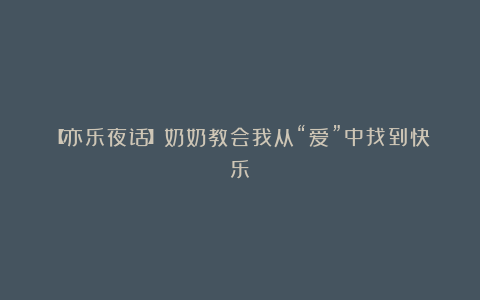
儿时我一直以为爷爷奶奶是可以陪我一生的,直到爷爷去世时我才深刻地认识到奶奶有一天也会去世的。那年奶奶71岁我13岁。爷爷去世后,晚年的奶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大妹和她睡在一起的。在那之后,她的房间我就很少进去。我现在回故居一定要到奶奶房间去看看,感觉没有印象中那么大。奶奶去世后,她的房间一直就空在那里。
我奶奶对我的宠爱是远近闻名的。在没有饭吃的年代,我从未饿过肚子,而且不缺少肉、蛋。我一直是吃着可口的新鲜蔬菜和水果长大的,因为我有一位勤劳的母亲和慈爱的奶奶。家里的鸡能生不少蛋,种的南瓜能有不少的瓜子,但来客人总是要买鸡蛋买瓜子,父亲总觉得奇怪,甚至有一次还发了火,但因为不太管家里的事,总是过后即忘。其实,家里的鸡蛋和瓜子大多数都是祖母悄悄做给我吃掉了(其实父亲、母亲心知肚明,不说而已)。我并非好吃,但禁不住奶奶的宠爱,她常常是“偷偷摸摸”地煮鸡蛋给我吃。我印象里,油炸锅巴是每天必吃的,饭后再拿一个饭团或一块很香的锅巴边走边吃是我和弟弟的招牌动作,很让别人羡慕。我吃瓜子的水平比较高,完全是小时候练就的功底。直到我工作后,她还会积攒一些鸡蛋,“偷偷”找路过我家的乡亲帮着卖掉,得来的钱攒在那里,等我回家给我。我不要她便掉泪。我上大学离开家后,凡我用过的东西,奶奶是不允许别人乱动的。有一次,我一个姑表弟拿走了我儿时常吹的一个大海螺(非常奇怪的是只有我一个人能吹响),奶奶竟然亲自跋涉数里山路硬给拿回来了。他对我姑姑说,“跃林还要玩的”。这样的故事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怀念奶奶。
(看到这只海螺我就想起奶奶)
因为是长孙,我在家里独享了更多宠爱。在奶奶的眼光中,我的地位是高出爷爷和父亲的。最好吃的,即使是招待客人的,她必定也要提前用小碗装一份放在锅边井罐上保着温。从有记忆开始直到她去世,我在家吃的饭多半是她盛好的,特别是第一碗饭。因为我嗜读,吃饭不喊几遍是不上桌的,所以基本都是奶奶盛好饭后被她三催四请才上桌吃饭。因为是她盛饭,所以还会不时出现吃着吃着突然发现饭里还埋着块肉,虽然我常有愠意,也只能看着奶奶紧盯我的眼神而意会。我读高中时寄宿,周日返校时会带一瓷缸咸菜。我带的咸菜是奶奶用大油炒的,非常好吃,但家里的咸菜往往少油。有一次,奶奶炒多了装不下,留下一小碗,大妹一吃便说:“怎么大哥哥带的菜这么好吃!”其实奶奶是偏心的。在奶奶看来,家里分“我”和“其他人”两类,必须先考虑我,然后才是其他人,包括爷爷。奶奶总是怕我读书累。我在家的时候,她总是一会儿来看一次,要么让我歇歇,要么端茶送水送点心。我唯一有一次可以成为飞行员的机会,也因为她的不舍,在最后的时刻放弃。我上大学她要去看,我工作了她也要去看,但均因她年高而又路远交通不便而未能如愿。1988年我分了套新房,她高兴地问弟弟“上厕所远吗”,弟弟逗她“不远,跟厨房隔壁”,她念叨了很久,“就是厕所和厨房太近。”
奶奶并非我的亲奶奶,他是父亲的舅妈,准确地说是我的舅奶奶。从遗传角度看,我和她之间并无血缘关系。然而人之为人正因为感情可以超越血缘关系。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叫“姚王氏”,她一定有本名,然而我从未问过。我祖父叫“茂菁”,文乎乎的,生于1897年,属鸡。我印象里他是蓄长须、穿长袍、戴老花镜的,他总是喜欢和我开玩笑,但我有点怕他,因为他总是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年轻人能说出祖父、祖母的姓名和年龄,可见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很不可靠的。儿时,我因为受到祖母的宠爱常常被人羡慕,有时也被人讥笑,所以对祖母的宠爱时有抵触。我在初中读书时,有一次因为天气炎热,祖母竟然亲自到学校给我送饭,招来了老师和全班同学的哄笑。刘轩说他奶奶是四寸金莲,我奶奶真的是三寸金莲,走那么多的路一定很辛苦。那次我哭了,奶奶自觉犯了错一样地也流了泪。但我自小是个乖孩子,我从未有过大声对奶奶说话,虽然她的过分宠爱有时让我难堪,但我知道这是我的福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也不会是一辈子都有的。
大学2年级,父亲因病去世,我帮助母亲操持这个家,我很快学会了包括做饭在内的各种家务活。直到工作以后,我仍然参加很艰苦的体力劳动。奶奶和妈妈虽然很心疼,但她们没有阻拦我,因为我已经到了该承担责任的年龄。所以,我的体会是,做父母的,对孩子是否宠爱并不重要,关键要教育孩子明白事理。动辄体罚,也要让他明白事理;让他在自己头上“做窝”,还是要让他明白事理。只要能明白事理,就能应付从天堂堕入地狱的变故,而那些小挫折更能应付裕余。专门的挫折教育纯粹是扯淡,让孩子徒步三五里就能培养抗挫折的能力实在是肤浅的教育理念。我甚至认为完全达不到目的,最多是一次徒步体验而已。
祖辈对孙辈的爱有甚于父辈,但孙辈对祖辈的爱往往很缥缈,乃至于“没感觉”。有奶奶的日子并不长。脑子里萦绕过这句话,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感谢奶奶!她教会我如何从对一个人的“爱”中找到快乐,这是我今天最大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