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尤爱画那些老门楼,门板早已褪了色,木质纹理却愈发清晰。有的门环已然锈蚀,却仍固执地扣在门上,仿佛还在等待什么人来叩响。学生们每每嫌其破败,我道:”破败处正是精神所在。”他们未必懂得,只管低头作画。
老槐树是最难描摹的。枝干虬曲,如老人暴起的青筋。夏日浓荫匝地,秋日黄叶纷飞。我画它不下百次,竟无一次相同。树下的石磨盘早就不用了,却总有人坐在那里歇脚。先是村中老人,后来是偶尔闯入的游客,如今竟是我的学生们最爱占据的位置。
线描之道,贵在取舍。我常对学生言:”须画其骨,而非其肉。”那些老房子的飞檐斗拱,若一笔笔如实描来,反倒失了神韵。有时略去几处砖瓦,线条反而活了起来。学生们初时不解,后来渐渐明白,这取舍之间,原是对物事最深的体贴。
村中有一处院落,门楣上”耕读传家”四字已然模糊。我每次来必画它,每次画法各异。或细如发丝,或粗若游龙。主人早已不在了,空余院落任风雨侵蚀。去年再去,门楣竟已坍塌,徒留一地的碎木残砖。我蹲在地上画了半日,有学生问:”老师,这有什么好画的?”我未答,只教他看那断口处的年轮。
冬日的骆驼道最为萧索。老树枝丫刺向灰白的天空,院墙上的枯草瑟瑟发抖。我们呵冻作画,墨水瓶都结了冰碴。这般天气,村中更无人迹,唯有我们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此时作画,线条反倒最为刚劲有力。
千幅线描,千种心境。同一处老房子,晴日画来明朗,雨天描之湿润;晨起时线条清新,傍晚时笔意苍茫。学生们笑我痴,我亦不自辩。他们哪里知道,这些线条早不是单纯的勾勒,而是我与这古村的一场无声对话。
近来村中渐有游客,偶见我们作画,便围拢观看。有夸赞的,有不解的,更有出价求购的。我皆婉拒。这些线描,原是我与这即将消逝的村落之间的私语,如何卖得?
近些日整理画稿,竟发现同一株老槐,已画了好几十幅幅。从茂盛到凋零,从完整到残损。我的线条,也从最初的工整谨慎,到如今的率性而为。这槐树若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它早已认命,静候着某日轰然倒地,化为灶中之柴。而我的线描,不过是徒劳地想要挽留些什么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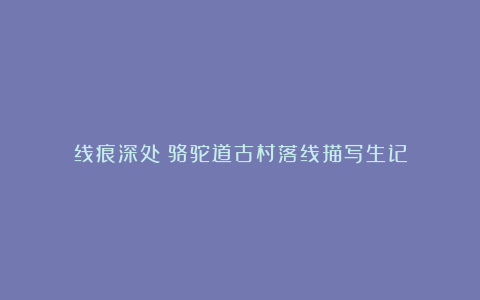
笔下的线条越来越简,心中的眷恋却愈加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