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春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马晓春,是中国重症医学分会发起者之一,辽宁省lCU奠基人。
撰写中国重症医学成长与发展史,马晓春是绕不开的人物。采访他,听他讲讲从事lCU的经历吧一一
我从事专业或者说从事医疗,有一些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读中学的时候,不太喜欢学医,那时候给我们的信息是,学医都要死记硬背,男孩子不太喜欢这个事。但是我比较特殊,稍微有一点戏剧性,我当初报的是工科理科的,但我父亲特别希望我学医。我把志愿报上去之后,在层层上报的过程中,我父亲竟然通过他的关系的把我的志愿给改了。我自己不太情愿地进入到医学院。
我中国医科大学78级的,学校在沈阳。在那个年代你想玩都没机会,没人陪你玩,想不用功都不行,周边人全在用功,你是被裹挟着往前走。
是什么时候对做医生感兴趣的?大概是进入临床课程之后,我说这个挺好玩,临床课程挺好,11月份毕业前一年,医科大学最早有英文班、日文班,我被分到日文班。我们教学的老师都是过去满洲国培养的,所有的课程都是用日本讲,相当于在日本上课,挺有意思。以后到临床实习觉得更有意思,因为它可以很直接的解决问题。考研究生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得很顺,毕业留校工作两年以后考博士又出国拿了学位。
我最早在呼吸科,实际呼吸科也蛮好,因为呼吸科就有部分患者是很危重的,需要做呼吸机。就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很好的ICU监护室,条件相对差,但是呼吸机有了,有些病人还能够救过来,所以说我挺感兴趣。2000年初,医院要重新组建一个全新的ICU,问我想不想干,我是机缘巧合,水到渠成。确实需要有个人来做这个工作,自己比较喜欢,另外以前有些基础,就这样自2000年初开始,在ICU干了差不多20年。
一个新兴的学会,在短时间内能够使整体规模和学会影响力发展到现在,确实不容易。重症医学领域,有一些专题会特别好,比如说像邱海波教授做的呼吸方面的专题,像我们做的全身严重感染的专题,严俊教授做的心脏重症专题,重症营养、重症镇痛镇静等等,影响力都很大。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学术的引领,学术的研究,对基础教育的推动和培训的推动作用也很大。
中华医学会和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包括医师学会,都有各自的工作。那么中华医学会这边做的是5C,做了100多期,培养了好几万人。我除了参与全国的大的事件推动之外,还主持辽宁的ICU,跟你讲讲辽宁的情况吧一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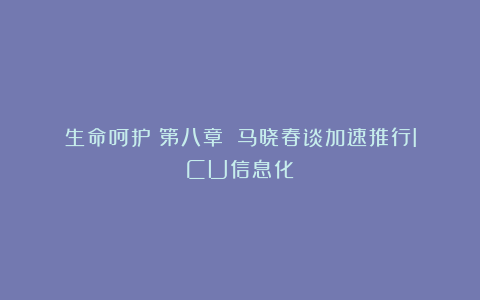
就全国而言,骨干的ICU还没那么多,但我觉得辽宁骨干的ICU已经很多了,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好的ICU。为什么?因为爱ICU的病人他不能随便走,他只能得了病,出了问题就在那个地方,转运起来很困难。不是说不可以转运,但是相对大部分的病人是不能转让的,或者有些病人他不适合这样做。这部分病人怎么办?所以我们想在每一个区域,比如说每个乡每个大的镇或者县里,起码在县里边要有很好的ICU,起到一个桥头堡的作用,让这部分病人在这个层级就有生命支持,为后续的治疗赢得时间和机会。
这样的话,各个区域发生的重点,第一时间点都可以得到救治。沈阳市四院冯伟主任在院里成立一个快速反应小组,不管院里哪个点,他们几分钟就会到场。
这个团队非常像特种部队,半年了已经抢救了60多个危重病人,他们医院仍在继续推动这个事儿。我们在2019武汉大会上宣布,要成立中国重症医学的专家委员会,与其它专家不一样,主要是通过这样的组织架构,使大家能够更有效的从事代表我们决策发展方向的一些前沿性的研究,为我们中国重症医学在国际上有发言权,提供一个平台。
至于提到有什么遗憾,我们中国人口占世界1/4,可在国际上的声音很小,我们有最多的重症医生,区域的发展仍然不平衡,重症病人早期很多没有得到救治。这种状洗和西方发达国家有特别大的区别,那些国家ICU也很多,但他没有那么多重病人,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重症病人,他前期干预做得好,人家不会等到变成中了重病号才去治。而在中国,恰恰是好多病人在前期没有得到一个合适的或者及时的医疗,所以中国才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ICU重症病人群。但我们从临床数据上来说,发言权非常差,因为大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数据链。这是我特别觉得遗憾的一件事情,各医院数据都不能共享。这是我们认识到的的痛点,也是我们要解决的方向。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想通过一些新的手段,逐步推行ICU信息化。
我个人经历太简单了,祖籍是河北昌黎,爷爷辈30年代中后期到的东北,那时还是满洲国。我爷爷学过做生意,也念过书,算盘打得特别好,菇吉林的东风镇落脚。当地有一个粮食仓库,爷爷帮助收账什么的,把弟弟妹妹都带过来了。生活虽不富裕,但是基本的生活还可以,孩子还都可以上学。山东姥爷是到吉林海龙县开了一个织布厂。不幸的是东北有瘟疫,我妈妈7岁就没父亲,靠姥姥一个小脚老太太拉扯,还有一个妹妹。她带着这两个孩子去农村拾穗,就是东北人种庄稼收割后的地上剩的东西,她捡回来解决温饱。国共战争开始后,爷爷失业,爸爸就失学了。怎么办?有个远房区亲属在沈阳,一家子就投奔过来了。1948年沈阳解放,战争结束,马上要恢复生产,年轻人工作还比较好找。
现在很多学生到我们这来,我首先问他,你喜不喜欢ICU,这极其重要。我说你不喜欢你做一段时间可以走。这工作一旦喜欢了,说实话,你不会觉得特别辛苦。如果你从事的工作你喜欢,这个工作又能使你过一种有层次的生活,我觉得这可以OK了。还漏了一个词:你最初喜欢上ICU有一个蛮大的因素,是眼看着要死的人,被你弄活了。
我老跟他们开玩笑,说你看就靠这点虚荣心活着,实际就是这种成就感,别人治不来的病人,别人觉得不行,我却行,这不多少有一点做专业人士的这种虚荣心是吧?多少还是有力量,有自豪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