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目光放在15世纪的欧洲大陆,那里刚刚经历起伟大思潮变革,文艺复兴的号角声洞穿了中世纪神学笼罩的暗影,将人文的思潮重新带到新的高度。商品经济飞速发展,而遗憾的是陆上丝绸之路,这条唯一连同东西方的商路却被一个古老的帝国死死扼制着。他们收取的赋税远远超过了欧洲商人们的预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想要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在浩瀚的海洋上开辟一条新的通往东方的道路。
人类的赞歌如果浓缩到了极致就会是“勇气”二字,当知识登上崭新的台阶,当造船技术已经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面对陆路封锁的现状,出海冒险探路就成为了必然。事实上最早承担起这兼具任务,把握住时代发展机遇的人并非强大的法国,也不是边陲岛国英国,而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他们将全国精力都押注在新航路上,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出海冒险家。而事实上,这份勇气也的确得到了回报。
15至16世纪,偏居欧洲一隅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如同两颗骤然划破夜空的流星,以其无畏的航海壮举开启了人类历史的大航海时代,并率先建立起横跨全球的海洋帝国。然而,它们的辉煌犹如昙花,绽放时绚丽夺目,凋零时却迅疾无声。明明把握住了先机,却并没能如后来的荷兰、英国一样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更近一步地拉大。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01
崛起于边缘
当欧洲的核心地区——意大利城邦沉浸于文艺复兴的奢华,法兰西和英格兰深陷百年战争的泥潭,神圣罗马帝国仍是一盘散沙时,位于欧陆西南边陲的伊比利亚半岛,却正在酝酿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静默革命。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长期处于伊斯兰文明影响下、刚刚完成“收复失地运动”的王国,以其独特的国家禀赋和历史际遇,成为了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
15世纪,欧洲对东方商品,尤其是香料、丝绸和瓷器的需求极为旺盛。传统的丝绸之路被意大利商人(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和阿拉伯中间商层层把控,价格高昂。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进一步加剧了商路的不稳定与成本。寻找一条直接通往“香料群岛”(东印度群岛)的海上通道,意味着能够打破垄断,获取近乎暴利的贸易收益。此外,对于黄金的渴求同样强烈,传说中的西非黄金产地是刺激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不断南下的直接诱因。
与当时欧洲许多封建王国不同,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完成统一后,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一个强大且稳定的中央政权有能力组织和资助耗资巨大、周期漫长的远洋探险。无论是葡萄牙的若昂一世、恩里克王子,还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双王”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他们都深刻理解海洋事业对于国家命运的战略意义,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这种“举国体制”是伊比利亚半岛能够率先突破地理局限的关键制度保障。
02
驾驭海洋的船与器是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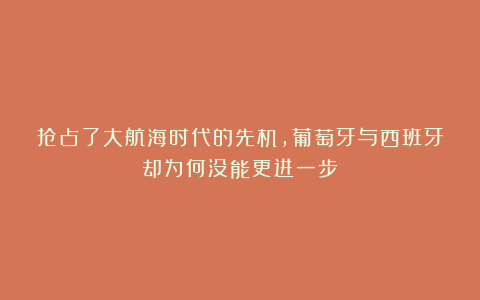
雄心需要技术的支撑方能化为现实。伊比利亚半岛的崛起,离不开一系列航海技术的融合与创新。葡萄牙人在船舶设计上取得了革命性突破。卡拉维尔帆船结合了欧洲的方帆与阿拉伯的三角帆,体型小巧,机动灵活,吃水浅,能够逆风航行,是进行海岸探索和未知海域侦察的理想工具。而体型更大、载货量更多的克拉克帆船,则成为后来远洋贸易和跨洋航行的主力。迪亚士绕过好望角、达·伽马抵达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所依靠的都是这些先进的船只。
伊比利亚的航海家们系统地吸收并发展了来自欧洲、阿拉伯乃至中国的航海知识。天文导航、象限仪、星盘的应用,使得船只在远离海岸的深海中也能大致确定纬度。虽然经度的精确测量在当时仍是难题,但通过“等纬度航行法”等实践技巧,航海家们依然能够进行有效的跨洋航行。此外,对信风与洋流规律的逐步掌握,为建立稳定的越洋航线奠定了基础。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短短半个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就完成了颠覆性的崛起,作为第一批冒险者,他们最早抢占了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大量财富就此涌入两国境内。
萄牙的迪亚士于1488年抵达非洲好望角;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印度卡利卡特,真正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海路;西班牙支持的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尽管他至死都认为那是印度);麦哲伦的船队(虽为西班牙服务,但其本人是葡萄牙人)在1519-1522年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这些发现立刻引发了西葡两国关于海外势力范围的激烈争端。在教皇的仲裁下,双方于1494年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这一史无前例的条约标志着伊比利亚双雄达到了其权力的巅峰,它们不仅是欧洲的强国,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的帝国。它们的旗帜从巴西沿岸到马六甲,从墨西哥高原到菲律宾群岛,宣告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然而盛极而衰的种子也恰恰在这一刻悄然埋下。
03
注定无缘的更进一步崛起
先说说葡萄牙,它的东方帝国是一个建立在战略据点和商站基础上的贸易网络。它通过武力控制关键海峡(如霍尔木兹)和港口(如果阿、马六甲),强迫当地商人与之进行贸易并试图垄断香料的供应。这种模式对于一个几乎谈不上战略纵深的欧洲边陲效果来说成本高昂,必然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护漫长的航线。最重要的是,葡萄牙本土几乎没有发展出任何能将殖民地原材料转化为高附加值商品的制造业。它只是一个巨大的中间商,将东方的香料贩运到欧洲赚取差价。一旦有新的、更有效率的竞争者出现,这种脆弱的垄断便不堪一击。
西班牙的问题则更深刻些,通过在中南美洲的残酷掠夺,巨量的黄金和白银涌入西班牙,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首先,它引发了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价格革命”,物价飞涨,而西班牙由于本土工业落后,需要大量从荷兰、英国、意大利进口制成品,导致白银迅速流出国库,白白肥了竞争对手,自己却产业凋敝。其次,轻而易举的财富腐蚀了社会的进取心,贵族们沉迷于消费和地产投资,而非风险性的工商业。白银没有成为工业资本的摇篮,反而成了扼杀本土经济的“资源诅咒”。
所以葡萄牙和西班牙,尽管抓住了先机,但由于种种原因注定没办法更上一层楼。他们掠夺来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新的、源源不断的财富链,而是成了拔地而起的庄园、贵族称号、或是漫天的地产挥霍。因此,当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展现出与西葡完全不同的海权模式时,它们也就必然会走向衰落。葡萄牙在东方的贸易垄断,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系统性的军事和商业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1588年被英国海军与风暴摧毁。
(图片来自于网络,侵权必删)
大航海时代不仅是地理发现的时代,更是制度创新的时代。伊比利亚半岛开启了全球化,但其内部制度却未能同步实现现代化。它们的管理模式仍然是封建的、王室专断的。荷兰和英国的成功关键在于其制度创新,它们创造了现代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所和中央银行体系。反观葡萄牙与西班牙,探险和贸易是“王室的生意”,利润归入王室金库,风险也由王室承担。当王室的财力因挥霍和战争而枯竭时,整个海外事业便随之萎缩。它们发现了新世界,却仍然用旧世界的规则去管理它,最终必然被淘汰。
真正的海权也许并不仅仅意味着拥有强大的舰队和遥远的殖民地。它更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依赖于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经济体系、一个能够激发社会活力的政治制度、一个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以及最为重要的、面向未来不断自我革新的战略眼光。伊比利亚双雄赢得了最初的赛跑,却未能适应随之而来的、更为复杂的马拉松。它们将世界的版图纳入怀中,却未能将现代性的基因植入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