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大脑衰老的关键驱动因素对于有效预防和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至关重要。在此,我们整合了人脑和生理数据以研究其潜在机制。对四个大型数据集(总计19,300名参与者)的功能性MRI分析显示,大脑网络不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变得不稳定,而且遵循非线性轨迹,从中年(40多岁)开始出现一致的大脑衰老时间“里程碑”。对代谢、血管和炎症生物标志物的比较表明,葡萄糖稳态失调是这些转变的驱动机制。大脑区域异质性衰老模式与基因表达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支持了这些发现,并特别指向了GLUT4(胰岛素依赖性葡萄糖转运蛋白)和APOE(脂质转运蛋白)。值得注意的是,MCT2(一种神经元而非胶质细胞的酮体转运蛋白)通过促进神经元独立于胰岛素的能量摄取,成为一个潜在的对抗因素。与这些结果一致,一项对101名参与者的干预研究显示,酮体在稳定大脑网络方面表现出强大的效果,这种效果在40至60岁之间最大化,这揭示了早期代谢干预的一个中年“关键窗口”。本文发表在PNAS杂志。
正文:
大脑衰老与多种退行性过程相关,包括葡萄糖代谢减退、萎缩、脑血管疾病以及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的沉积。然而,这些表现通常只有在衰老的后期阶段才能被检测到,此时已超过了可能进行有效干预的时间点。相比之下,通过功能性MRI(fMRI)和脑电图(EEG)识别的与年龄相关的神经系统变化可以提前数十年被检测到。因此,基于神经影像的生物标志物有潜力在疾病前驱期就识别机制并评估治疗效果,特别是如果它们足够敏感,能够在短时间内测量对干预的反应。
我们先前的研究表明,从40多岁后期开始,源自fMRI和EEG的大脑网络(一种衡量全脑神经连接或信号传递的指标)会经历显著的重组,其特征是不稳定和去同步化。这种重组与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中观察到的情况相似,这表明神经元胰岛素抵抗是驱动大脑代谢减退和认知衰退早期阶段的候选机制。在机制上,我们进一步表明,通过阻断胰岛素依赖性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4来实验性诱导神经元胰岛素抵抗,会导致放电动力学改变和轴突传导速度减慢,从而破坏神经元信号传递。最后,通过多尺度计算模型,我们确定了神经元中ATP可用性降低可导致钾离子梯度减小、轴突传导速度降低,从而在全脑尺度上导致大脑网络去同步化的机制通路。
虽然葡萄糖是大脑的主要燃料,但酮体提供了一种替代能源,可以被神经元在没有胰岛素的情况下代谢,因此可以绕过胰岛素抵抗。因为这种替代燃料可以被胰岛素抵抗的神经元利用,酮体已被提议作为治疗与年龄相关的代谢减退的潜在疗法。无论是通过禁食或低碳水/高脂肪饮食内源性产生,还是作为补充剂外源性给予,酮体已被证明可以改善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并恢复由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轴突传导速度缺陷。此外,即使在基线状态下,酮体也可能改善神经功能,为没有受胰岛素抵抗影响的神经元增强信号传递,并对20多岁和30多岁的年轻人的全脑产生作用。这种在酮症状态下代谢效率的提高,与对其他器官(如心脏)报道的效果一致。
在此,我们整合了我们关于生命周期大脑衰老轨迹、机制和干预的研究发现,特别关注区分早期的催化过程与后期的下游效应。首先,我们通过在四个独立的大规模fMRI数据集(总计19,300名受试者)中测试大脑网络失稳曲线的可重复性,确立了我们先前发现的非线性(S型)轨迹的稳健性。其次,一旦大脑衰老轨迹得到确认,我们探究了哪些生理变化与其非线性转变点(S型曲线的基点α和拐点I)同时发生。第三,我们探究了大脑衰老的空间异质性意味着哪些机制因素。通过识别哪些大脑区域比其他区域更早受到差异性影响,我们将与年龄相关的空间异质性与基因表达的异质性进行比较,以探究哪些机制与衰老模式一致或被其排除。生理生物标志物和基因表达分析均证实,神经元胰岛素抵抗是驱动大脑衰老轨迹的机制。基于这些结果,我们随后将酮体干预从衰老轨迹的基线(20至39岁)扩展到研究酮症对101名受试者在网络失稳开始(代谢应激期,40至59岁)及其拐点I(60至79岁)后大脑的影响。与我们先前的研究一样,酮体均经过禁食标准化、个体化按体重给药,并与葡萄糖进行热量匹配,以便比生酮饮食研究更精确地分离它们的差异化效应。我们的结果表明,有益效果在网络失稳最快的时期(40至59岁)达到最大化。这揭示了一个干预的关键窗口:一个神经元代谢应激期,之前是稳态,之后是代谢减退,在此期间,维持大脑最佳能量供应的调节机制在“断裂”之前先“弯曲”。
方法
生命周期神经影像数据集
为了研究生命周期趋势,我们利用了来自四个公开的大型神经影像数据集的静息态fMRI数据。它们是英国生物银行(UKB)、人类连接组计划衰老生命周期2.0数据集(HCP-A)、梅奥诊所衰老研究数据集和剑桥衰老与神经科学中心(Cam-CAN)数据集(81)。相应特征总结在表1中。
代谢数据集
为了研究急性给予D-βHB酮单酯和热量匹配的葡萄糖对大脑网络稳定性的影响,我们从年龄在21至79岁的健康成年人队列中收集了静息态fMRI数据(表1)。该研究已在ClinicalTrials.gov上注册为临床试验,并在麻省总医院(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监督下进行。此外,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IRB审查并批准了该方案,以确保符合机构政策。参与者通过广告从波士顿都会区招募。排除标准包括MRI禁忌症、神经或精神疾病、脑损伤史、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娱乐性药物使用、重度饮酒以及近期遵守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在获得知情同意后,参与者接受了体格检查并完成了标准化简易精神状态检查(SMMSE),以确认认知正常。随后,在另一个场合,经过一夜禁食后,参与者接受MRI扫描以建立基线,然后接受D-βHB酮单酯或葡萄糖,并在给药30分钟后再次进行MRI扫描,这个时间点先前已被确定为能在大脑中产生稳定的D-βHB和葡萄糖浓度。该程序在另一天(时间锁定)重复进行,参与者接受另一种代谢物,从而建立了一个受试者内实验设计。D-βHB酮单酯和葡萄糖均以液体形式在无标签容器中给予。D-βHB酮单酯溶液使用纯(R)-3-羟基丁基-(R)-3-羟基丁酸单酯(ΔG酮单酯,HVMN Inc)制备,剂量为每公斤体重395毫克,并用水稀释(体积比1:1.6)。葡萄糖溶液是橙味的葡萄糖耐量测试饮料(Fisher Scientific Inc),其热量含量与D-βHB酮单酯饮料相匹配。我们总共收集了104名受试者的数据。由于在扫描期间平均帧间位移超过0.5毫米,表示运动过度,有三名受试者被从所有分析中排除。纳入分析的受试者在三个年龄组内性别均衡(男/女,20至39岁:20/18,40至59岁:21/18,60至79岁:12/12)。
MRI采集
影像数据集使用超高场(7T)MRI获得,包括全脑血氧水平依赖(BOLD)[回波平面成像(EPI)]和T1加权结构[多回波磁化准备快速梯度回波(MEMPRAGE)]图像。BOLD图像使用一种为检测静息态网络而进行定量优化的方案捕获。该优化过程使用动态模型(BrainDancer;ALA Scientific Instruments)进行。BOLD采集的最终方案包括同时多层(SMS)切片加速因子为5,主相位编码方向上的R = 2加速(48条参考线),以及在线广义自校准部分并行采集(GRAPPA)图像重建。其他采集参数包括重复时间(TR)为802毫秒,回波时间(TE)为20毫秒,翻转角为33°,体素大小为2×2×1.5毫米,总采集时间为9分53秒(740个体积)。T1加权结构体积以1毫米各向同性体素大小和四个回波采集,使用的方案为TE1 = 1.61毫秒, TE2 = 3.47毫秒, TE3 = 5.33毫秒, TE4 = 7.19毫秒, TR = 2,530毫秒, 翻转角为7.0°, 主相位编码方向上的R = 2加速(32条参考线),以及在线GRAPPA图像重建,总体积采集时间为6分3秒。关于7T质子(1H)MRS方法的信息可在SI附录中找到。
图像预处理
UKB和HCP-A数据以已经预处理的格式获取。Mayo、Cam-CAN和代谢干预数据集使用fMRIprep进行预处理,并结合了来自SPM(SPM12, UCL)和nilearn python库的图像处理方法。T1加权解剖图像首先进行偏置场校正,然后去颅骨,并配准到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MNI)模板。从每个参与者获得的BOLD对比功能图像进行重对齐以校正头部运动,进行切片时间校正,并校正由磁场不均匀性引起的几何畸变。后一步通过将BOLD参考图像与强度反转的T1参考图像共配准来完成。这些步骤之后是与解剖图像的共配准和到MNI空间的配准。从白质和脑脊液体素中提取的平均信号从所有时间序列中回归去除,以减轻生理混淆,同时还有六个运动回归量以最小化与运动相关的伪影。最后,在进行后续针对特定指标的步骤之前,对数据应用了半高全宽为5毫米的空间平滑。
大脑网络不稳定性
大脑网络不稳定性是我们先前工作中使用的衡量功能性脑网络随时间持续性的标量指标(引文8, 11)。它量化了整个时间序列中连续时间窗口(或快照)之间功能连接性的相似性(SI附录,图S1)。值越大表示大脑网络越不稳定。为了计算大脑网络不稳定性,预处理后的数据经过了额外的处理步骤。首先,清洁的体素空间BOLD时间序列进行带通滤波(0.04至0.1赫兹),其中高通滤波器根据当前关于时间窗口大小的指南确定。接下来,滤波后的时间序列被划分到Seitzman功能性感兴趣区(ROI)图谱中,该图谱定义了13个功能性子网络。随后,划分后的时间序列被分箱成不重叠的时间窗口,每个窗口长度为24秒。对于每个快照,使用Ledoit–Wolf协方差估计器计算全对全有符号相关。之后,计算连续快照之间的差异矩阵,然后使用L2范数将每个快照对压缩成一个标量。最后,通过对每对快照进行平均,得到每次采集的一个标量,代表大脑网络不稳定性。在关注特定子网络的分析中,这些计算仅限于相应子网络内节点之间的相关性。
S 型曲线拟合
为了刻画脑网络不稳定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非线性变化趋势,我们将年龄 (x) 与脑网络不稳定性 (y) 的配对数据拟合为四参数 S 型函数:
其中
-
ymin:脑网络不稳定性的最小值;
-
R:极值差,即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
k:拐点处的增长速率;
-
I:拐点所在的年龄。
我们使用 scipy.optimize (文献 88) 进行拟合。为增强稳健性,共进行了 20 次不同初始条件的独立优化,并选取最佳拟合结果。随后采用 F-检验,将 S 型模型与线性模型及零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比较。
此外,我们在 S 型曲线上确定了两个标志性年龄点 α 和 β₁,分别对应非线性转折的起始和结束位置,这些点可由拟合参数计算:
其中ln(0.95/0.05) 为自然对数。
低频波动振幅。
低频波动振幅(ALFF)是静息态fMRI分析中使用的一个指标,用于根据BOLD信号评估区域性自发神经元活动。它涉及量化特定频率范围(通常为0.01至0.1赫兹)内的积分功率,这对应于源自神经元来源的波动。在时域中,这相当于信号的标准差。我们在HCP-A和UKB数据集中量化了ALFF。清洁且空间平滑的体素空间时间序列首先进行带通滤波(0.01至0.1赫兹),然后从得到的信号中计算标准差,以得出每个体素的ALFF。接下来,考虑到不同成像会话之间信号的任意缩放,我们用每个受试者大脑掩模内所有体素计算的平均ALFF值对每个ALFF进行归一化。因此,后续对与年龄相关效应的量化代表了相对的重组,而非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绝对增加或减少。为了量化这些与年龄相关的效应,我们首先用前述的Seitzman功能性ROI图谱对计算出的ALFF值进行划分,以降低计算成本。接下来,我们为每个ROI独立拟合线性回归模型,以ALFF为因变量,年龄为自变量。然后,我们提取与年龄对应的回归系数来量化效应大小。最后,对于每个ROI,我们用所有受试者的平均ALFF值除以计算出的效应大小。
与基因表达的空间相关性。
我们利用了来自艾伦人脑图谱的基因表达脑图谱,该图谱代表了大脑中体素水平上mRNA表达的对数值。我们最初筛选了这个数据集,只保留了参考文献90中报道的脑特异性基因集中的基因。这个筛选过程保留了原始16,826个基因中的87%。随后,我们选择了一个基因子集,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代表了三个机制组:代谢、血管和炎症机制(表2)。接下来,我们将选定的基因表达图谱划分到300个ROI中,以使其与源自ALFF的年龄效应统计图谱对齐。然后,我们通过选择与自动解剖标记图谱中概述的皮层结构重叠的区域来筛选皮层ROI。为了量化划分后的基因表达图谱与fMRI统计图谱之间的相似性,我们计算了斯皮尔曼相关性,同时根据当前标准考虑了空间自相关。我们利用neuromaps生成具有相似自相关结构的空间图谱。我们生成了1,000个这样的图谱,并为每个图谱计算了斯皮尔曼相关性,从而得到了所有置换中相关性值的分布。然后,将这些得到的相关性进行组合并用正态分布进行拟合,从中我们量化了观察到的基因表达图谱与fMRI统计脑图谱之间斯皮尔曼相关性的统计显著性。最后,为了校正多重比较,得到的P值进行了Bonferroni校正。
表2. 为研究与衰老效应的空间关联而考察的基因表达图谱列表
组间比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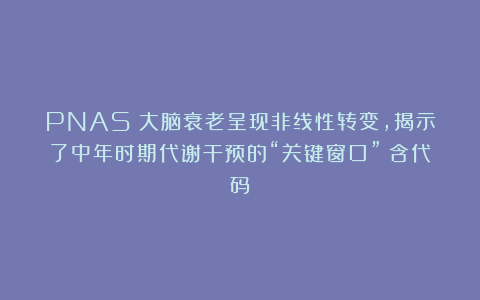
我们使用scipy.stats中的独立样本t检验,来比较已识别出的里程碑点附近的生物标志物。为评估代谢干预对大脑网络不稳定性的影响,我们利用受试者内实验设计,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在所有组间比较之前,我们使用基于四分位距(IQR)的方法移除了统计离群值,其中IQR计算为第三四分位数(Q3)与第一四分位数(Q1)之间的绝对差。超出Q3以上或Q1以下1.5倍IQR的数据点被舍弃。
结果
在以大脑网络不稳定的非线性生命周期趋势为特征的大脑衰老加速阶段,代谢变化占主导地位。
利用四个大规模神经影像数据集(HCP-A、英国生物银行[UKB]、梅奥诊所衰老研究和Cam-CAN),我们首先重现了我们先前测量到的大脑网络不稳定性的非线性趋势(SI附录,图S1),重点关注被确定为对衰老最敏感的三个子网络:听觉、视觉和扣带-岛盖网络(SI附录,图S2)(8)。然而,神经影像领域对于如何解析和分类静息态子网络缺乏神经生物学或方法论上的共识。因此,为了最大化普适性,我们还将网络不稳定性分析扩展到涵盖全脑网络。然后,我们通过关注时间分辨率最高(<1秒)的数据集(HCP-A和UKB)来最大化检测灵敏度。在这两个数据集中,全脑网络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表现出显著的不稳定(线性拟合,HCP-A: t = 8.25, P < 1E-10, N = 712;UKB数据集: t = 3.8, P = 0.0002, N = 16,435)。
为了量化观察到的非线性轨迹,我们用S型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对于HCP-A数据集,该模型与线性趋势相比提供了显著更好的拟合效果(F检验,F = 1.5, P < 1E-8)(图1A)。从S型模型的参数中,我们确定了三个关键的转变点或里程碑:α = 43.7岁,标志着不稳定的开始;I = 66.7岁,标志着最快不稳定的年龄(S型曲线的拐点);以及β₁ = 90.1岁,标志着不稳定达到平稳期的年龄。对于UKB数据集,S型模型与零模型相比产生了更优的拟合(F = 5.0, P < 1E-10);然而,与HCP-A不同,UKB与线性模型相比没有显示出显著的改进(F = 0.29, P = 1)。这可能是由于UKB的年龄范围较窄,其下限与不稳定期的开始相吻合(SI附录,图S3)。从UKB数据集拟合的S型参数中,得出的年龄里程碑为α = 46.9岁,I = 61.5岁,以及β₁ = 76.5岁。我们确认头部运动不是一个混淆变量(r = -0.02, P = 0.7)(SI附录,图S4)。
图1. 在以大脑网络不稳定的非线性生命周期趋势为特征的大脑衰老加速阶段,代谢变化占主导地位。
(A) HCP-A功能性神经影像数据集揭示了整个生命周期中大脑网络不稳定的S型趋势。利用曲线拟合得出里程碑年龄点α(不稳定开始)、I(最快不稳定年龄)和β₁(不稳定平稳期年龄)。
(B) 评估了代表代谢健康(HbA1c)、血管健康[收缩压(SysBP),舒张压(DiaBP)]和炎症状态[C-反应蛋白(CRP)血液水平]的生物标志物在根据其与α和I里程碑关系定义的年龄组中的平均变化(Nage<α = 111, Nα≤age<I = 281, NI≤age<β₁ = 227)。误差棒代表连续年龄组之间平均变化的95%置信区间,并按每个生物标志物在整个年龄范围内的方差进行归一化。α里程碑与HbA1c的增加关联最强(t = 4.8, P = 4E-6),而I里程碑与收缩压的增加关联最强(t = 5.7, P = 3E-8)。相比之下,指示炎症的血液CRP在任一里程碑附近均未显示显著变化。n.s.,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P ≤ 0.01; ***P ≤ 0.001; ****P ≤ 0.00001。
为了研究观察到的不稳定背后的驱动机制,我们进一步将分析范围缩小到HCP-A数据集,因为它具有更宽的年龄范围,并包含了针对三个候选机制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代谢(血液HbA1c)、血管(收缩压和舒张压)和炎症(血液C-反应蛋白)。然后,这些指标被用来确定是否有任何显著的生理变化与推断出的里程碑点相吻合。我们将样本根据年龄里程碑点划分为子组(年龄<α,α≤年龄<I,I≤年龄<β₁),年龄>β₁的组因样本量小而被省略。双样本t检验显示,α里程碑与HbA1c的显著增加关联最为一致(t = 4.8, P = 4E-6),伴随着收缩压不太一致的升高(t = 4.0, P = 0.0001)(图1B)。相比之下,I里程碑与显著的血管变化关联最为一致,其中收缩压表现出最大的效应量(t = 5.7, P = 3E-8),其次是HbA1c(t = 3.9, P = 0.0001),然后是舒张压(t = 2.6, P = 0.01)(图1B)。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一里程碑附近均未检测到血液C-反应蛋白水平的显著变化。这些发现表明,能量代谢的变化在脑网络不稳定的开始阶段占主导地位,而血管生物标志物的改变只有在不稳定的快速阶段后期才变得明显。
基因表达脑图谱突显了神经元胰岛素抵抗是大脑衰老的驱动因素,而神经元酮体转运则起到对抗作用。
为了进一步理解每个候选机制如何与S型生命周期轨迹相关,我们考虑了大脑衰老的空间异质性及其与区域基因表达模式的对应关系(图2A)。为了识别与年龄相关的大脑活动变化,我们首先测量了每个大脑的低频波动振幅(ALFF),这是一种基于体素的大脑活动测量方法(ALFF对每个个体大脑进行了归一化;因此,ALFF提供了大脑中相对而非绝对活动的度量)。利用这些ALFF值,我们接着计算了特定年龄的大脑活动图谱,随后将其与艾伦人脑图谱(Allen Human Brain Atlas)提供的机制性基因表达图谱进行比较。为了计算空间相似性,我们校正了空间自相关和多重比较。我们首先使用基因集富集分析,以无监督的方式解释了与衰老效应显著相关的基因。该分析突显了与突触功能和跨膜转运相关的通路(SI附录,图S7)。接下来,基于我们生命周期研究发现提示代谢失调为潜在驱动机制,我们测试了编码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 GLUT3, GLUT4)、酮体/乳酸转运蛋白(MCT1, MCT2)和APOE的六个基因。作为对照变量,我们分析了各包含六个基因的匹配集合,分别代表血管过程、炎症,以及一组与这三个候选机制均无已知关联的基因(表2)。在这24个基因中,只有三个与代谢相关的基因在UKB和HCP-A数据集中均与衰老模式表现出显著相关性(图2B)。相比之下,与血管功能、炎症和其他无关机制相关的对照基因在两个数据集中均未显示出可重复的相关性(SI附录,图S8),这表明观察到的大脑功能衰老模式特定于能量代谢过程。
图2. 基因表达脑图谱突显了神经元胰岛素抵抗是大脑衰老的驱动因素,而神经元酮体转运则起到对抗作用。
(A) 示意图说明了建立大脑功能衰老模式与基因表达分布之间相似性的方法。
(B) 色码方块显示了与年龄相关的ALFF变化模式与可能的大脑衰老关键机制相关的基因表达空间分布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性。每个显示的散点对应一个皮层功能感兴趣区。标签指示表达的蛋白质而非其基础基因。研究的机制包括细胞葡萄糖摄取(基因翻译为GLUT1, GLUT3, GLUT4)、酮体/乳酸摄取(MCT1, MCT2)、脂质转运(APOE)、血管功能(NOS1, ACE, ET-1, VEGFA, VEGFB, VEGFR1)、炎症(TNF, TNF受体1, IL-1β, IL-6, IL-23A, P2RX7),以及作为无关对照的管家基因和细胞骨架结构基因(ACTB, NF-L, GAPDH, PGK1, EEF1A1, RPL13A)。空间相关性在UKB和HCP-A数据集中均进行了计算。
(C) 散点图描绘了在UKB和HCP-A数据集中均可重复的基因的大脑衰老效应与基因表达(对数尺度)之间的关联。这些基因包括编码GLUT4、MCT2和APOE的基因。显示的功能数据来自UKB数据集。
三个代谢基因与年龄相关的大脑活动变化显著相关(α = 0.05,Bonferroni校正)。它们是神经元胰岛素依赖性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4(UKB: r = 0.28, P = 0.0003; HCP-A: r = 0.3, P = 0.0007),神经元乳酸/酮体转运蛋白MCT2(UKB: r = -0.37, P = 0.00003; HCP-A: r = -0.35, P = 0.002),以及脂质转运蛋白APOE(UKB: r = 0.35, P = 0.0003; HCP-A: r = 0.34, P = 0.001),其ε4等位基因显著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图2C)(45–47)。与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葡萄糖和酮体/乳酸转运蛋白GLUT1和MCT1,以及神经元胰岛素非依赖性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3缺乏显著相关性,进一步将机制锁定在与神经元、胰岛素和脂质相关的代谢上。与MCT2的负相关表明,这些衰老效应可能被神经元乳酸/酮体转运所缓解。
D-β-羟基丁酸通过绕过胰岛素抵抗,逆转大脑衰老加速阶段的大脑网络不稳定。
上述基因表达结果不仅显示大脑衰老效应与受损的GLUT4一致,还指出了通过MCT2的酮体摄取是一个潜在的缓解途径(图3A)。利用超高场(7T)fMRI,我们先前表明,急性给予个体化按体重给药的外源性酮单酯(下文称其水解产物D-β-羟基丁酸[D-βHB]),而非热量匹配的葡萄糖,可以稳定中年期前成人(<50岁)的大脑网络。在此,我们进行了相同的受试者内方案(代谢干预研究;图3B),但将其扩展到包括大脑衰老轨迹上的α(40至59岁)和I(60至79岁)转变点(表1)。为了对每个参与者在D-βHB和葡萄糖测试日之间的重测方差进行归一化(r = 0.44,SI附录,图S5),所有网络稳定性值均根据其当天推注前的禁食值进行了个体化基线校正。
图3. D-β-羟基丁酸通过绕过胰岛素抵抗,逆转大脑衰老加速阶段的大脑网络不稳定。
(A) 大脑的氧化供能途径。神经元可以利用葡萄糖、酮体或乳酸(通过星形胶质细胞)来获取能量,不同的转运蛋白促进其摄取。D-βHB是神经元易于代谢的主要酮体之一。D-βHB以及乳酸的摄取依赖于不依赖胰岛素信号的单羧酸转运蛋白(MCT)。
(B) 代谢干预数据集的实验设计。每个参与者被扫描两次,时间锁定以消除昼夜变异,D-βHB酮单酯按个体体重给药(395毫克/公斤)。然后,每个个体的葡萄糖剂量与他们的D-βHB酮单酯剂量进行热量匹配。
(C) 两种代谢干预(葡萄糖和D-βHB酮单酯)对大脑网络不稳定性的基线(禁食)减除效应。D-βHB在20至39岁(P = 0.01)和40至59岁(P = 0.00003)年龄组中稳定大脑网络,但在60至79岁年龄组中则不然(P = 0.4)。给予热量匹配的葡萄糖没有显著效果。
GLC:葡萄糖 vs. 禁食,D-βHB:D-βHB vs. 禁食,Δ:葡萄糖 vs. D-βHB。(D) 神经元代谢是“先弯曲”再“断裂”吗?功能网络不稳定的非线性阈值效应,假设是由胰岛素抵抗破坏神经元连接性所致。n.s.,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P ≤ 0.01; ***P ≤ 0.001; ****P ≤ 0.00001。
表1. 所用神经影像数据集摘要
我们的fMRI结果显示,对于20至39岁年龄组(α之前),与禁食相比,D-βHB显著稳定了大脑网络(t = -2.6, P = 0.01, N = 38)。对于40至59岁年龄组(α之后),酮单酯的效应量比最年轻组大84.62%(t = -4.8, P = 0.00003, N = 39)。相比之下,对于60至79岁年龄组(I),酮单酯的效应量不到最年轻组的一半(t = -0.8, P = 0.4, N = 24)(图3C)。同时,与我们先前在年轻成年人中的结果一致,与每个参与者的D-βHB剂量热量匹配的葡萄糖推注,在任何年龄组中均未显示出稳定效应(图3C),这表明结果特定于非GLUT4(因此非胰岛素)介导的通路。
最后,我们检查了可能以与能量利用无关的方式解释干预的年龄相关效应(关键窗口)的潜在混淆因素的证据:
头部运动:我们先前在HCP-A数据集中已证实,头部运动与大脑网络不稳定性不相关(r = -0.02, P = 0.7)(SI附录,图S4)。对于代谢干预研究数据集,我们同样确认了运动的变化与观察到的效应不相关(r = 0.09, P = 0.4)(SI附录,图S6),因此,不能解释最年长年龄组中效应量显著减小的现象。
方差:巴特利特检验表明,40至59岁和60至79岁年龄组的方差之间无显著差异(B = 1.0, P = 0.3),这表明最年长组中缺乏显著发现是由于平均效应较小,而非方差增加。
酮体剂量:给予D-βHB后,平均血液酮体水平为3.9±1.1 mmol/L,反映了高生理浓度,并且在40至59岁和60至79岁年龄组之间没有差异(t = -1.3, P = 0.2)。
血脑屏障:最后,为了测试最年长受试者中效应减弱是否可能反映了D-βHB穿过血脑屏障能力的变化,我们用7T质子(1H)磁共振波谱(MRS)扫描了我们干预研究队列的一个代表性子集(N = 41)。我们的结果确认,大脑内D-βHB的绝对或相对浓度均无显著的年龄相关差异(SI附录,图S9)。因此,我们的MRS结果表明,疗效的年龄相关变化并非源于大脑内酮体浓度的差异,而是源于酮体被代谢的程度。
讨论
在生物系统中,当维持稳态的控制机制受到超出其生理最佳范围的偏差挑战时,“应激”便会发生。虽然生物系统通常使用负反馈来补偿小的扰动,但细胞环境中超出控制系统补偿能力的更深层变化最终将破坏系统。胰岛素抵抗是一种直接影响细胞的扰动,它通过损害GLUT4介导的葡萄糖利用来实现。由于葡萄糖是脑细胞的主要能源,因此胰岛素抵抗会诱发代谢减退,这是一种代谢应激状态。我们先前通过药理学诱导的神经元胰岛素抵抗,利用神经元场电位记录表明,代谢应激会减慢轴突传导速度,而当给予神经元与我们代谢干预研究中参与者相同的D-βHB时,这种效应可以被逆转。这将导致长程去同步化,与观察到的随年龄增长的网络不稳定及其被D-βHB逆转的现象相一致。
在控制系统生理学中,S型曲线和崩溃的典型轨迹(图3D)与稳态调节的崩溃是一致的,即系统在最终断裂之前会先弯曲。在此,我们表明,源自fMRI的功能网络的不稳定并不遵循线性模式,而是表现出独特的里程碑,其中最早的转变点α与由HbA1c测量的系统性胰岛素抵抗的显著增加同时发生。此外,我们的基因表达分析表明,主要效应是神经元的(MCT2)而非胶质细胞的(GLUT1, MCT1),并且这种效应不仅是普遍的葡萄糖代谢减退,而是特异性地与胰岛素依赖性(GLUT4)而非胰岛素非依赖性(GLUT3)的神经元葡萄糖转运相关。我们进一步表明,大脑网络可以通过D-βHB恢复。这种燃料可以绕过胰岛素抵抗,在一个假定的关键窗口期内——此时神经元已开始受到代谢应激,但在持续的饥饿导致其不可逆转地受损(断裂点及随后的细胞死亡)之前。尽管最近一项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研究表明,老年人(包括轻度认知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神经元仍表现出酮体摄取,但在此阶段不可逆转的病理变化的开始可能会限制其治疗影响。与此一致,我们观察到D-βHB的效应在60至79岁范围内显著减弱。观察到的大脑衰老里程碑与其他研究中使用系统性多组学衰老标志物所识别的里程碑相对应,这为分子机制与我们的神经生物学结果之间提供了进一步的联系。在行为上,D-βHB效应的减弱与认知衰退开始加速的年龄以及临床症状通常显现的年龄相吻合。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神经影像分析都是在静息状态下测量网络稳定性的。因此,未来一个研究方向是,在具有更高能量需求的认知负荷下,能量限制是否可能在更年轻的年龄就已显现。
在机制上,神经元功能从“弯曲”到“断裂”的转变可以反映细胞死亡前各种病理变化,这些变化一旦超过临界阈值就变得不可逆转。稳定的蛋白质聚集体(如tau和α-突触核蛋白原纤维)的形成,可以启动自我延续的聚集循环,即使在初始触发因素被移除后仍然持续。来自氧化应激的线粒体DNA损伤通常被证明是无法修复的,导致细胞能量生产的永久性损害。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轴突变性超过某些点后变得不可逆转,尤其是在存在抑制性分子和胶质瘢痕的情况下。一些应激诱导的表观遗传修饰会永久“锁定”,改变基因表达模式,并可能维持炎症状态。此外,晚期细胞衰老代表了一个不归点,此时神经元不仅失去正常功能,还通过衰老相关分泌表型积极损害周围组织。然而,许多早期的病理变化如果能被及时识别和治疗,仍有可能是可逆的,这强调了在神经系统疾病中早期干预的至关重要性。
设计大脑衰老早期干预策略的一个关键概念性挑战是,该过程涉及许多相互作用和相互加强的机制。特别是,大脑衰老的临床研究已揭示了代谢、免疫和血管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表明相互关联的失调循环可以加速衰老过程。例如,线粒体功能障碍可以产生过多的活性氧,从而损害血管内皮并激活炎症通路。这种血管损伤因年龄相关的脑血流量减少而加剧,这损害了营养物质的输送和代谢废物的清除。由此产生的组织应激会触发小胶质细胞活化,并促进慢性低度炎症或“炎性衰老”,其特征是促炎细胞因子升高,进一步损害代谢和血管功能。血脑屏障功能障碍在这一相互作用中成为一个关键节点,因为它影响免疫细胞运输、代谢底物可用性和整体大脑稳态。这些变化因细胞衰老而进一步复杂化,细胞衰老通过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影响所有三个系统,促进持续的炎症和组织功能障碍。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创造了自我强化的循环,其中一个系统的功能障碍可以传播到其他系统,可能加速认知衰退并增加对与年龄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易感性。因此,从治疗的角度来看,确定大脑衰老在其最早阶段是代表一个许多独立机制同时汇聚导致失调的“完美风暴”,还是存在一个驱动机制,靶向该机制可能从而缓解其他机制的催化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的机制性发现在三种互补的研究设计中得到了重复,这一策略反映了补偿每种方法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需要:
首先,我们分析了一个在临床前大脑衰老轨迹上采样的大规模群体,其假设是衰老过程中较早出现的变化更可能是驱动机制,而较晚出现的变化更可能是下游效应。虽然具有启发性,但这种方法的一个明显警告是,在生命周期研究中最可能获得的微创且临床普遍的生理生物标志物(例如,HbA1c, BP, CRP)在机制上并非最敏感的。因此,我们展示这些效应的顺序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生物标志物的敏感性,而非损伤发生的机制顺序。为此,我们通过测试大脑活动模式与共定位基因表达之间的关系,为生理生物标志物的结果提供了额外的确认。然而,对基因表达分析的解释也值得几个重要考虑。鉴于量化人脑基因表达的挑战,我们利用了来自开放的艾伦人脑图谱的微阵列数据,该图谱独立于我们研究中使用的神经影像数据集。艾伦图谱来源于六名年龄在24至57岁、无已知神经病理的成年人,并呈现了平均数据,因此错过了可能在衰老后期发展的基因表达差异性变化。然而,该数据集的基线特征捕捉了易感性,使其更适合于识别大脑衰老早期阶段的驱动机制,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核心焦点。对于包含16,826个基因的完整数据集,我们选择了一个规模大幅缩小的目标子集,以便突出单个基因及其与特定机制的对应关系。这种细节水平通常是无监督方法无法实现的,后者会产生庞大的通路功能组(SI附录,图S7)。尽管如此,突显了突触过程的基因集富集分析,可以被认为与我们的监督分析是一致的。
鉴于突触是活动依赖性神经元GLUT4转位的主要位点,表达与突触密度相关的基因很可能通过这种关系而间接被牵涉进来。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基因表达水平与其相应蛋白质产物的丰度密切相关,但由于转录后和翻译后机制,在同一组织内可能会出现显著偏差。未来系统评估这些偏差或提供更直接的人脑蛋白质组测量的努力,可以增强通过这些分析获得的机制性见解。为进一步支持生理生物标志物和基因表达的结果,我们证明了绕过神经元胰岛素抵抗的急性干预能够逆转衰老效应。在这种情况下,酮症在几分钟内被诱导是分离机制的关键。已知营养性酮症会系统性地影响所有三个候选机制:代谢、免疫和血管。然而,我们先前已表明,在我们研究中测量的时间尺度(推注后30至60分钟),急性干预会影响神经元信号传递,从而影响神经元连接性和网络稳定性,但不会影响诸如肌醇等神经炎症的生物标志物,也不会仅仅反映可能混淆fMRI的血液动力学变化。最后一个注意事项涉及神经元胰岛素抵抗作为代谢应激驱动机制的特异性。虽然我们的结果表明代谢变化发生在血管和免疫变化之前,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神经元胰岛素抵抗本身可能是由更早的与年龄相关的神经元线粒体功能变化引起的——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大多数关于痴呆的神经影像研究都是在出现疾病最初体征和症状的个体上进行的。然而,当探究疾病病因时,关注已经受损的人群可能不是最具战略性的选择,原因有二。首先,当患者出现症状时,疾病已经进展到足以难以区分哪些病理生理特征是驱动因素,哪些是次要或基于相互作用的效应。其次,由于无法利用葡萄糖而处于代谢应激状态的神经元,可能仍有能力利用酮体作为替代能源。如果是这样,任何试图用酮体恢复或正常化神经元功能的尝试,只有在目标神经元仍然存活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因此,出于科学和临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在此的主要焦点是临床前生物标志物,在此期间可以检测到神经元代谢应C激,但在症状出现之前。通过比较这些推定的生物标志物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神经能量学,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驱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非线性阈值效应的潜在调节过程的崩溃,并利用这种理解来确定最具战略性的干预时期。我们的结果激励了未来更大规模和纵向的研究方法,以测试在代谢关键窗口期靶向神经元胰岛素抵抗的治疗是否可以延缓或预防后期大脑变化(包括葡萄糖代谢减退、萎缩、脑血管疾病、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沉积以及认知衰退)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