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润九
从我记事的时候,家里面就穷,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都揭不开锅,姊们6个,还有我爷,一家老小9口,生活担子就担在父亲的肩上。我爷在我的记忆中,身体刚强,冬天不戴帽子,光着头里面穿个老布衫子,外面套个穿了几年的棉袄,袖口黑得发亮,腰里襟条腰带,那时候我10岁左右,爷80多岁,我在家最碎,爷最倩我,爷的枕头盒子,黑得发亮,爷头枕的那块,磨得见了木头,那黑色,不知道是爷炕沿上平时用火盆烧水熬茶熏的,还是年时已久包浆的。爷最爱的就是平时喝茶的泥性壶(宜兴壶),那是我大在四川放蜂的时候,给爷带回来的,十几年了爱不释手。
在物质匮乏的70年代,过年是大人最愁的事,吃油吃菜都是生产队按人头分的,谁家劳力多,挣的工分多,分的就多,我们姊们几个就是,大哥,二哥,大姐能算个半个劳力,我,二姐,三哥,都在念小学,三个人只能分点口粮,分不到油和菜。秋季,父亲就摘渠沿上,路边上,涝池旁的蓖麻,在家里的铁锅里,蒸炒,泡制,沉淀,过滤,煎熬,把青石门墩绑在2根长洋槐木檩条上,物理压榨,再放进锅里火煎,多道工序完成,就让家人吃上香香的蓖麻油。
父亲,为了能够养活一家人,就在学校西边,那块1亩3分地的自留地,种了白菜,地少人多,让地能多产点粮和菜,父亲让1亩3分地,实现1年收3料庄稼,麦子割了,点玉米,玉米发黄,在玉米行里套白菜,欻掉玉米棒子以下的老叶子,打掉玉米顶,能使白菜得到光合作用,玉米早成熟,每窝白菜都要基肥一把蓖麻油渣。白露时节,在白菜行里勾种小麦,霜降就开始用棉花杆的皮捆白菜,白菜就卷心快,长得实在,也让小麦多些光合作用,分孽多,产量高。
那时候,我10岁不到,到了冬季,白菜成熟的时候,父亲就在西边2台高的地坪上,搭个玉米杆蓭子,里层蒙一层油纸,油纸上,散一扎厚的麦秸草,外面靠一圈玉米杆,用棉花杆皮拧的绳,一圈绑紧,固定好床铺,最下面,还是一尺厚的玉米杆,上面一层油纸,油纸上铺两扎厚的麦秸草,再上面就是用蛇皮袋子衲的大花包一铺,一个冬季暖和的蓭子就好了。
冬天的早上,天不亮,上学的娃娃,一路上说着唱着就在学校的路上走开了,三五成群,有的手提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肩上斜挎用旧衣服缝制的书包,书包带有点长,几本书本在书包里,上下打着我的屁股,妈妈衲的棉窝窝,在硬棒棒的地上,噌噌的响,二姐右手拉着我的手,生怕我迟到了似的,二姐左手上馍袋子里两个玉米面馍馍,在袋子里来回磕碰着,白菜上一层白白的霜,地冻得硬棒棒的,东边麻麻亮的天空,镶着几颗微微闪烁的星,
每年腊月23,赶城里的3、7会,是我最高兴的事,父亲先一天,带着我们姊们们,刨白菜,削根,摘黄叶,捆绑收拾好的白菜,即使掉下来一块白菜边股(白菜帮子),父亲都要哥哥们想办法夹到白菜身上,收拾好,就开始装车,架子车底铺上油纸,垫上草帘,下面放大的实在的,中间小的填空,最上面一层把最好的放上,这样子,到集会上能拉住买主,最外层,盖上被子,角角缝缝塞上麦秸草,生怕冻了,裹上油纸,绑上几道绳,车轮胎气打饱。一切就绪,就等23早上,天不亮进城。
天不亮,妈就熬好了玉米糁饭,热好了黄菜,摊了些热玉米面巴巴,在爷的柴火盆上烤了一布袋油花馍,牢牢的绑在车辕的蛇皮袋里,生怕一路馍布袋,断了系系,饿了我们。
我早早起来,穿上冬季黑撅勾子棉袄,套了个黄色军用袄罩,蹬上棉裤,穿上大姐用旧毛线织的袜子,勒紧窝窝鞋带,戴上上学时的裢裢帽,就在白菜车旁边转,怕不撕赶我。
70年代的冬天,真是滴水成冰的天,塑料纸上,落下了一指厚霜,塑料纸里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凌,手按上去,可嚓可嚓响。西北风,抽得树枝呜呜的响,带了口哨似的,天上零星的挂着几颗星,一闪一闪,一轮残月,落在了后院那棵老槐树底下,我在院子里的走动,惊吓了槐树上的老鸦,扑拉扑拉的朝北边后墙外面飞去。
作者简介:高润九,70年,生于大荔县石槽乡三教村,石槽初中读完,步入社会,种庄稼十余载,勉强养家糊口,不得已出门打工,漂泊异乡至今,偶看《洛河文苑》。
相关链接(点击蓝字直接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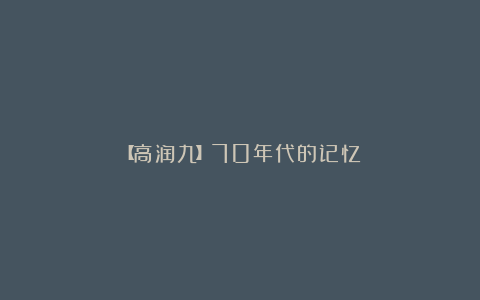
【关宁】 汲华山之灵气,纳黄河之膏泽——这块土地中,走出了人类的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