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个月,指挥家丹尼尔·加蒂就要在德累斯顿走马上任,成为那支历史长达 475 年之久的乐团的首席指挥。
对于以演绎德意志音乐而闻名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而言,加蒂并不是第一位来自亚平宁半岛的艺术领袖。时间闪回二十多年以前的世纪之交,正是当年担任乐团首席指挥的意大利人朱塞佩·西诺波利,邀请加蒂完成了在这里的首秀。
人们常说,60 岁才是指挥家黄金年龄的开始。从亚平宁半岛出发的加蒂,职业生涯的前 40 年已将欧洲的古典音乐重镇遍历。正如他的许多伟大前辈们那样,加蒂的下一站,如今也来到了德意志。
壹
『
I think I have the honor probably to say that the Italian conducting tradition is equally important in the worldwide like the German tradition or the German school.
因为歌剧这一伟岸的存在,人们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将「意大利指挥」与「歌剧指挥」划上等号。「这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加蒂直率地说。更准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没有哪位意大利指挥不擅长那些深植于自己基因中的歌剧,但真正的大师们从来都不局限于此。
加蒂坦言,20 世纪之前的意大利,在交响乐方面的积淀,的确不如德奥、法国和俄国那般深厚。但要说到指挥,亚平宁并不逊于任何一片土地。
NCPA Magazine:自 20 世纪以来,意大利在指挥领域大师辈出,而且保留曲目都不只局限于意大利一地。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加蒂:意大利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指挥传统。它的起点甚至早于托斯卡尼尼,可以追溯到安杰罗·玛利亚尼大师。他是我们的第一位重要指挥,主要活跃在 19 世纪下半叶。玛利亚尼最初与威尔第私交甚笃,还指挥过他的歌剧首演。但他们后来分道扬镳了——因为他首次把瓦格纳的作品带到了意大利演出,成为了瓦格纳音乐的传播者。
托斯卡尼尼是第一位同时胜任歌剧和交响乐的意大利指挥。他曾在斯卡拉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担任首席指挥,但纽约爱乐乐团和 NBC 交响乐团这两支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在他的事业中同样举足轻重。托斯卡尼尼擅长的曲目范围极广,数量极多,在音乐演绎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指挥的贝多芬、理查·施特劳斯、瓦格纳和勃拉姆斯作品,至今都是里程碑式的演绎。
从托斯卡尼尼开始,来自意大利的指挥大师相继登上了最顶尖的舞台:卡洛·玛丽亚·朱利尼、朱塞佩·西诺波利、克劳迪奥·阿巴多、里卡尔多·穆蒂、里卡尔多·夏伊……有趣的是,我们之间总是大约相隔 10 至 15 年。克劳迪奥(阿巴多)是 1933 年,穆蒂是 1941 年,夏伊是 1953 年,而我自己是 1961 年出生。我一直都在尝试追寻和跟随这些音乐巨人们的足迹。
NCPA Magazine:你在米兰出生,曾就读于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并且在职业生涯初期就担任了罗马圣切契利亚交响乐团的艺术指导。意大利的血统、文化和教育,为你的指挥艺术带来了什么?
加蒂:我在米兰的音乐学院学习了 14 年,除此之外我没有在其他地方上过学,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大师班。我必须要说,至今我仍然感到十分幸运,当时遇到了非常出色的教授,既教会了我技术,也培养了我对音乐的认识。在意大利,学音乐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除非完成十年的作曲和声学习,否则你不可能被录取进入指挥专业。我从 18 岁开始在乐队里指挥,因此,当我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几乎已经养成了职业的工作习惯。
NCPA Magazine:你所在的艺术传统和你本人,如何定义「什么是一个好指挥」?
加蒂:(指着自己的脑门)指挥最重要的是这里。
每年夏天,我都在意大利锡耶纳的齐基雅纳音乐学院教授指挥。通常我会在哪里待上两到三周,我的大师班面向全世界的学生。指挥家们要学习手势,这没错。但只要在座的你足够聪明,我可以在五分钟内就把你教会。当你知道第一、二、三、四拍(的手势),其实就可以去乐团面前指挥了。但问题也会随之而来。在我看来,「技术」并不是指挥的关键。
指挥家必须首先是一名诠释者,早早地做好对于作品的演奏法、色彩、内在张力等方面的规划。我每次都会告诉学生们,当你为乐谱签上自己的名字,当你能想象这首曲子在你自己听来是什么样时,就忘掉其他的演奏吧。比如贝多芬著名的《第五交响曲》,它伴随着我们长大,一想到作品开始的「砰砰砰砰」,我们好像就能反应出一种习惯性的速度。但事实上,它也许可以快一些,或者慢一些——这取决于你想通过音乐表达什么。所谓「诠释」, 就是把你的乐谱带给听众,而不是要求听众过来,再重新听一遍你已经烂熟于心的乐谱。
贰
『
Sometimes people consider Italian opera like a series of arias, with the conductor and the orchestra playing accompaniment like the piano. It’s absolutely not like this for me.
几年前一次与歌剧导演兼指挥家丹尼尔·阿巴多同台的活动上,加蒂在讲解威尔第的歌剧《弄臣》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之一《女人善变》时,重点关注的也并不是它的歌词或音乐本身。他试图探寻一个问题:威尔第为什么要把这支男高音(注:歌剧的主人公利戈莱托是男中音)的咏叹调,安排在歌剧结尾戏剧性最突出的时刻?
加蒂的答案是:这不仅是一支男高音展示技巧的华丽唱段,更是利戈莱托最终被曼图瓦公爵彻底击败的标志,在戏剧的结构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利戈莱托原本确信袋子里装着的尸体就是公爵,却在下个时刻听到了远远传来公爵演唱这支咏叹调的歌声。这让他目瞪口呆,也是对他而言致命的伤害。」加蒂如是向在场的观众解释道,「因此,这支咏叹调必须要在那个精确的时间点上来演唱。」
NCPA Magazine:如今的你在歌剧和交响乐这两个领域都有突出建树,它们各自在你的事业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加蒂:我现在的日程表上,交响乐曲目大约占 70%,歌剧大约占 30%,我每年的歌剧演出一般不会超过 3 部,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因为我们需要很多时间来排练。在有限的制作之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戏剧性更强的作品。我会在演出季开始前选择剧目,比如在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剧院(加蒂目前在这里担任首席指挥),我会和剧院在确定剧目之后,再来寻找合适的导演和演员,将项目搭建起来。
NCPA Magazine:你会不会把歌剧的思维带到交响乐之中?或者是把演出交响乐曲目的经验带到歌剧之中?
加蒂:这并不容易回答。有些音乐属于完美的结构性作品,比如赋格,你不能在音乐中加入任何个人的观点,因为它只是纯粹的数学。但在交响曲中,比如奏鸣曲式,你会看到第一主题、第二主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对话。这就像是歌剧中的两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奏鸣曲式本身就有一种戏剧的质感。当你拥有了第一主题,很快就会过渡到另一种习惯之中,随后就拥有了个性完全不同的第二个频道。
有时,人们认为意大利歌剧就是一连串的咏叹调,指挥和乐队(在其中的角色)只是像钢琴一样伴奏。对我来说,事情绝对不是如此。指挥应该是歌剧是关键所在,就像是音乐的导演。我会根据我认为有价值的内容,在歌剧中强调相应的观念。(与伴奏相比)我会向前再迈出一步,如果要演奏一支咏叹调,我会关注这首咏叹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唱词、情感、心理,这样我就可以让乐团做好相应的准备,来为演唱提供最好的支持。
NCPA Magazine:你不仅擅长意大利歌剧,而且是少数几位曾登台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意大利指挥家之一。你如何理解瓦格纳和威尔第歌剧的异同?
加蒂:我对瓦格纳和威尔第抱有同样的崇敬之情,他们都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歌剧作曲家。但他们的音乐非常不同。瓦格纳吸引我的不仅仅是音乐之美,还有歌剧中的躁狂的气质,这是一种抽象的美。
威尔第则是具体的——他是一位莎士比亚式的歌剧作曲家,尤其擅长挖掘人类的心理。他的歌剧绝不是咏叹调的集合,而是要研究所有角色、乃至全人类的痛苦。在他的全部 27 部歌剧中,你总能找到这三个主题或其中的两个:嫉妒,父子关系,以及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平衡。从《纳布科》(注:威尔第的悲剧代表作)到《法斯塔夫》(注:威尔第的喜剧代表作)都是如此,三个元素从不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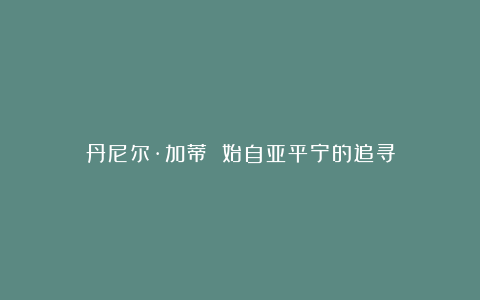
威尔第有时甚至会让观众感到非常不舒服。当身临其境之时,你很可能会忘记聆听那些优美的旋律,而是陷入对戏剧的思考。你会看到自己的生活投射在其中,因为一切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人们因为嫉妒而互相残杀,家庭成员之间矛盾深重……尽管我们已经来到 21 世纪乃至日后的 22 世纪,但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与当年是完全一样的。
叁
『
Sometimes I would like to combine Mendelssohn and Brahms in a concert, because both Mendelssohn 14 years before and Brahms were the same.
接到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打来电话的那一刻,加蒂正在诊所接受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鼻子里还插着取样的小棍。事实上,三天前乐团总经理就已经和他通过气,「丹尼尔,下个星期一下午的 5 点或 6 点,我们可能会给你打个电话。」但偏偏就在这个周末,加蒂一不小心得了感冒。虽然症状很轻,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决定去诊所做个检测。如此巧合的一幕,便这样发生了。
回忆起那段充满戏剧性的小插曲,加蒂毫不掩饰脸上的笑容,「那还是个视频电话!我只能先说,『对不起,我现在可能没法说话,因为我的鼻子里还插着小棍。』然后我就听到对方说,『我们选举决定请你来担任我们的首席指挥』。」来不及想太多,加蒂先回复了一句「Okay!」,随后补充,「两小时后我再打给你!」
邀约送抵的瞬间虽然有些意外,但这段缘分早已埋下草蛇灰线。加蒂第一次站上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的指挥台,是在 2000 年 2 月。那是一场音乐会。自那以后,无论交响乐还是歌剧,他与这支传奇乐团碰撞出的艺术火花不胜枚举。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里,加蒂不仅在欧洲各地不断出任重要的音乐总监或首席指挥职务,更在拜罗伊特音乐节、柏林爱乐乐团这样的音乐重地积累了难得的口碑。
NCPA Magazine:你即将出任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对于自己的新任期,你有哪些规划?
加蒂:我们的第一份合同将会持续 6 年,目前已经推进了一些项目。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是世界上最好的三支交响乐团之一,拥有最伟大的历史传统。这是玛利亚·冯·韦伯的乐团,也是理查德·瓦格纳的乐团,尤其是在演绎德国曲目时仿佛有种魔力。这也会激励我对这些曲目爱得更深,演出得更多。而在传承这些曲目和保存乐团遗产的同时,我也希望用法国和俄国等音乐来拓展乐团的曲目,因为乐团的演奏同样需要广度。
NCPA Magazine:德国交响乐作品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加蒂:于我而言,德国的传统意味着最伟大的音乐,我从未对它们感到过厌烦,也从未停止过学习。贝多芬是一位冒险家和探索者,浪漫主义时期的罗伯特·舒曼也是如此,他们都试图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勃拉姆斯则是一位「追随者(epigone)」。很多时候人们喜欢将舒曼和勃拉姆斯放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彼此认识,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这固然很有趣。但舒曼的音乐会有时让你感到震惊,因为你能从中听到过去从没有人尝试过的声音。勃拉姆斯的确是德国音乐的灵魂人物,但他并未打开新的方向,而更多是作为崇高的德国浪漫主义音乐道路的里程碑式角色。
我们需要等到马勒和第二维也纳乐派的时代,才又有了这种音乐上具有冒险精神的探索。这也是为什么有时我喜欢把门德尔松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编排在一场音乐会上来演出,因为门德尔松与小他 14 岁的勃拉姆斯(的音乐本质)是一样的。他是一位莫扎特式的作曲家,非常精致和优雅。舒曼是一个疯狂的人,但他在我眼中非常有魅力。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更想和舒曼一起碰杯。当然,我也很敬重门德尔松!
NCPA Magazine:你曾在欧洲各地担任音乐总监或首席指挥,也一直在客座指挥所有的主流交响乐团。与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乐团接触,体验有哪些不同?
加蒂:如你所说,我一直在不同的国家担任职务。与五六十年前不同,今天的音乐更加全球化。人们也在不断旅行,你会发现法国人在德国乐团里演奏,意大利人在英国乐团里演奏。但大家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作为指挥的你如何排练?乐团的反应速度有多快?
如果你去伦敦,常常只需要在两天半的时间里排练三次,就能准备好一套曲目。伦敦本就是一座速度飞快的城市,当你带着乐团过第一遍曲目时,音乐家们就已经准备好了 70%。因此只需要三次排练,音乐会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而在意大利,你很可能需要更多的排练。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水平低,而是我们希望抵达音乐的更深处,所以需要更多时间。德国的情况也有相似性,第一次排练更多只是熟悉作品和音乐家,但从第二天开始,音乐就会达到极佳的规格。
作为指挥,我们必须善待乐团并不断学习。当你与德国乐团或英国乐团合作时,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这(掌握这些)只是时间和经验的问题。
NCPA Magazine:现在你在马勒室内乐团(Mahler Chamber Orchestra)和莫扎特管弦乐团(Orchestra Mozart)同时任职,它们都是指挥大师阿巴多留下的重要音乐遗产。这是巧合吗?
加蒂:就莫扎特管弦乐团而言,这的确是个巧合,但可能也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尽管我和克劳迪奥没有见过几次面,但我们彼此非常熟悉。后来我得知,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病得很重的时候,曾经对音乐家们说,「我无法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了,请你们去找丹尼尔吧,让丹尼尔接替我,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你能想象,我是多么感动。
不过,马勒室内乐团就谈不上巧合了。我还记得那是 2010 年,我指挥马勒室内乐团演出了三场阿尔班·贝尔格的歌剧《露露》。那次演出结束后,乐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首席指挥。但因为我那时在欧洲已经有了其他职位,所以没法再接受这个邀请。但是后来我答应来做艺术指导,这更像是一个友情身份,非常自由。但如果乐团需要我,我就在那里。
肆
『
Sometimes I like to buy new scores of a piece I’ve conducted 50 times, because I don’t want to see my old sign. When I open a new book, it sounds new for me, and I re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to be fresh.
如果不是特意关注,加蒂的足迹总是并不显眼,更游离于媒体的聚光灯之外。但他无疑已经像是自己口中希望「追寻」的托斯卡尼尼、朱里尼和阿巴多等等前辈们那样,能够同时在歌剧和交响乐的世界,以及在从意大利到法兰西、再到德意志的土壤中游刃有余。
艺术管理人扬·赖斯曾与许多大指挥家共事,也是加蒂在阿姆斯特丹任职时的搭档。在他看来,加蒂与伯恩斯坦和捷杰耶夫是同道中人。「他们的指挥都有冒险精神,因为他们敢于超越乐谱。」赖斯写道。
这两年准备与莫扎特管弦乐团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音乐会时,加蒂买了一套全新的总谱,尽管这些作品他早已烂熟于心,并且在世界各地演出过数不清的场次——事实上,这恰恰是他这样做的理由。「有时我会为我演奏过 50 遍的乐曲购买新乐谱,因为不想看到自己写的旧标记。当我打开一本新的乐谱时,它的音乐也像是全新的。我会从头开始(案头工作),这样一切对我来说就都是新鲜的了。」加蒂如是说。
NCPA Magazine:你在演绎作品时是如何与乐谱互动的?
加蒂:乐谱就像是作曲家的笼子(Cage),因为作曲家使用的是符号,而不是文字。只有疯狂的古斯塔夫·马勒使用了比较多的文字,几乎每页都有写给指挥的注释,「请这样做,请那样做……」但其他作曲家只是会在强音、弱音、渐弱、渐强的位置做个记号,然后就结束了。
我对深入研读乐谱非常感兴趣。但有时我在聆听别的诠释时,却发现它并不完全遵循乐谱。我的问题是:这究竟是作曲家的想法,还是诠释者的想法超越了作曲家?其实,有时候我也喜欢一些与乐谱本身想去甚远的诠释。我习惯于不仅仅以垂直或水平的方式来阅读音符,而是更多地关心演奏法,比如连线、附点、力度记号等等细节。透过这些,我需要把乐谱当成一种类型来研究。分析乐谱意味着要了解作曲家是如何构建它的,使用了什么样的骨架、我们此刻又在那个部分。这个过程很容易出错,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要准备充分。如果做出错误的分析,并且据此来指挥的话,音乐就是不可靠的了,就像是说话的口音不对一样。最终应该达到的境界,是在技术上主导乐谱(to dominate the score technically)。而一旦做到了这点,它就会融入你的血液。
NCPA Magazine:乐谱最终表达出的是什么呢?
加蒂:写在谱面上的内容是一个没有被讲述的故事,就像是一个谜。当我不断往深处挖掘,时而见到它对我说「不要太快的快板」,时而又说「有活力的行板」。但这里面并没有具体节拍器数字来告诉我最好的速度,而是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敲打着我的内心。我可能会在一个乐章里使用两到三种不同的节拍器,比如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也许乐章开始的部分稍微慢一些,后面则会更流畅一些。完成了所有这些分析过后,那种感觉就像是作曲家第一次把乐谱交给了我。我好像听到了他对我说:「请为我指挥这份乐谱。」而我必须从这封写给我的信中,找到它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