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雅克·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中是同一战壕的同志和战友,他们为自由和民主并肩作战。然而不久后,丹东被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法治国家处死,理由是丹东触犯了他们浴血奋战得来的自由民主新伦理。
这是真的吗?听起来太荒谬了,难道丹东是自己的掘墓人?他故意给自己挖坑吗?他明明也崇尚人民公意的自由,怎么最终又被代表这种自由的革命法庭处死了呢?是丹东变了还是自由变了?
事情的起因是革命后的丹东,不是与同伙发犬儒主义的牢骚,就是经常与妓女调情,说下流话,一个主张高尚的、绝对道德的新国家不容许这些行为存在。
这个新国家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们用战争得来的,是人民的国家,是自由和民主的载体。罗伯斯庇尔认为这个自由以人民道德的公意为准则,法律保障的是人民公意的自由,不是个人生活想象的自由。
问题是,这个人民与个人是什么关系呢?人民不应该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吗?但人民公意肯定不是个体意志的简单相加,那么,个体的价值偏好千差万别,万一与人民公意相冲突,岂不就得放弃自我意志?自我意志侵犯他人权利还好,自我意志无碍于他人,难道也得自我牺牲?这其中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
估计丹东也隐约感到了其中的诡异,有一天他在夕阳如血的光辉中突然说: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流的血太多了!
从丹东后来的言辞来看,这个流血不仅仅指为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曾经流过的血,也指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后人民仍然在流的血,因为他说人民公意的自由专吃自己的孩子,是需要活人献祭的罗马食神。因此,他开始散布反自由反民主言论。
丹东的思想转变与一位名叫玛丽昂的妓女有关。“人民”的道德洁白无瑕,从这个角度,玛丽昂的行为道德败坏,她是社会渣滓。玛丽昂的母亲不高兴了,玛丽昂自己也认为,根据自己的感觉偏好去生活,本身就是道德行为。
于是,作为自由民主新伦理的“人民”公意道德与个体的生存感觉偏好杠上了,前者有消灭后者的权力和自由,罗伯斯庇尔就是这个权力和自由的化身,他要建立的是穿着华丽丽的道德长袍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人民公意的体现,人民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甚至拉什么都不能随随便便;
而丹东们要建立的却是体现个体肉身曲线之美和丑的国家,这个国家允许粗俗、文雅,有教养和没教养同在,每个人只要不损害别人,就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生活,不关国家什么事,总之,身体享乐本身没有罪恶可言。
罗翔也曾说:很多人爱的是抽象的人,具体的人都是充满汗臭味的。
众所周知,人民公意的道德是有强制机关来保障的,谁要跟它作对,就把谁扔到监狱里去。
丹东觉得太可怕了,当抽象共同体(人民)的公意道德的自由高于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个体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这就是专制,是道德专制,这样,暴政也就不可避免了,而强制机关比如法庭便成了暴政的工具。
原来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因为道德观的不同导致各自对自由的理解不同,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国家观念。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不同思想竟然来自相同的基础:他们都是从单纯的生存感觉出发,都是为解决人的身体痛苦而行动。
然而,在克服痛苦的方法上,他们分道扬镳了。
作为享乐道德的捍卫者,丹东以为,身体偶在的受损或受挫无须抱怨身体,顺其自然地享乐,让生存处于自然循环的节律,这样就不会走到夸张痛苦,进而呼吁用外在的公义来解决这个痛苦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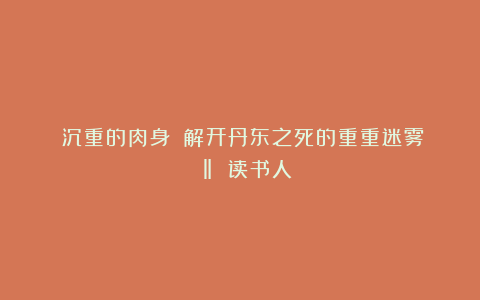
而罗伯斯庇尔的“道袍”国家,人为设定了“应然”的人民公意道德,非常积极自由地建立这种公意道德的社会制度来克服身体的痛苦。
这样,就违背了丹东“任何一种感觉都没有在道德意义上高于其它感觉的权利”,正如我不喜欢这朵花的感觉与你喜欢这朵花的感觉是平等的一样。
问题到此也还好理解,因为丹东与罗伯斯庇尔都有自由感觉和思考的权利。
其中最大的谜团是,罗伯斯庇尔们滔滔雄辩地演说道:“革命……把人类的身体肢解,只是为了使他返老还童。人类……将生长出强健有力的肢体……”这的确很催人奋进参加革命,为了自由民主继续战斗。
可是,身体重新健硕后干什么呢?追随罗伯斯庇尔的现代思想家马尔库塞说:为了性爱的自由享乐。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以为他们要去干什么经天纬地的事业,哪知说了半天,罗伯斯庇尔们回到玛丽昂的道德水平,跟玛丽昂的个体生存道德一致了。
原来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思想分歧仅在于返回自然人性的方式不同。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那些为了自由的革命流血尽是多余!
但丹东反对以人民道德名义杀人的理由并非革命流血本身或它的残忍,而是操革命屠刀的人与被杀的所谓“道德败坏者”同样都有身体,更令丹东不能接受的是,操革命屠刀的正当性仍然基于身体的感觉,并不是超越身体的什么“应然”。这相当于A杀了B,依据恰恰是B反对A 的理由。
这真是太荒谬了。
然而压死丹东的最后一根稻草还不是这种荒谬,是丹东的另一个发现:他发现自己为之辩护的自然性身体不过是一团肉身物质。
正如在厕所这种污秽的地方看到自己最崇拜的老师也来大小便,学生心中原有的老师光辉形象崩塌一样,丹东此时也绝望了,他不仅拒绝人民公意的积极自由,对之前竭力捍卫的,个体享乐的消极自由也绝望了。
身体这团肉身终将化为虚无,捍卫还有什么意义呢?
跟尼采一样, 丹东看了个透彻,甚至看到了现代性的未来:今天人们无论做什么都是用人的骨肉。这就是我们这一时代所受的诅咒,现在我的身体也要用进去了。
罗伯斯庇尔其实有意放他走,现在丹东却要主动去死了,他生无可恋,觉得死于断头台和死于热病老朽没什么区别,临行前他从容地说:“……生命对我是一个负担,谁要夺去,尽管让他夺去好了……空虚不久将成为我的托身之所……”
丹东说要像走下一个女郎的床铺,而不是像离开忏悔椅子那样跟生命告别,算是对自己死感的最后慰藉。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生命的一切经历,皆因“吾身”,丹东看穿了这个臭皮囊,终究是红楼一梦,万境归空,与庄子对待死亡一样,饱含智慧,又有一丝丝悲凉。
刘小枫教授很幽默,把理清丹东的心路历程称作思想侦探在破案,而案犯是诸如卢梭、马克思一类的思想家,被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扰得鸡犬不宁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们是案件的受害人。本案中的侦探毕希纳费劲脑力搞清楚了案子的来龙去脉,自己却身心憔悴死于伤寒。他为后来的思想家们写下了这样的谶语:
……人啊,自然一点吧!你本来是用灰尘、沙子和泥土制造出来的,你还想成为比灰尘、沙子和泥土更多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