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需要大脑网络中整合与分离的动态平衡。我们报告了一种基于fMRI的度量指标,即整合-分离差异(integration-segregation difference, ISD),它捕捉了两个关键的网络属性:网络效率(整合)和聚类(分离)。通过这一指标,我们量化了由麻醉剂异丙酚诱导的从清醒到无反应状态的大脑状态转变。观察到的ISD变化表明,在麻醉期间,大脑网络发生了向分离的深刻转变。在意识反应分别消失和恢复期间,大脑网络中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单模态-跨模态的解体和重组序列。使用整合和分离数据的机器学习模型能准确识别清醒与无反应状态及其转变过程。亚稳态(非平衡瞬态的动态重现)能更有效地由整合来解释,而复杂性(神经活动的多样性)则与分离更紧密地相关。对睡眠状态的并行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发现。我们的结果表明,ISD(整合-分离差异)能可靠地指示意识状态。本文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
引言
大脑面临着将传入的感官信息、行动规划、执行功能及其他认知过程无缝地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意识体验的任务。这需要将空间上分散的模块中的局部神经活动整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过度的整合可能导致不受控制的同步化,如癫痫发作;而整合不足则可能损害统一体验的形成。因此,意识被认为关键取决于大脑在维持灵活计算能力的同时,平衡这两种属性的能力。
整合-分离平衡的理念最初被概念化为对认知捆绑问题的重新表述,后来与神经复杂性的概念建立了联系。在另一个发展阶段,引入了一种名为phi (Φ)的测量方法来定量评估整合信息。然而,计算上的挑战以及关于其神经生物学意义的持续争论限制了phi的实用性。虽然phi的修改版本(如phi*、phi-MIP和phi-max)适用于小规模的动态系统,但对于包括大脑在内的更复杂系统则变得不切实际。
实证研究通常分别测量整合和分离。图论中的度量,如连接器枢纽和参与系数,被用作整合的代理指标,而模块性、局部效率和系统分离则用于衡量分离。这些方法未能捕捉到整合与分离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特性,凸显了对一种基于经验且计算上可行的整合-分离平衡测量方法的需求。
受成熟的小世界性概念的启发,我们假设大脑内的整合-分离平衡依赖于两个关键的网络属性:(1)全局效率,衡量整个网络中信息交换的便捷程度;以及(2)全局聚类,网络中节点聚集并形成紧密互联群组的程度。在清醒意识状态下,效率(与整合相关)和聚类(与分离和模块化相关)被认为得到了优化,以确保适应性强且复杂的大脑功能。
在此,我们提出一种网络度量,我们将其命名为整合-分离差异(ISD;图1a)。ISD定义为整合减去分离,两者分别通过多层次效率和聚类系数进行量化(定义见“方法”部分)。我们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信号的动态功能连接性计算ISD,并通过药理学扰动来描述在意识状态转变期间大脑网络的解体和随后的重组过程(图1b)。通过应用机器学习方法,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根据观察到的整合和分离变化来预测意识状态的转变(图1c)。我们检验了整合-分离平衡、亚稳态和复杂性之间的关系——这些特征被认为是意识状态的重要决定因素(图1d)。最后,我们通过评估在自然睡眠期间采集的fMRI数据,再现了我们的关键发现。
图1:概念与方法框架概述
a 通过ISD(整合-分离差异)量化的整合-分离平衡,定义为整合(由效率捕捉)减去分离(由聚类捕捉)。
b 在诱导和复苏转变期间,网络解体和重组的序列。
c 使用整合和分离来预测意识状态的转变。机器学习模型以跨数据集的方式进行评估。
d 整合-分离平衡与亚稳态和复杂性概念之间的关联。
VIS 视觉网络;SMN 躯体运动网络;DAN 背侧注意网络;VAN 腹侧注意网络;FPN 额顶网络;DMN 默认模式网络;SUB 皮层下网络;Pr 概率;BOLD 血氧水平依赖。
结果
我们分析了在不同研究地点收集的六个独立的fMRI数据集。数据集1至4涉及不同剂量的异丙酚静脉输注。实验条件包括清醒基线、轻度和深度镇静、外科手术水平的麻醉以及意识恢复。数据集1和数据集2包含了转变期(即诱导和复苏)。数据集1(n=19)的fMRI数据采集作为主要数据。数据集2(n=26)用于再现关键结果,并在分析转变期间网络变化的时间顺序时增强统计效力,以及用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跨数据集验证。在数据集1和数据集2中,深度镇静是通过逐渐增加异丙酚输注速率直至受试者对口头命令不再有反应(称为反应消失;LOR)来诱导的。数据集3和数据集4(使用不同剂量的异丙酚)、数据集5(包含不同睡眠阶段)以及一个人脑连接组计划数据集(Dataset-HCP)被用来验证ISD(整合-分离差异)指标的有效性并推广我们的发现。
健康的清醒大脑平衡了整合与分离
我们使用Dataset-HCP(n=1009)来评估健康的清醒大脑是否维持着整合与分离的平衡。使用我们的整合与分离度量,我们观察到在所有参与者中,整合(平均值±标准差:0.41±0.08)和分离(0.46±0.03)的值相似(补充图1)。整合与分离的差异(ISD)为–0.05±0.07,表明正常的清醒大脑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异丙酚诱导的反应消失期间,整合-分离平衡向分离方向偏移
我们分析了数据集1(n=19),以研究在异丙酚诱导的深度镇静期间整合-分离平衡的变化。在基线期间,整合和分离维持在约0.5,导致ISD值约为0(图2a-c)。相比之下,与清醒基线和恢复期相比,LOR(反应消失)与整合的降低和分离的增加相关(图2d, e)。这导致LOR期间ISD值出现统计学上的显著下降(图2f;弗里德曼方差分析:p = 0.0021;事后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基线 vs. LOR p = 0.0050,LOR vs. 恢复 p = 0.0012;p值经过FDR校正;详细统计数据见源数据),表明在麻醉下,全脑网络向更分离(即更少整合)的状态转变。恢复后,ISD恢复到基线水平。基线与恢复之间的ISD差异在统计学上不显著(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p = 0.1165)。即使在ISD计算过程中排除了全局信号回归(GSR)程序,观察到的LOR(反应消失)期间ISD的降低也得到了一致的再现(补充图2c, f;关于我们使用GSR的考虑见“方法”部分)。此外,LOR期间ISD的降低在数据集2中得到了独立再现(补充图3c, f)。斯皮尔曼偏相关分析显示,在控制平均异丙酚浓度时,平均ISD与清醒参与者百分比之间存在强正相关(数据集1:ρ = 0.863,p < 0.0001;数据集2:ρ = 0.803,p < 0.0001;源数据)。这表明ISD是意识状态的可靠指标,独立于异丙酚潜在的非特异性药理效应(如图2中紫色曲线所示)。
图2:异丙酚诱导的无反应状态期间的时间分辨整合-分离平衡。
a-c 数据集1(n=19)的整合、分离和整合-分离差异(ISD)的组平均时间进程。水平虚线是基线期间的中位值。异丙酚浓度由紫色线表示。红色虚线表示对口头命令有反应的受试者百分比。阴影区域代表±SEM。滑动窗口大小为4分钟。
d-f 基线、反应消失(LOR)和恢复状态下整合、分离和ISD的状态平均值(n=19)。每个点代表一个受试者,由灰色线连接。中位值由白色圆圈标记。灰色框表示四分位距。星号表示统计学上显著的差异(配对双侧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FDR校正后p < 0.05。整合:基线 vs. LOR p = 0.0327;LOR vs. 恢复 p = 0.0058;基线 vs. 恢复 p = 0.3144。分离:基线 vs. LOR p = 0.0038;LOR vs. 恢复 p = 0.0029;基线 vs. 恢复 p = 0.0363。ISD:基线 vs. LOR p = 0.0050;LOR vs. 恢复 p = 0.0012;基线 vs. 恢复 p = 0.1165。
g 八个预定义功能性脑网络的可视化。这些网络包括视觉(VIS)、躯体运动(SMN)、背侧注意(DAN)、腹侧注意(VAN)、边缘(LIM)、额顶(FPN)、默认模式(DMN)和皮层下(SUB)网络。
h 基线、LOR和恢复状态的代表性脑网络配置,由其在数据集1中的各自质心图示。网络节点根据分配的网络进行颜色编码。
为了说明功能性脑网络结构的状态依赖性变化,我们描绘了每种状态(基线、LOR和恢复)的代表性网络(图2g, h)。我们通过从数据集1的所有数据点中选择整合-分离空间内每种状态的质心来选定这些网络(例如图3a)。在基线和恢复期间,网络显示出更强的连接性。相比之下,在LOR(反应消失)期间,整体连接性减弱,网络拓扑结构变得更加分离(位于网络中心的节点更少)。
图3:整合-分离差异性能的详细分析。
a 一个等高线密度图,展示了清醒(灰色)和反应消失(LOR;红色)状态在整合和分离参数上的分布。
b 清醒(灰色)和LOR(红色)状态的整合-分离差异(ISD)值分布直方图。
c 比较ISD和其他网络指标性能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通过曲线下面积(AUC)量化。指标包括ISD、整合(多层次效率)、分离(多层次聚类系数)、模块性、参与系数、制图法和系统分离(System Seg)。
d ISD的性能(以AUC衡量)与滑动窗口大小的关系。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ISD(整合-分离差异)在异丙酚诱导的反应消失期间是否表现出滞后现象。滞后现象,即脑状态转变相对于药物浓度变化的延迟,被归因于神经惯性——一种对行为状态转变的阻力。我们的发现揭示了全脑和单个网络ISD轨迹中清晰的滞后模式。具体来说,从LOR复苏期间的ISD恢复发生在比诱导期间ISD初始下降时更低的异丙酚效应室浓度下。这种大脑过程相对于效应室浓度的延迟支持了神经惯性假说(补充图4)。
为了检验大脑状态在整合与分离的二维(2D)域中的分布,我们使用了一个等高线密度图(图3a),该图揭示了清醒(基线和恢复)和LOR状态的明显分布。在清醒状态(灰色),大脑位于整合水平0.519±0.077(平均值±标准差)和分离水平0.503±0.024附近,从而形成一个平衡的大脑状态。相比之下,LOR(反应消失)状态伴随着整合下降至0.457±0.073和分离增加至0.535±0.037。ISD值的分布在清醒与LOR之间有显著不同(图3b;清醒:0.015±0.081;LOR:−0.079±0.094)。为了评估ISD在区分清醒和LOR状态方面的有效性,我们通过比较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将其性能与单独的整合(多层次效率)、单独的分离(多层次聚类系数)以及其他广泛使用的指标进行了评估。ISD在区分清醒与LOR方面表现出优越的性能,AUC为0.77(图3c),不仅优于单独的整合和分离,也优于其他指标,如模块性、平均参与系数(网络间连接的比例)、制图法(节点属性剖面)和系统分离(网络内与网络间连接的差异)。ISD的性能在0.5至8分钟的滑动窗口大小变化范围内保持稳健(图3d)。所有分析,包括ISD的优越性能,都在数据集2中得到了独立再现(补充图5)。
为了进一步证实ISD的稳健性和普适性,我们通过整合另外两个数据集(数据集3和数据集4;见补充图6)的数据,比较了六种不同的异丙酚给药方案(效应室异丙酚浓度[ESC]范围从0到4.0 µg mL⁻¹)。在所有数据集中,清醒基线状态(ESC = 0 µg mL⁻¹)始终保持在特定的整合(0.4–0.6)和分离(0.45–0.55)范围内。在较低剂量的异丙酚下(ESC = 1.0和1.9 µg mL⁻¹),大脑在整合或分离方面表现出显著变化,但不是两者同时变化(补充图6c, d;详细统计数据见源数据)。例如,较轻的镇静(ESC = 1.0 µg mL⁻¹)仅显示整合的降低,而较深的镇静(ESC = 1.9 µg mL⁻¹)仅表现出分离的增加。虽然整合随着剂量的增加而降低(ESC = 1.0 µg mL⁻¹除外),但分离呈现出非线性趋势,即它最初增加,但在最高的外科手术异丙酚剂量(ESC = 4.0 µg mL⁻¹)时下降,接近一种类似于无功能的、空连接的状态。然而,通过整合这两个方面,ISD一致地捕捉到了这种剂量依赖性的轨迹,在所有异丙酚剂量下都显示出与基线相比的显著下降(补充图6e)。
大脑网络解体和重组的时间序列
我们旨在确定全脑ISD(整合-分离差异)变化相对于异丙酚诱导的LOR的诱导和复苏的时间点(图4a, f)。为增加统计效力,我们将数据集1和数据集2连接起来(总n=45)。然后,我们计算了所有受试者(平滑后)ISD曲线的斜率,并确定了斜率值分布在统计学上不同于零的时间段。如图4b中的水平条所示,全脑ISD在LOR(失去反应)开始附近开始下降,并持续下降超过7分钟。在复苏期间,重组开始得比反应恢复要早,大约在转变前4分钟开始,并持续了6分钟(图4g)。
图4:意识状态转变期间整合-分离差异变化的网络序列。
a, f (a)诱导和(f)复苏期间全脑整合-分离差异(ISD)轨迹的组平均值(n=45)。蓝色曲线代表样条平滑的平均值。
b, g (顶部) 样条平滑的ISD轨迹的组平均斜率。实心区域表示统计学显著性时期(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FDR校正后p < 0.05),而虚线区域表示不显著。(底部) 标识统计学显著性时间段的水平条。
c, h 网络ISD曲线的平滑平均值,相应的斜率显示在(d, i)中。曲线周围的阴影区域表示±SEM。
e, j 按显著性起始时间排序的各网络显著ISD变化的时间序列。k 诱导与复苏期间ISD变化的幅度(n=45)。
l 比较诱导和复苏期间ISD斜率极值的散点图(n=45)。
m 单个ISD轨迹与组平均值之间归一化平均绝对误差(NMAE)的条形图(n=45)。在所有子图中,误差棒表示平均值±SEM。
LOR 反应消失,VIS 视觉网络,SMN 躯体运动网络,DAN 背侧注意网络,VAN 腹侧注意网络,LIM 边缘网络,FPN 额顶网络,DMN 默认模式网络,SUB 皮层下网络。 所有八个 预定义的功能性脑网络在LOR期间都经历了显著的解体,并在恢复期间发生了重组(即ISD恢复到基线水平)(补充图7)。基于此,我们检验了与诱导和复苏相关的ISD变化的时间点在不同网络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图4c, d, h, i揭示了在解体和重组过程中,ISD变化时间点的网络差异。在诱导阶段(图4e),我们观察到一个从单模态网络(如视觉(VIS)和躯体运动(SMN)网络)开始的顺序性解体模式。它们在LOR前1-2分钟开始解体。随后是跨模态网络的变化,如额顶网络(FPN)和默认模式网络(DMN)。皮层下(SUB)网络是最后一个解体的。有趣的是,在复苏期间观察到的重组序列与诱导期间观察到的顺序非常相似。重组始于单模态网络(VIS和SMN)的变化,然后是跨模态网络(FPN和DMN),最后是皮层下(SUB)网络(图4i, j)。
关于ISD的变化(图4k),SMN和注意网络(VAN和DAN)显示出比SUB、LIM和跨模态网络(FPN和DMN)更大的变化幅度。在最大斜率,即意识状态转变期间的变化速度方面,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图4l)。我们还证实了网络转变存在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表现为约40%的归一化平均绝对误差(NMAE)(图4m)。
整合与分离作为意识状态的预测指标
为了评估大脑网络的整合与分离是否可以预测意识状态,我们使用了多种监督式机器学习模型(图5a)。这些模型包括随机森林(RF)、支持向量机(SVM)、人工神经网络(ANN)、k-近邻(KNN)和逻辑回归(LR)。在训练时,我们将全脑和所有八个脑网络在每个时间点的整合与分离值连接起来作为输入(共18个特征)。在这五个模型中,RF在预测意识状态方面表现最为准确,当用数据集1进行测试时,其AUC达到0.984,平衡准确率(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平均值)达到93%(图5b, c)。单独使用整合或分离值训练的RF模型分别得到了87%和91%的平衡准确率(补充图8)。
图5:使用机器学习评估整合与分离的预测能力
a 所采用的监督式机器学习模型的示意图:随机森林(RF)、支持向量机(SVM)、人工神经网络(ANN)、k-近邻(KNN)和逻辑回归(LR)。
b 使用数据集1(n=19)比较模型准确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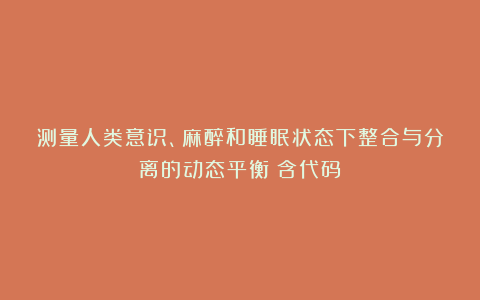
c 模型的ROC曲线(括号内为AUC值)。
d RF模型预测的清醒状态百分比(蓝色)与观察到的行为状态(红色)的时间进程。RF模型在(e)数据集1和(f)数据集2的诱导(蓝色)和复苏(橙色)期间对清醒状态百分比的预测。
g, h 在一个数据集上训练并在另一个数据集上测试的RF模型的可迁移性测试。在不同数据集上测试的RF模型的平衡准确率:i 整个数据,j 转变前后12分钟(第一和第四个条形:n=19;第二和第三个条形:n=26)。在所有面板中,误差棒表示在留一受试者交叉验证中所有受试者的平均值±SEM。
RF模型的预测紧密跟随着通过行为评估的意识状态的时间进程(图5d)。这种一致性在转变期(诱导或复苏前后12分钟)尤为明显(图5e)。RF模型在转变期的准确率很高(平衡准确率为87%)。我们强调,这些转变期并未包含在训练数据中,这凸显了模型的泛化能力(图5i, j)。当用RF模型分析数据集2时,我们观察到了与数据集1中明显的相似趋势(图5f, i, j)。RF模型的跨数据集性能通过在一个数据集上训练然后在另一个数据集上测试来评估。这些可迁移性测试显示平均准确率约为75%(图5g-j)。在预测转变期方面,RF模型优于其他四个模型(SVM、ANN、KNN和LR),如补充图9所示。
整合-分离平衡与亚稳态的关系
已有假说认为,整合-分离平衡可能影响大脑网络的亚稳态程度。亚稳态,即非平衡瞬态的动态重现,促进了大脑在不同神经配置之间流畅转换以及克服能量壁垒的能力,这两者对于应对多样化且快速呈现的认知需求至关重要。为了量化大脑的亚稳态,我们使用了仓本序参数R的移动标准差作为代理指标(图6a)。低亚稳态(图6b)的特征是同步(高连接性)和去同步(低连接性)状态之间的动力学减弱,而高亚稳态(图6c)则与这两种状态之间的突然转变相关。这种波动通过仓本序参数的时间剖面图得以说明(图6d)。
图6:整合-分离平衡与亚稳态。
a 亚稳态计算过程示意图。BOLD信号通过希尔伯特变换转换为相位。动态亚稳态被量化为仓本序参数的移动标准差(σR)。
b, c 具有低(16.7百分位数)和高(83.3百分位数)亚稳态值的代表性时间段,及其对应的地毯图、功能连接(FC)矩阵、脑图和网络图。
d 仓本序参数R的时间变化,对应于(b)和(c)中显示的时间段。
e 数据集1中反应消失和恢复期间亚稳态的组平均时间进程。阴影区域代表±SEM。
f 亚稳态的状态平均值(n=19)。每个点代表一个受试者,由灰色线连接。中位值由白色圆圈标记。灰色框表示四分位距。星号表示统计学上显著的差异(配对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基线 vs. LOR p = 0.0134;LOR vs. 恢复 p = 0.0016;基线 vs. 恢复 p = 0.1075。
g 为单个受试者测量的亚稳态和ISD的斯皮尔曼相关性(n=19)。每个点代表一个受试者,由灰色线连接。中位值由白色圆圈标记。灰色框表示四分位距。
h 用于区分清醒和LOR状态的ISD与亚稳态的等高线密度图。i 一项优势分析中,将亚稳态与整合和分离相关联的增量R²(n=19)。每个点代表一个受试者,由灰色线连接。中位值由白色圆圈标记。灰色框表示四分位距。星号表示统计学上显著的差异(配对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p = 0.0002。ROI 感兴趣区域,LOR 反应消失。
亚稳态的时间进程(图6e)和状态平均分布(图6f)跟踪了意识状态的变化,在LOR期间与基线和恢复期相比有显著降低(弗里德曼方差分析:p = 0.0004;事后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基线 vs. LOR, p = 0.0134;LOR vs. 恢复, p = 0.0016;基线 vs. 恢复, p = 0.1075;p值经过FDR校正;详细统计数据见源数据)。我们还发现亚稳态与ISD有中等到强的相关性(斯皮尔曼相关性:ρ = 0.591 ± 0.226;图6g, h)。为评估整合和分离对亚稳态的各自影响,我们应用了优势分析(图6i)。整合比分离能解释更多亚稳态的方差(整合的增量R² = 0.263 ± 0.190;分离的增量R² = 0.054 ± 0.040;p = 0.0002,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突显了整合在解释大脑亚稳态现象中的相对重要性。这些发现在数据集2中得到了独立再现(补充图10a-c)。
整合-分离平衡与复杂性的关系
我们还研究了在不同意识状态下,大脑信号的复杂性如何与整合-分离平衡相关。优化的复杂性被认为有助于大脑在分离的模块中实现专门化功能,同时保持足够水平的整合。通过应用时间k-均值聚类,我们将fMRI衍生的血氧水平依赖(BOLD)时间序列转换为一个分类的模式序列(图7a)。我们测量了三个不同的复杂性代理指标:模式出现熵、转移概率矩阵熵,以及信息论的复杂性度量“压缩功”。我们观察到这些代理指标之间存在高相关性(补充图11)。为简化起见,我们将它们线性组合成一个统一的度量(称为模式复杂性;更多细节见“方法”部分)。这使我们能够评估大脑活动模式的多样性和时间演变。低模式复杂性时期以更规则、更像晶格的大脑状态和更弱的连接性为标志(图7b),而高复杂性时期则不然(图7c)。
图7:整合-分离平衡与模式复杂性。
a 模式复杂性计算过程示意图。BOLD信号通过k-均值聚类(k=3–100)转换为模式序列。计算每个k值的模式出现熵(Hpatt)和转移概率矩阵熵(HTM)以及压缩功(ETC)。模式复杂性(Cpatt)定义为Hpatt、HTM和ETC的归一化曲线下面积(AUC)的平均值。
b, c 具有低(16.7百分位数)和高(83.3百分位数)模式复杂性值的代表性时间段,及其对应的地毯图、功能连接(FC)矩阵、脑图和网络图。
d 模式复杂性的组平均时间进程。阴影区域代表±SEM。
e 模式复杂性的状态平均值(n=19)。每个点代表一个受试者,由灰色线连接。中位值由白色圆圈标记。灰色框表示四分位距。星号表示统计学上显著的差异(配对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基线 vs. LOR p = 0.0002;LOR vs. 恢复 p = 0.0002;基线 vs. 恢复 p = 0.8092。f 为单个受试者测量的模式复杂性和ISD的斯皮尔曼相关性(n=19)。每个点代表一个受试者,由灰色线连接。中位值由白色圆圈标记。灰色框表示四分位距。
g 用于区分清醒和LOR状态的ISD(整合-分离差异)与模式复杂性的等高线密度图。
h 一项优势分析中,将复杂性与整合和分离相关联的增量R²(n=19)。每个点代表一个受试者,由灰色线连接。中位值由白色圆圈标记。灰色框表示四分位距。星号表示统计学上显著的差异(配对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p = 0.0004。
ROI 感兴趣区域,LOR 反应消失。
模式复杂性的时间进程(图7d)和状态平均分布(图7e)也紧密跟随着意识状态的变化(弗里德曼方差分析:p < 0.0001;事后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基线 vs. LOR, p = 0.0002;LOR vs. 恢复, p = 0.0002;基线 vs. 恢复, p = 0.8092;p值经过FDR校正;详细统计数据见源数据)。我们发现复杂性与ISD有中度相关性(斯皮尔曼相关性:ρ = 0.419 ± 0.285)(图7f, g)。优势分析显示,分离比整合能解释更多复杂性的方差(分离的增量R² = 0.292 ± 0.180;整合的增量R² = 0.042 ± 0.154;p = 0.0004,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图7h)。这些发现在数据集2中得到了独立再现(补充图10d-f)。
自然睡眠期间整合-分离平衡向分离方向偏移
接下来,我们旨在确定我们在异丙酚诱导的药理性无反应状态中的发现是否能推广到自然睡眠的生理状态。我们分析了在人类不同睡眠阶段采集的fMRI数据集(数据集5)。与清醒和NREM1(N1)睡眠相比,整合在NREM2(N2)睡眠期间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下降(图8a;弗里德曼方差分析:p = 0.0058;事后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清醒 vs. N2, p = 0.0322;N1 vs. N2, p = 0.0322;清醒 vs. N1, p = 0.1329;p值经过FDR校正)。分离没有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变化(图8b;弗里德曼方差分析:p = 0.2484)。受整合变化的影响,ISD在N2睡眠期间相比清醒和N1睡眠显著下降(图8c;弗里德曼方差分析:p = 0.0087;事后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清醒 vs. N2, p = 0.0222;N1 vs. N2, p = 0.0222;清醒 vs. N1, p = 0.1943;p值经过FDR校正)。
图8:自然睡眠期间整合-分离平衡、亚稳态和模式复杂性的变化。
a 清醒和各睡眠阶段的整合比较(n=28),包括清醒 vs. N1 p=0.1329,清醒 vs. N2 p=0.0322,N1 vs. N2 p=0.0322。
b 清醒和各睡眠阶段的分离比较(n=28)。分离的变化在统计学上不显著(弗里德曼方差分析 p=0.2484)。
c 清醒和各睡眠阶段的整合-分离差异(ISD)比较(n=28),包括清醒 vs. N1 p=0.1943;清醒 vs. N2 p=0.0222;N1 vs. N2 p=0.0222。
d 清醒和各睡眠阶段的亚稳态(σR)比较(n=20),包括清醒 vs. N1 p=0.1560;清醒 vs. N2 p=0.0334;N1 vs. N2 p=0.0657。
e 一项优势分析中,将亚稳态与整合和分离相关联的增量R²(n=20,整合 vs. 分离 p=0.0002,配对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
f 清醒和各睡眠阶段的模式复杂性(Cpatt)比较(n=20),包括清醒 vs. N1 p=0.6274;清醒 vs. N2 p=0.0414;N1 vs. N2 p=0.0414。
g 一项优势分析中,将模式复杂性与整合和分离相关联的增量R²(n=20,整合 vs. 分离 p=0.0001,配对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在a, c, d, f中,星号表示统计学上显著的差异(事后配对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FDR校正后p < 0.05。在所有子图中,每个点代表一个受试者,由灰色线连接。中位值由白色圆圈标记。灰色框表示四分位距。N1:NREM1期睡眠;N2:NREM2期睡眠。
与清醒和N1睡眠相比,亚稳态在N2睡眠期间下降(图8d;弗里德曼方差分析:p = 0.0078;事后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清醒 vs. N2, p = 0.0334;N1 vs. N2, p = 0.0657;清醒 vs. N1, p = 0.1560;p值经过FDR校正)。模式复杂性在N2睡眠期间也显示下降(图8f;弗里德曼方差分析:p = 0.0407;事后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清醒 vs. N2, p = 0.0414;N1 vs. N2, p = 0.0414;清醒 vs. N1, p = 0.6274;p值经过FDR校正)。值得注意的是,在异丙酚诱导的LOR期间观察到的整合、分离、亚稳态和复杂性之间的关系(图6, 7)在睡眠数据中得到了一致的再现。亚稳态能更好地由整合解释(增量R² = 0.263 ± 0.054),而非分离(增量R² = 0.189 ± 0.040;p = 0.0002,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图8e),而模式复杂性则能更好地由分离解释(增量R² = 0.292 ± 0.180),而非整合(增量R² = 0.041 ± 0.049;p = 0.0001,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双侧;图8g)。
考虑潜在头部运动效应的控制分析
我们调查了ISD、亚稳态和模式复杂性的变化是否由不同意识状态下的头部运动差异引起。为了控制头部运动的潜在影响,我们进行了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并回归掉了帧间位移(FD)值。我们发现头部运动对我们的研究结果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源数据),表明观察到的ISD、亚稳态和模式复杂性的变化并非由运动伪影造成。
讨论
本文证明了整合-分离差异(ISD)能够追踪在异丙酚诱导的反应消失(LOR)的诱导、维持和复苏阶段中意识状态的变化。此外,我们揭示了在进入和脱离LOR的转变过程中,大脑子网络在解体和重组方面存在一个共同的时间序列。通过运用机器学习模型,我们表明ISD可以预测意识状态变化的时间进程。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亚稳态和复杂性依赖于大脑整合-分离平衡的不同方面。具体而言,亚稳态与网络整合相关,而复杂性则更多地与网络分离相关。这些结果可推广至自然睡眠,表明ISD或可用于客观识别意识状态的变化,对评估意识障碍有潜在意义。
意识依赖于大脑整合信息的能力,同时维持分离的子过程以支持专门化的计算。这需要整合与分离的最佳平衡,而这种平衡取决于大脑网络的功能和拓扑属性。以往研究或独立测量两者,或仅关注其中一个方面。在常用的制图法中,大脑状态根据节点属性分布被聚类为主要整合或主要分离的状态。该方法因其二元分类的性质而面临局限,难以对平衡状态进行细致量化,且不适合进行组级推广。
为克服这些局限,我们提出了ISD(整合-分离差异)。该方法通过在多重阈值下计算网络的全局效率(代表整合)和聚类系数(代表分离),然后计算两者的差值,从而得到一个单一、连续的平衡指标。作为一个连续变量,ISD能够量化大脑状态的动态变化及其与意识的关联,从而扩展了以往的方法。
探索意识转变期间的网络序列,有助于揭示麻醉作用下大脑功能动态解体及其随后恢复的机制。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有序的解体与重组序列,与麻醉的诱导和复苏阶段一致。诱导期,单模态网络(如感觉网络)先于高阶跨模态网络(如默认模式和额顶网络)解体,这可能反映了大脑整合感觉信息能力的级联下降。高阶网络的解体发生在反应消失之后,表明即使在无反应状态下,高阶区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在信息处理。然而,功能网络的解体可能阻碍了信号的全局广播,导致反应消失。
复苏期的重组序列与诱导期类似,感觉能力先于额叶执行功能恢复。值得注意的是,复苏始于反应恢复之前约4分钟,且行为反应和大脑动力学相对于药物浓度均表现出滞后现象(如补充图4)。这些发现支持了“神经惯性”假说,即神经元对行为状态的改变存在内在阻力²⁵⁵¹,也与意识丧失和恢复过程中神经动力学不对称的先前研究相符。
我们利用机器学习证明了整合与分离能够预测意识状态。通过随机森林模型,我们能以超过80%的准确率预测从清醒到LOR状态的转变。该模型的跨数据集可迁移性凸显了网络整合与分离作为预测指标的稳健性,并暗示了其临床应用价值。例如,ISD有望用于客观识别意识障碍患者的状态,尤其是在无法获得行为指标的非交流患者中。
我们的结果揭示了整合-分离平衡与亚稳态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亚稳态与整合-分离平衡相关,且主要由网络整合驱动。这支持了亚稳态是与意识涌现相关的系统动力学的神经标志之一的观点。
复杂性是另一个相关量,代表神经模式的多样性。为评估复杂性,我们引入了“模式复杂性”指标,发现无反应状态下其复杂性降低,这与先前研究一致。进一步分析表明,模式复杂性与分离的关联比与整合更紧密。这表明神经动力学的复杂性更多地依赖于促进复杂神经轨迹的局部化拓扑结构,而非全局互联性,凸显了分离的、专门化的神经网络对维持意识体验的重要性。
整合-分离平衡是整合信息论(IIT)和全局神经工作空间理论(GNWT)等多种意识理论的基础概念。两种理论都认为,破坏整合过程是全身麻醉的机制之一。我们的发现支持了无意识状态(如深度睡眠和麻醉)会破坏整合-分离平衡,导致大脑状态以分离为主的假说。全局连接的破坏可能意味着神经工作空间的解耦或整合信息的减少。因此,ISD(整合-分离差异)可能是探测意识所必需的神经工作空间功能完整性或全局信息整合的一个潜在代理指标。
意识状态下,大脑功能连接可动态探索不受解剖结构严格限制的构型;相反,无意识状态的特点是功能连接模式与解剖连接更紧密地对齐,即高结构-功能相似性。因此,我们推测ISD与结构-功能相似性之间存在负相关。我们研究中观察到的无反应状态和睡眠期间ISD的下降,与先前报道的在类似条件下结构-功能相似性增加的发现一致,支持了这一假设。未来的研究需要结合结构与功能数据来严格检验此假说。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研究结果的普适性需通过涵盖更多麻醉剂、致幻剂和意识障碍的研究来加强。其次,观察到的网络转变序列仅限于异丙酚,不能推广到其他类型的无意识状态。第三,4分钟的滑动窗口限制了我们检测更短时间尺度上瞬时波动的能力。第四,我们观察到外科手术水平的异丙酚剂量下脑网络分离度显著下降,这与较低剂量下的增加形成对比,表明麻醉剂存在剂量依赖效应,其神经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结
总之,我们提出了一个衡量大脑整合-分离平衡的指标,并初步证明它能以一种有原则的方式评估变化的意识状态。该方法可广泛应用于不同研究领域,以深入考察大脑网络动力学及其与药理、神经病理和精神疾病的关联。通过将大脑动力学的多个方面(如亚稳态和复杂性)联系起来,我们的发现为理解整合-分离平衡及其与意识的关系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