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相关性血管炎(AAV)是一组小血管炎,常表现为威胁器官或危及生命的症状。目前,免疫抑制治疗已改善了生存率和缓解率,但并非根治性治疗,且副作用常见,无法有效预防复发。临床试验已确立利妥昔单抗(一种抗CD20 B细胞耗竭性单克隆抗体)在疾病诱导缓解期和维持期的作用,并证明糖皮质激素剂量可从历史用药水平显著降低,而不会影响治疗效果。具有更大潜力的更有效且更安全的疗法已经可用或正在研究中。阿伐可泮(Avacopan)是一种口服C5a受体拮抗剂,已获批作为AAV的辅助治疗药物。该药物与利妥昔单抗或环磷酰胺联合使用,可显著减少糖皮质激素的用量,其疗效优于既往标准治疗方案,且可能带来更好的肾脏恢复效果。用于AAV治疗的其他研究中的药物包括下一代抗CD20单克隆抗体、抗CD19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新型补体抑制剂以及可靶向纤维化的药物。除了传统的以临床终点为指标的随机对照试验外,实验医学研究正专注于机制性终点和疾病生物标志物。
Part 1
概述
AAV包括三种罕见疾病——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PA)、肉芽肿性多血管炎(GPA)和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EGPA),其特征是小血管炎症及寡免疫沉积物。MPA和GPA均表现出高频率的坏死性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和肺泡出血,这些症状由小血管炎引起,且通常与ANCA阳性相关。此外,肉芽肿性炎症是GPA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主要影响耳鼻喉(ENT)和肺部,而MPA则不具有这一特征。EGPA的主要特征是哮喘和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肾小球肾炎较为罕见,且仅30%~40%的患者ANCA检测呈阳性。EGPA的治与GPA和MPA的治疗有显著差异,在此不作讨论。
在MPA和GPA患者中ANCAs主要靶向髓过氧化物酶(MPO)或蛋白酶3(PR3),这些酶主要存在于中性粒细胞中,但也存在于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中。抗原特异性与临床表型和预后相关。PR3-ANCA在GPA中更为常见,与发病年龄较轻、复发率较高和死亡率较低相关;而MPO-ANCA在MPA中较为普遍,提示更高的肾脏受累风险、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SRD)的风险以及死亡风险。遗传关联更与ANCA的类型相关,而非临床诊断;因此,区分PR3-AAV和MPO-AAV(而非GPA和MPA)可能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危险分层,并更准确地反映其致病差异。然而,即使基于ANCA的分型也无法将AAV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因为两者均表现出重叠特征和显著的异质性。PR3-AAV 可与局部耳鼻喉疾病相关,或表现为以肾脏受累为主导的全身表现,其特征与 MPO-AAV 中所见难以区分;而部分被归类为 GPA 的患者检测出 MPO-ANCA 阳性,这一发现主要见于中国和日本等地区,在这些地区 MPO-ANCA 是主要的血清型。基于模型的大型患者数据集聚类已识别出多个疾病簇,例如非肾脏型AAV、伴有或不伴有PR3-ANCA的肾脏型AAV,以及以胃肠道和中枢神经系统受累为特征的小型簇,从而为二元分型无法解决AAV谱系复杂性提供了证据。根据是否存在肉芽肿性特征或肾脏受累来定义患者亚组也已被提出,前者会增加复发风险,后者会增加死亡风险。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AAV的病因仍不明确,但血管炎性病变的发病机制已得到更清晰的阐明。在T细胞的辅助下,自反应性B细胞产生分泌ANCA的浆母细胞和浆细胞。循环中的ANCAs可与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表面表达的MPO和PR3结合,在促炎细胞因子和补体因子存在的情况下,导致中性粒细胞活化、脱颗粒并释放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见图1)。随后的组织炎症最终会导致纤维化;然而,尽管ANCAs在AAV中具有明确的致病作用,但其他因素也起着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活动性疾病的患者可能表现为ANCA阴性,而其他不表现出任何AAV特征的个体也可能检测出ANCA阳性。MPO和PR3表位以及替代性ANCA特异性可能解释了致病性差异。
图1. AAV的发病机制。ANCA自身抗原(PR3和MPO)通常被封存在中性粒细胞的初级颗粒中。感染或其他环境刺激可导致中性粒细胞活化,促使PR3和MPO向细胞表面转移。ANCA与这些自身抗原的结合会导致中性粒细胞活化,进而使中性粒细胞黏附于血管内皮细胞。中性粒细胞脱颗粒会导致活性氧(ROS)、蛋白酶和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的释放,从而损伤内皮细胞。趋化因子和PR3、MPO在组织中的沉积导致自身反应性T细胞和单核细胞的募集,从而加剧组织损伤。
标准免疫抑制疗法(如环磷酰胺)的使用改善了AAV患者的生存率,将一种常致死的疾病转变为慢性复发-缓解病程。然而,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出现终末器官损害(如ESRD)、疾病复发或治疗相关毒性,这会影响其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关键致病因素的识别,包括B细胞和补体系统,支持了所谓“靶向”疗法(如利妥昔单抗和阿伐可泮)的发展,并促进了创新治疗方案的评估,这些方案有望为AAV扩大治疗选择。此外,正在研究或已有的策略包括减少感染的发生率(感染是AAV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以及应对常伴随血管炎的合并症,如慢性肾脏病(CKD)。本文聚焦AAV管理中的当前治疗、进展和争议。
Part 2
当前治疗和争议
MPA和GPA患者在临床试验中常被归为一组,接受相似的免疫抑制治疗方案。该方案通常包括3~6个月的“诱导缓解”阶段,随后是较长的“维持缓解”阶段。缓解被定义为疾病活动的停止,应根据治疗开始以来的时间以及是否需要持续治疗(如口服糖皮质激素剂量)来界定。这些参数在不同试验中存在差异,因此各研究之间的缓解率无法直接比较。尽管如此,两项主要试验在其缓解定义中均采用了6个月时伯明翰血管炎活动度评分为0以及糖皮质激素停用的标准。由于缺乏活动性疾病和缓解期的生物标志物,疾病活动度通过经过验证的伯明翰血管炎活动度评分(Birmingham Vasculitis Activity Score)或其衍生评分进行量化,该评分是对活动性疾病临床特征的检查表,例如血尿和鼻结痂。某些临床特征并非血管炎所特有,因此区分由其他原因(包括损伤,即不再对免疫抑制治疗产生反应的不可逆器官功能障碍)引起的症状可能具有挑战性。疾病和/或治疗的长期后遗症还包括不育、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
在过去5年中,国际学会已更新了AAV管理指南。以下章节讨论缓解的诱导与维持,表1和表2概述了主要疗法的特征。当前治疗应用中的主要争议总结于表3。
2.1 诱导缓解
诱导AAV缓解的主要方案是糖皮质激素与利妥昔单抗或环磷酰胺的联合应用。这种方法在6个月内使70%~90%的患者达到缓解,具体取决于定义的严格程度、所应用的糖皮质激素阈值剂量以及其他免疫抑制疗法的使用情况。对于无器官危象或生命威胁表现的患者,如肾小球肾炎、肺泡出血、多发性单神经炎、脑膜受累和眶后疾病,环磷酰胺和利妥昔单抗的替代药物包括霉酚酸酯和甲氨蝶呤,但这些药物的使用因复发率高于环磷酰胺而变得复杂。此外,对于部分筛选的患者,除免疫抑制治疗外,还可使用血浆置换(PLEX)和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2021年,阿伐可泮(一种口服补体抑制剂)获批作为环磷酰胺或利妥昔单抗的辅助治疗药物,与低于标准剂量的糖皮质激素联合使用。
难治性疾病,即未能通过标准治疗方案达到缓解、无法将糖皮质激素减量至低剂量或疾病进展,在AAV患者中发生率约为10%~30%。治疗方案包括从利妥昔单抗转换为环磷酰胺,反之亦然,增加阿伐可泮、血浆置换或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但该组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仍然较差。所有患者,尤其是难治性疾病的患者,均应考虑继发性血管炎的病因,包括娱乐性药物和恶性肿瘤。
2.1.1 糖皮质激素
临床试验结果表明,糖皮质激素的剂量(毒性的重要决定因素)可从之前的常规剂量显著降低,而不会影响治疗效果(见表1)。在国际PEXIVAS试验中,该试验纳入了700多例合并肾脏受累(eGFR < 50 ml/min/1.73 m²)和/或肺泡出血的AAV患者,这些患者接受了环磷酰胺或利妥昔单抗以及一种糖皮质激素减量方案治疗。结果显示,在6个月时口服泼尼松的累积剂量比标准减量方案降低了40%,在疗效方面非劣效,并且与更少的严重感染相关。LoVAS试验还发现,低剂量泼尼松龙(0.5 mg/kg/d)联合利妥昔单抗在疗效上不劣于高剂量泼尼松龙(1 mg/kg/d)。然而,在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均来自日本,且主要为新诊断的MPO-AAV伴轻度肾脏受累,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在国际RITAZAREM试验中,该试验纳入了复发性疾病患者,研究者被允许在每日0.5 mg/kg或1 mg/kg泼尼松(与利妥昔单抗联合使用)之间进行选择,两种糖皮质激素方案的缓解率未观察到差异。总体而言,这些结果鼓励减少糖皮质激素的剂量,但在AAV的初始治疗中,这些药物仍然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治疗手段。通常在开始口服泼尼松龙之前,会给予大剂量静脉注射糖皮质激素,一般为甲基泼尼松龙冲击疗法,剂量为1~3g,疗程3天。大多数试验,包括那些研究口服糖皮质激素减量的试验,均允许使用此类激素。尚无随机对照试验评估甲基泼尼松龙冲击治疗在AAV中的获益情况;因此,缺乏支持该实践的证据(见表3)。一些研究报告显示,静脉注射糖皮质激素在疗效上无差异,但感染风险增加,因此仅建议用于具有器官危象或危及生命疾病特征的患者,例如PEXIVAS试验中的患者。
2.1.2 RTX和CTX
利妥昔单抗(RTX)是一种可耗竭B细胞的嵌合型单克隆抗体,其靶向CD20。自RAVE研究发现其在诱导缓解方面不劣于环磷酰胺(CTX)(一种长期作为AAV标准治疗方案的细胞毒性药物,随后通常使用硫唑嘌呤进行维持治疗)以来,利妥昔单抗的应用日益广泛。与环磷酰胺相比,利妥昔单抗不会增加恶性肿瘤或不育的风险,在复发性疾病和PR3-ANCA阳性的患者中疗效更优(见表1)。此外,对同一试验的事后分析显示,两种方案在肾脏结局方面无差异。
表1. 用于AAV诱导缓解的主要治疗方法。注:ADCC,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CDC,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DCD,直接细胞死亡;IVIG,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NOS,一氧化氮合酶;PML,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a 甲基泼尼松龙或等效药物。b 泼尼松或等效药物。c 血清肌酐>354 μmol/l(4 mg/dl)或需要机械通气的肺泡出血。d 剂量根据年龄GFR进行调整。e 肾小球肾炎、肺泡出血、多发性单神经炎、脑膜受累、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眶后疾病、肠系膜受累和心脏受累。f ENT疾病,无骨骼受累、软骨塌陷或耳聋,皮肤受累但无溃疡,非空洞性肺结节和表层巩膜炎。
然而,由于血清肌酐>4 g/dl的患者被排除在RAVE试验之外,因此利妥昔单抗和环磷酰胺在eGFR显著降低的患者中是否也具有等效性仍不得而知。回顾性观察显示,在晚期肾衰竭患者中,两种方案的结果相似。在PEXIVAS试验中,诱导治疗类型与复合结局无关联,尽管该试验的样本量不足以比较利妥昔单抗和环磷酰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推荐的PEXIVAS减量糖皮质激素方案低于RAVE试验中使用的口服糖皮质激素方案;然而,在PEXIVAS试验中,大多数患者接受了环磷酰胺治疗,而在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中,标准剂量糖皮质激素方案显示出有利趋势,这引发了担忧:与利妥昔单抗联用时,减量糖皮质激素可能不如标准剂量有效。与环磷酰胺不同,利妥昔单抗对驱动炎症的髓系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没有直接作用,这可能导致疾病表现的控制速度较慢。
另一种选择是利妥昔单抗与环磷酰胺的联合使用(见表3)。RITUXVAS试验表明,利妥昔单抗可在严重肾小球肾炎患者(包括需要透析的患者)中减少环磷酰胺的使用。利妥昔单抗治疗组仅接受2~3剂静脉环磷酰胺治疗,而标准环磷酰胺单药治疗组接受6~10剂环磷酰胺治疗,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无差异。利妥昔单抗与低剂量环磷酰胺联合应用在观察性研究中也显示出潜在的减少糖皮质激素用量的作用。目前正在进行一项随机试验,以测试在利妥昔单抗治疗中增加环磷酰胺冲击治疗是否能比标准利妥昔单抗疗法实现更持久的缓解(NCT03942887)。
2.1.3 血浆置换
血浆置换(PLEX)旨在快速清除ANCAs,作为辅助治疗已使用40年,用于治疗具有生命威胁表现的AAV(见表1)。MEPEX试验报告称,对于血清肌酐>500 µmol/l(5.7 mg/dl)的患者,接受PLEX治疗后1年终末期肾病(ESRD)的风险降低。然而,PEXIVAS试验的结果显示,在平均随访3年期间,对于eGFR<50 ml/min/1.73 m²的患者,其复合结局(死亡和/或终末期肾病)发生时间并未显著缩短,该试验规模大于MEPEX试验。PEXIVAS试验中存在一种趋势,即对于血清肌酐>500 µmol/l(5.7 mg/dl)的终末期肾病(ESRD)亚组患者,PLEX治疗更有利,但未观察到对死亡率的影响,这或许可归因于该终点的多因素性质。然而,PEXIVAS试验的事后分析发现,PLEX治疗肾功能的早期恢复显著改善,并且与12个月时ESRD的风险降低相关。此外,尽管PR3-ANCA与组织病理学病变活动性更高、肾脏恢复更好相关,但与未接受PLEX的患者相比,PR3-ANCA组和MPO-ANCA组在接受PLEX后eGFR均有改善,这表明PLEX的治疗反应不因ANCA血清型而异。
一项更新的九项随机试验(包括MEPEX和PEXIVAS)的荟萃分析显示,在接受PLEX治疗的患者中,1年时ESRD的风险显著降低,但死亡风险未降低。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基线血清肌酐水平的升高,估计的绝对风险降低幅度更大。对于血清肌酐为300~499 µmol/l(3.4~5.6 mg/dl)的患者,绝对风险降低为5%;而对于血清肌酐>500 µmol/l(5.7 mg/dl)的患者,绝对风险降低为16%。这表明PLEX在高ESRD风险患者中能提供更大的益处。该荟萃分析还得出结论,PLEX会增加严重感染的风险,且对肾脏存活的益处会随时间减弱。基于这些分析,现行指南和建议指出,对于血清肌酐>300 µmol/l的患者,可考虑使用PLEX治疗(见表3)。相比之下,PLEX应始终用于ANCA和抗肾小球基底膜(GBM)抗体双重阳性的患者;然而,在AAV中,PLEX的剂量尚不确定,存在ANCA清除不完全的可能性,且尚无研究采用针对ANCA阴性的PLEX方案,而这是抗GBM病的推荐做法。采用更有效的降低ANCA水平的方法,如免疫吸附或imlifidase(是一种源自化脓性链球菌的抗体裂解酶),将更好地解决这种方法的治疗获益问题。
2.2 维持缓解
复发,即缓解后活动性表现的再次出现,在诱导治疗后18个月内约1/3的AAV患者中发生。传统与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GPA的诊断、PR3-ANCA阳性、耳鼻喉受累以及既往复发史,但将这些风险因素转化为个性化策略仍然具有挑战性。
2.2.1 糖皮质激素
鉴于其毒性,糖皮质激素应在6个月或更早时减量至低剂量,例如每日5mg(见表2)。糖皮质激素停药的效果尚不明确,已在通过TAPIR试验(NCT01933724)达到缓解的GPA患者中进行了研究。初步结果显示,停用泼尼松治疗的患者在6个月时发生“轻度”复发的频率高于继续每日服用5mg泼尼松的患者(15.5% vs 4.2%,P=0.022),但“重度”复发的频率无显著差异。然而,在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中未观察到差异。
2.2.2 RTX vs AZA
两项针对新诊断患者(使用环磷酰胺诱导治疗)的MAINRITSAN试验和针对复发性AAV患者(接受利妥昔单抗诱导治疗)的RITAZAREM试验均显示,利妥昔单抗在维持缓解方面优于硫唑嘌呤(AZA),且安全性特征相当(见表2)。这些研究中利妥昔单抗的维持剂量有差异,从每6个月0.5g至每4个月1g,持续2年。在RITAZAREM试验中,利妥昔单抗组和硫唑嘌呤组在完成2年治疗后的复发率相似,尽管利妥昔单抗使用了高累积剂量,这表明这些治疗的效果会逐渐减弱。因此,没有证据表明长期使用利妥昔单抗治疗复发性AAV患者可’重置’免疫系统并防止自身免疫表现的复发,从而改变疾病的长期病程。因此,通常需要重复给药,且超过2年的延长治疗可减少复发,但治疗的最佳持续时间尚未确定;然而,利妥昔单抗会增加获得性免疫缺陷的风险,导致低丙种球蛋白血症,降低对疫苗和感染的反应,并已使用个体化方案来限制暴露。在一项随机临床试验中,当ANCA水平升高或B细胞重建时给予利妥昔单抗,与固定给药方案相比,所需累积利妥昔单抗剂量较低,但复发风险数值上更高,这引发了这些生物标志物指导个体化治疗能力的疑问。
表2. 当前AAV缓解期维持治疗的主要疗法。注:ADCC,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CDC,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DCD,直接细胞死亡;NOS,一氧化氮合酶;PML,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a 泼尼松或等效药物。b 耳鼻喉疾病无骨受累、软骨塌陷或耳聋,皮肤受累无溃疡,非空洞性肺结节和表层巩膜炎。
2.2.3 RTX给药时机
诱导治疗后持续ANCA阳性或再次出现,与ANCA稳定阴性相比,与更高的复发风险相关,可能需要继续使用利妥昔单抗治疗。然而,仅有一半的ANCA阳性患者会出现复发,而轻微复发发作可能在ANCA水平无变化或ANCA阴性患者中发生。临床表型有助于解释连续ANCA检测结果,因为ANCA水平的升高似乎与具有血管炎表现的患者(尤其是肾脏受累者)的复发关联更强,而非肾脏和肉芽肿性疾病患者。同样,MPO-ANCA状态与复发风险的关联性高于PR3-ANCA,这可能是因为它与血管炎表现的关联性更强。一项针对MPO-AAV合并肾脏受累患者的大型队列研究发现,在达到并维持MPO-ANCA阴性的患者中,几乎不存在复发;而在MPO-ANCA复现或持续阳性的患者中,复发风险显著增加。因此,对于仅累及肾脏且达到MPO-ANCA阴性的患者,考虑到复发可能性较低,可停用利妥昔单抗;若出现血清学转换(seroconversion),则可重新启用该药物,其预测价值良好。但对于PR3-ANCA阳性且合并肾外受累的患者,决策更具挑战性。
尽管B细胞数量的再次出现表明利妥昔单抗的疗效正在减弱,但B细胞重建与复发之间的关联具有变异性。一些研究报道称,B细胞重建在12~18个月内发生,早于所有复发事件;而在其他队列中,无论B细胞计数如何,均会出现复发。一项单中心随机试验比较了在B细胞重建时给予利妥昔单抗与在ANCAs水平升高后给予利妥昔单抗的情况,研究对象为已完成24个月固定方案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前者导致复发次数减少,但与更高的利妥昔单抗暴露量(平均每年1g)相关,这证实了个体化方案的局限性以及利妥昔单抗的短期效应。
利妥昔单抗固定间隔给药方案的优势在于较低的复发率、可预测性以及可能减少的监测就诊次数;然而,与个体化方案相比,该方案的累积剂量以及使用利妥昔单抗导致的感染风险和继发性免疫缺陷风险可能更高。采用预期性方法,即仅在疾病复发或ANCA水平升高时才给予进一步的利妥昔单抗治疗,需要密切监测并与管理中心保持良好沟通(见表3)。潜在复发的后果应基于患者的既往疾病病程进行考虑。如果复发的影响可能较轻微,例如仅表现为全身症状和耳鼻喉症状,则可采取期待性治疗策略;而如果患者既往已发生严重并发症,例如肾功能丧失,则该策略会增加实质性器官损伤(如ESRD)的风险。
表3. 当前AAV治疗的主要争议及潜在解决方案。注:BiTE,双特异性T细胞结合子;CAR,嵌合抗原受体;GTI,糖皮质激素毒性指数;MPL,甲基泼尼松龙。
Part 3
靶向B细胞和T细胞的治疗进展
利妥昔单抗的疗效支持了B细胞在AAV中具有关键作用的观点。B细胞是浆母细胞和浆细胞的前体,浆母细胞和浆细胞分别是寿命较短和寿命较长的抗体产生细胞,并且能向T细胞呈递抗原,通过分泌细胞因子来协调免疫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利妥昔单抗并不靶向重建B细胞池的祖细胞、浆母细胞或浆细胞,所有这些细胞均为CD20阴性(见图2),可能是导致难治性和复发性疾病的基础的持续性或复发性ANCA阳性的原因。此外,尽管利妥昔单抗治疗后外周血中通常可观察到B细胞完全耗竭,但记忆B细胞仍会持续存在于淋巴组织和靶器官中,并与活动性疾病相关。在AAV中,利妥昔单抗治疗后B细胞重建较其他疾病更为常见地出现延迟,这与B细胞发育的固有缺陷有关,而这些缺陷早于免疫抑制治疗开始之前即已存在,这引发了对该疗法毒性的担忧。
图2. 骨髓和外周的B细胞分化。
T细胞参与AAV的发病机制。T细胞活化的血清标志物(如可溶性IL-2受体)在AAV患者中升高,并与疾病活动度相关;而T细胞耗竭的转录组谱表达则与缓解期延长相关。T辅助细胞(Th 细胞)支持B细胞对ANCA抗原的应答以及ANCA的产生,ANCA是高亲和力、类别转换的IgG1抗体。此外,Th细胞在活动性疾病中会增殖,并分泌与Th1型(IL-12和IFNγ)及Th17型(IL-6和IL-17)相关的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可促进炎症和组织损伤。
针对淋巴增殖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兴B细胞耗竭疗法、B细胞抑制疗法以及影响T细胞的药物已在AAV中进行了研究。以下段落讨论了针对AAV的B细胞靶向治疗和T细胞靶向治疗(表4展示了这些疗法的主要特征,图3描绘了它们的靶点)。
表4. AAV中正在评估的B细胞靶向和T细胞靶向疗法的特征。注:ADCC,抗体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APCs,抗原呈递细胞;APRIL,诱导增殖配体;BAFF,肿瘤坏死因子家族B细胞活化因子;CDC,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性作用;CTLA4,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DCD,直接细胞死亡;NK,自然杀伤细胞;SLE,系统性红斑狼疮;TACI,跨膜激活物、钙调节物、亲环蛋白配体相互作用因子。
3.1 B细胞耗竭疗法
下一代抗CD20单克隆抗体在B细胞耗竭能力和耐受性方面均优于利妥昔单抗。
3.1.1 奥法木单抗
奥法木单抗是一种全人源单克隆抗体,可诱导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增强,在7例AAV患者中使用,其中部分患者对利妥昔单抗不耐受或无反应(见表4)。该治疗方案疗效确切且耐受性良好,但尚未对该药物进行临床试验。
3.1.2 奥妥珠单抗
奥妥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单克隆抗体,通过糖工程改造的Fc段引起增强的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和直接导致细胞死亡,已成功用于少量患者的治疗(见图3)。正在进行的ObiVas试验(ISRCTN13069630)正在检验假设:奥妥珠单抗在诱导PR3-AAV患者组织B细胞耗竭方面优于利妥昔单抗,主要终点为第26周鼻相关淋巴组织中CD19 细胞数量相对于基线的相对百分比变化。ObiVas试验未设计用于比较奥妥珠单抗与利妥昔单抗的临床疗效,但结果可能为其优越性提供生物学证据。更深层次的B细胞清除可能转化为更完全且持久的缓解,这将特别有利于难治性疾病患者,并与利妥昔单抗相比减少再次治疗的需求。奥妥珠单抗在狼疮性肾炎和膜性肾病中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在这些疾病中利妥昔单抗的疗效往往不完全,但其在AAV中的作用仍需确定。
3.1.3 伊奈利珠单抗
抗CD19单克隆抗体,如伊奈利珠单抗(inebilizumab)具有潜力,因为它们能够清除CD20阴性浆母细胞,但尚未在AAV中应用。
3.1.4 达雷妥尤单抗
达雷妥尤单抗是一种主要靶向浆细胞的抗CD38单克隆抗体,在少数对利妥昔单抗及其他治疗均耐药的AAV患者中似乎取得了成功,这提示针对更广泛的B细胞谱系可提高AAV的缓解率(见图3)。抗CD20疗法与抗CD38疗法的联合应用已在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显示出益处,并正在儿童肾病综合征(NCT05704400)中进行评估。值得注意的是,CD38也表达于髓系细胞和部分B细胞亚群;因此,达雷妥尤单抗的有益作用可能还源于该疗法除靶向浆细胞外,还靶向这些细胞。
3.2 B细胞抑制疗法
3.2.1 BAFF抑制剂
针对参与B细胞发育和成熟过程的分子,例如B细胞活化因子(BAFF,也称为BLyS),可以抑制致病性反应,而无需耗竭B细胞。BAFF促进自身反应性B细胞的存活,与健康个体相比,AAV患者的BAFF水平升高(见图3)。BREVAS试验评估了每月静脉注射贝利尤单抗(一种能中和可溶性BAFF的人源单克隆抗体,已获批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联合硫唑嘌呤,用于GPA和MPA缓解期维持治疗的效果(见表4)。本试验因利妥昔单抗逐渐被用作维持治疗药物而提前终止,未观察到贝利尤单抗对复发率的影响;然而,在接受贝利尤单抗治疗的14例患者中,这些患者接受了利妥昔单抗诱导治疗均未发生复发,提示联合使用这两种药物可能具有相加效应。随机、安慰剂对照的COMBIVAS试验正在评估在PR3-AAV患者的标准诱导方案(利妥昔单抗1000mg,分别于第8天和第22天给药)基础上,增加皮下注射贝利尤单抗(自第1天起每周200mg,持续52周)的效果。这项小型研究(36名患者)的主要机制终点是达到PR3-ANCA阴性的所需时间。探索性终点旨在评估利妥昔单抗-贝利尤单抗联合疗法在外周血和淋巴组织中的作用效果。观察到BAFF可保护B细胞免受利妥昔单抗诱导的耗竭,并促进其重建,这表明贝利尤单抗可能增强B细胞耗竭疗法的疗效,并巩固AAV的缓解状态;然而,这种联合疗法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中的研究结果存在矛盾。
图3. 靶向B细胞和T细胞的AAV治疗。目前获批用于AAV的疗法以绿色显示;红色疗法在AAV中无显著疗效;黄色突出显示的疗法目前正在研究中或在病例报告中显示出积极结果;蓝色疗法虽已被提议用于AAV,但迄今为止仅用于其他疾病。CD19由pro-B细胞、B细胞和浆母细胞表达,可通过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或双特异性T细胞结合子耗竭。未成熟B细胞、成熟B细胞和记忆B细胞(未示)表达CD20,可被利妥昔单抗( rituximab)、奥妥珠单抗( obinutuzumab)和奥法木单抗(ofatumumab)(未示)清除;而浆细胞则被达雷妥尤单抗(daratumumab)靶向,达雷妥尤单抗可结合CD38。能够通过B细胞受体(BCR)识别PR3等分子的自身反应性B细胞,可被以PR3为自身抗原的嵌合自身抗原受体(CAAR)T细胞选择性清除。B细胞和T细胞表达CD52,而CD52是阿仑单抗(alemtuzumab)的作用靶点。滤泡B细胞向辅助T细胞提供共刺激信号,可被CTLA4样融合蛋白阿巴西普(abatacept)抑制。ANCA刺激的中性粒细胞产生TNF家族B细胞活化因子(BAFF),这是一种促B细胞存活因子,其作用可被贝利尤单抗(belimumab)拮抗。B细胞刺激性细胞因子BAFF和APRIL共享受体,例如TACI;TACI样融合蛋白,包括泰它西普( telitacicept)和povetacicept能够中和这两种配体。其他BAFF受体包括BAFF-R和BCMA,在B细胞谱系的不同阶段表达。注:APRIL,增殖诱导配体;BAFF-R,BAFF受体;BCMA,B细胞成熟抗原;CTLA4,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TACI,跨膜激活物、钙调节物、亲环蛋白配体相互作用因子。
3.2.2 BAFF和APRIL双重抑制剂
增殖诱导配体(APRIL)是另一种TNF家族细胞因子,可促进B细胞功能,并与BAFF共享受体,该受体包括跨膜激活物、钙调节物、亲环蛋白配体相互作用因子(TACI)。BAFF–APRIL系统的失调与AAV有关。针对GPA和MPA的泰它西普(NCT05962840)和povetacicept(NCT05732402)临床试验已启动,这两种药物均为基于TACI的BAFF和APRIL双重抑制剂(见图3)。
3.3 基于细胞疗法
3.3.1 CAR-T治疗
抗CD19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是经过工程化改造的自体淋巴细胞,能够清除CD19阳性细胞(见图3)。这种疗法可显著耗竭B细胞和浆细胞,并已在对常规治疗难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中实现了持续的临床和血清学无药物缓解。抗CD19 CAR T细胞可保护小鼠免受MPO-ANCA诱导的肾小球肾炎侵害,并且在一名难治性AAV患者中实现了骨髓内B细胞完全耗竭和ANCA阴性。多项I-II期研究将评估CAR T细胞疗法在AAV患者中的应用。
尽管抗CD19 CAR T细胞通过清除自身反应性细胞具有提供治愈的潜力,但在AAV中实施这种疗法仍具有挑战性(见表4)。CAR T细胞的生产成本高昂,涉及多个步骤,包括白细胞分离、基于慢病毒的转导以及体外扩增。此外,患者在回输前需要接受淋巴耗竭性预处理方案,并服用低剂量糖皮质激素,以促进体内良好的细胞扩增。因此,该治疗需要临床稳定,可能不适用于AAV急性发作的诱导缓解方案。更适宜接受该治疗的人群可能是患有非重度、难治性或频繁复发性疾病且需要长期无药物完全缓解的患者,因此或许可以证明该治疗的高成本是合理的。CAR T疗法在AAV中的已知不良事件(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的风险尚不明确,但这些风险也可能改变风险——获益比,并影响患者选择。
使用来自健康供体的异基因CAR T细胞已被提出,与自体CAR T细胞不同,这些细胞可以立即可用。但这些细胞可能会引起移植物抗宿主病,并被受体快速排斥。
3.3.2 CAAR-T治疗
已对工程化表达嵌合自身抗原受体(CAAR)的T细胞或自然杀伤细胞在某些自身抗体介导的疾病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这些细胞可能用于AAV的治疗(见图3)。CAAR细胞可被自身反应性细胞识别,并能选择性地清除这些细胞,从而保护其余的B细胞池。
3.3.3 双特异性T细胞结合子治疗
另一种选择是双特异性T细胞结合子,这类抗体可靶向B细胞标志物(如CD19)和T细胞上的CD3,从而形成免疫突触并增强对B细胞的杀伤作用,该方法已在类风湿关节炎中得到应用(见图3)。细胞治疗领域发展迅速,多种体内细胞生产方法正在被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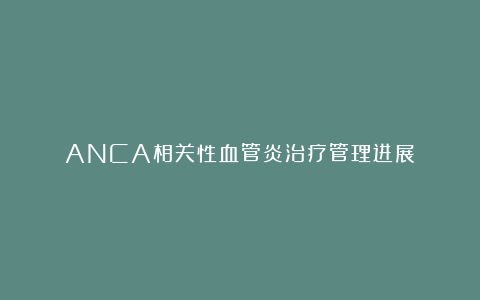
3.4 靶向T细胞疗法
T细胞受多种用于AAV的疗法影响,包括糖皮质激素、环磷酰胺、硫唑嘌呤和霉酚酸酯。此外,环孢素A作为一种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可抑制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在一小部分GPA患者中作为维持治疗药物显示出积极结果。对RITUXVAS试验的分析发现,T细胞小管炎的存在与利妥昔单抗治疗反应不佳相关,强调了在治疗中靶向T细胞的临床意义。新兴的T细胞靶向疗法已在AAV中进行了评估。
3.4.1 阿伦单抗
阿仑单抗是一种用于多发性硬化的抗CD52单克隆抗体,可诱导T细胞的持续耗竭,对B细胞、单核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也有一定程度的耗竭作用(见图3)。II期Aleviate试验纳入了12例对标准治疗无反应的AAV患者,比较了30mg与60mg阿仑单抗的疗效。仅有1/3的患者达到完全缓解,且频繁复发;因此,阿仑单抗尚未被提议作为利妥昔单抗的替代方案。
3.4.2 阿巴西普
阿巴西普是一种融合蛋白,由惰性的Fc片段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的胞外结构域组成。它与共刺激蛋白CD80和CD86结合,从而阻止T细胞活化(见图3)。尽管在一项小规模先导试验中取得了良好结果,但III期ABROGATE试验(NCT02108860)显示,在复发性、非重度GPA患者中,阿巴西普与安慰剂相比,在治疗失败率方面无差异,这表明该疗法在AAV中并无显著获益。
3.4.3 乌司奴单抗
肾脏受累的AAV患者,其肾脏中产生Th1和Th17细胞因子的CD4 T细胞富集的证据,促使人们考虑使用乌司奴单抗。乌司奴单抗是一种人单克隆抗体,其靶向IL-12和IL-23共有的p40亚基,这两种细胞因子分别促进Th1和Th17细胞的分化(见图5)。乌司奴单抗联合糖皮质激素及小剂量环磷酰胺治疗4例复发性AAV患者,与良好的临床疗效相关。
Part 4
补体靶向治疗的进展
补体系统包括经典途径、凝集素途径和旁路途径,这些途径均汇聚于补体成分5(C5)的生成,C5被裂解为过敏毒素C5a和膜攻击复合物,后者也称为C5b-9。补体因子在AAV中的作用长期以来被认为较为次要,尽管在若干患者的血清和组织中可检测到补体因子的降解产物,且其水平与疾病活动度相关。在过去二十年中,动物模型表明补体系统,特别是旁路途径,在血管炎病变的发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见图4)。C5a被鉴定为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在ANCA诱导激活中的关键启动因子,这导致进一步的C5a生成,从而维持该过程的放大(见图5)。在MPO-ANCA诱导的小鼠肾小球肾炎模型中,基因敲除C5a以及药理学抑制C5a受体(C5aR1,也称为CD88)可阻止肾小球新月体的形成,并促成了针对C5a-C5aR1轴的治疗方法的发展。
图5. 补体在AAV中的作用。ANCA与细胞表面的自身抗原(PR3和MPO)结合,会导致中性粒细胞活化并释放因子(如备解素,P因子),从而激活补体旁路途径。膜攻击复合物(MAC;C5b-9)的作用有限,但过敏毒素C5a的生成可吸引更多中性粒细胞。当C5a与细胞表面的C5a受体(CD88)结合时,会增强中性粒细胞的致敏和活化,从而形成促进炎症的扩增环路。
4.1 阿伐可泮
阿伐可泮(avacopan)(曾用名CCX168)是一种口服给药的小分子药物,可抑制C5aR1,但不干扰C5b-9。C5b-9在防御包膜细菌(如脑膜炎奈瑟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见图5)。2021年,它作为首创新药( first-in-class)的补体抑制剂获批,这在AAV领域是一个里程碑,因为阿伐可泮是首个以GPA和MPA为主要适应症开发的疗法。II期临床试验CLEAR和CLASSIC以及III期临床试验ADVOCATE显示,阿伐可泮作为辅助治疗具有疗效且耐受性良好,并显示出其作为减少糖皮质激素用量的疗法的潜力。
ADVOCATE是一项双盲、双模拟试验,比较了阿伐可泮30mg 每日两次服用52周与泼尼松60mg 每日服用(21周时逐渐减量至停药),联合环磷酰胺,随后使用硫唑嘌呤或利妥昔单抗(不联合硫唑嘌呤)治疗330例新诊断或复发性AAV患者。受试者可接受开放标签静脉甲基泼尼松龙和口服泼尼松治疗,最长持续4周。阿伐可泮在第26周实现缓解方面不劣于泼尼松,在维持缓解至研究结束(52周)方面更优。阿伐可泮组患者的平均累积糖皮质激素剂量比泼尼松组低2/3,且糖皮质激素毒性更少。此外,接受阿伐可泮治疗的患者在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方面的改善程度大于接受泼尼松治疗的患者,这可能反映了更好的疾病控制以及糖皮质激素部分不良反应的减少,例如失眠、体重增加和皮肤脆弱性。
阿伐可泮还与蛋白尿的早期减少以及更好的肾功能恢复相关,在基线eGFR较低(15~30 ml/min/1.73 m²)的患者中观察到最佳改善。使用阿伐可泮治疗时,eGFR的增加在第26周后持续存在,而使用泼尼松治疗时则未出现这种情况,这表明阿伐可泮具有持续的有益效果。
当前指南建议,在活动性疾病患者中,除环磷酰胺或利妥昔单抗外,应考虑将阿伐可泮作为糖皮质激素广泛使用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在糖皮质激素毒性风险增加的患者以及伴有严重肾脏受累的患者中。使用阿伐可泮可立即起效,大多数患者在4周时可实现糖皮质激素的快速减量。此外,尽管阿伐可泮在维持缓解方面具有疗效,但其对于接受利妥昔单抗维持治疗的患者是否存在额外益处,以及是否应持续使用超过1年,目前尚不清楚。阿伐可泮通过抑制中性粒细胞的活化和脱颗粒,从而减少MPO和PR3的释放,这可能会降低促进针对ANCA抗原的免疫应答的抗原驱动作用,进而有助于预防复发。
目前,阿伐可泮的高昂成本既限制了对该疗法的获取,也限制了治疗持续时间,且长期治疗结果尚不可用。授权后研究,如一项IV期随机试验(NCT06072482)和一项前瞻性登记研究(NCT05897684),将进一步评估阿伐可泮的安全性,并明确治疗是否转化为肾脏衰竭发生率和总体生存率的改善。令人欣慰的是,阿伐可泮在真实世界人群中似乎具有益处,包括那些患有低氧性肺泡出血、eGFR<15 ml/min/1.73 m²或需要透析的患者,这些患者被排除在ADVOCATE试验之外,这表明其疗效覆盖了更广泛的表现形式。
图5. 针对ANCA诱导炎症机制的创新疗法。用绿色突出显示的是目前获批用于AAV的疗法;用黄色突出显示的是已在AAV患者中使用或正在接受测试的疗法;而用紫色突出显示的疗法则在体外实验或其他疾病中显示出益处。组织蛋白酶C( Cathepsin C)抑制剂可能阻止未成熟中性粒细胞溶酶体中PR3的激活。ANCAs可被imlifidase(一种特异性IgG抗体裂解酶)降解,ANCAs通过与Fc受体(FcR)结合并随后激活SYK信号通路来诱导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的活化(未显示),而这种活化可被福坦替尼(fostamatinib)抑制。补体旁路途径,该途径可生成C5a,对中性粒细胞的活化、趋化和脱颗粒以及内皮细胞活化至关重要。补体激活可通过伊普可泮(Iptacopan)(B因子)、依库珠单抗(eculizumab)(C5)、韦洛利单抗(Vilobelimab)(C5a)和阿伐可泮(avacopan)(C5aR)靶向不同阶段。活化的中性粒细胞释放PR3和MPO,这增强了活性氧(ROS)的产生及随后的内皮炎症。此过程可被mitiperstat抑制。中性粒细胞也会发生NETosis,释放解凝聚的染色质和毒性蛋白,如MPO和PR3,这些物质会被T细胞识别。GSK484抑制PAD4,一种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形成的关键酶。IL-12和IL-23分别促进Th1细胞和Th17细胞的分化,进而导致促炎性Th1细胞和Th17细胞因子(如IFNγ和IL-17)的释放,而这些通路可被乌司奴单抗抑制。内皮细胞在炎症刺激下被激活,并获得促血栓表型,这促进了血小板聚集。注:PAD4,肽基精氨酸脱亚胺酶4。
4.2 其他补体靶向疗法
4.2.1 韦洛利单抗
韦洛利单抗(Vilobelimab)(IFX-1)可中和C5a,并阻止其与C5aR1以及另一种C5a受体C5L2结合,后者可能作为C5aR信号通路的负调节因子发挥作用(见图5)。两项II期临床试验(IXPLORE,NCT03712345)和(IXCHANGE,NCT03895801)显示,与泼尼松相比,韦洛利单抗具有安全性及有效性,且糖皮质激素累积剂量较低,但目前暂无进一步研究计划。
4.2.2 依库珠单抗
依库珠单抗(eculizumab)及作用时间更长的雷夫利珠单抗(ravulizumab)可抑制C5,并阻止C5a以及C5b-9的生成,而C5b-9在补体介导的血栓性微血管病的发病机制中起核心作用(见图5)。少数AAV患者,包括合并血栓性微血管病的患者,已成功接受依库珠单抗治疗。与阿伐可泮不同,抗C5疗法需要对包膜细菌进行疫苗接种和抗生素预防。
4.2.3 伊普可泮
针对旁路途径中靠近C5的成分,如C3、B因子和D因子,这一靶向策略得到了观察结果的支持,这些成分的降解产物与AAV的疾病活动度相关。伊普可泮(Iptacopan)(一种口服的B因子抑制剂)将在AAV(NCT06388941)的II期研究中进行调查(见图5);
4.2.4 其他
抑制旁路途径主要调节因子的补体H相关蛋白在AAV中升高,并已被提议作为治疗靶点。其他针对C3及其他补体通路方面的新兴治疗药物正在被考虑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包括AAV。
尽管肾脏中C3和B因子的沉积以及血清C3水平降低与更严重的疾病表型持续相关,但尚无研究评估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对补体拮抗剂的反应。出现补体激活迹象的患者可能更能从针对补体通路的疗法中获益,未来的研究可识别能够指导这些疗法应用的标志物。
Part 5
新靶点和生物标志物
目前正在开发多种可作为AAV免疫抑制治疗补充疗法的治疗手段。对疾病发病机制的深入理解已促成了新型治疗靶点的识别,以阻止ANCA诱导的炎症。此外,人们日益认识到,纤维化以及其他合并症(如心血管疾病和免疫缺陷)在AAV患者中会造成显著损害,应予以特异性治疗。能够实现疾病早期识别并预测复发的生物标志物也有助于改善疾病管理。以下部分将讨论新型靶点和生物标志物方面的进展(表5展示了这些疗法的特征,图5展示了部分药物及其靶点)。
表5. AAV患者管理的潜在策略。注:MMP,基质金属蛋白酶;NET,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PAD4,肽酰精氨酸脱亚胺酶4;PD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ROS,活性氧物种;STAT,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SYK,脾酪氨酸激酶;TLR, Toll样受体。
5.1 靶向ANCAs诱导的炎症
5.1.1 IgG裂解剂
Imlifidase是一种源自化脓性链球菌的重组蛋白酶,可降解循环和组织结合的人类IgG(见图6),并在GOOD-IdeS-01试验中快速清除抗肾小球基底膜(anti-GBM)病双血清阳性(同时存在抗GBM抗体和ANCA)患者的ANCAs。据报道,imlifidase在PR3-AAV合并难治性肺出血患者中的成功应用。II期研究INFLIMIDARDSe(EudraCT编号:2021-004706-22)将评估imlifidase在与AAV相关的肺泡出血患者中的疗效(见表5)。
图6. imlifidase作用机制。
5.1.2 组织蛋白酶C抑制剂
PR3需要在中性粒细胞成熟过程中由溶酶体蛋白酶组织蛋白酶C激活。体外实验表明,组织蛋白酶C抑制会降低中性粒细胞表面PR3的表达,从而降低PR3-ANCA诱导细胞活化、NET形成和肾小球内皮细胞损伤的能力(见图5)。这些发现可能会促使对AAV中的组织蛋白酶C抑制剂进行进一步研究,目前这些抑制剂正被用于支气管扩张症的评估(见表5)。
5.1.3 MPO抑制剂
活化中性粒细胞分泌的MPO介导氧化损伤,并与肾脏疾病严重程度相关。在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小鼠模型中,抑制MPO可改善肾脏炎症。Mitiperstat(AZM198)是一种口服的MPO抑制剂,已在心力衰竭中进行过研究,可考虑用于AAV的治疗(见图5)。
5.1.4 SYK抑制剂
脾酪氨酸激酶(SYK)介导多种受体的细胞内信号传导,包括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CAs)与Fc段的结合,并在ANCA激活的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中表达上调(见表5)。在活动性肾AAV患者的肾小球中观察到SYK表达增加。福坦替尼(fostamatinib)是一种口服SYK抑制剂,已获批用于治疗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在MPO-AAV小鼠模型中改善了肾脏和肺部病变(见图5)。
5.1.5 PAD4抑制剂
ANCAs还会诱导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的形成,而这些NETs对内皮细胞具有毒性,并会进一步刺激ANCA的反应。肽基精氨酸脱亚胺酶4(PAD4)可使组蛋白瓜氨酸化,是NET形成所必需的(见图5)。GSK484是一种口服的PAD4抑制剂,在MPO-ANCA诱导的小鼠肾小球肾炎模型中,可阻断NET的产生、MPO沉积和肾小球炎症,可能在AAV的治疗中发挥作用(见表5)。
5.2 纤维化
Claudin-1是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的组成部分,由肾小球新月体中的壁层上皮细胞过度表达并在非连接部位暴露,已与肾小球硬化(肾小球内的纤维化)相关。Lixudebart(ALE.01)是一种单克隆抗体,其靶向暴露的非连接性claudin-1表位,在MPO-ANCA诱导的小鼠肾小球肾炎模型中降低了蛋白尿和纤维化。II期临床试验RENAL-F02(NCT06047171)正在研究Lixudebart是否能延缓肾AAV患者进展为CKD的进程(见表5)。
间质性肺疾病(ILD)在MPO-ANCA阳性患者中较为常见,预后较差。抗纤维化疗法(如尼达尼布和吡非尼酮)现已获批用于特发性肺纤维化,但在MPO-ANCA相关间质性肺疾病中的评估仅限于回顾性研究系列。一项关于吡非尼酮在MPO-ANCA-ILD(NCT03385668)中的初步研究已完成患者招募,结果有待公布(见表5)。
5.3 标志物
在过去十年中,已对具有改善肾脏复发检测潜力的尿液生物标志物进行了评估。与AAV相关性肾小球肾炎患者尿液可溶性CD163(usCD163)水平升高,该标志物为巨噬细胞脱落的清道夫受体,可将活动性肾脏血管炎患者与健康个体及缓解期患者区分开来。一项大型多中心分析将usCD163-肌酐比值阈值定义为250 ng/mmol,作为活动性肾脏血管炎的cut-off值,目前已有经验证的诊断试剂盒可供商业使用。值得注意的是,usCD163水平可反映肾小球炎症,但并非特异性于AAV,在其他类型的肾小球肾炎中也正在被评估。
已提出进一步的潜在血液和尿液疾病活动生物标志物,可能结合使用以提高检测和监测疾病复发的准确性。在RAVE试验中,入组时循环免疫检查点的水平与利妥昔单抗治疗失败相关,并且与持续缓解和感染均相关。如果这些发现能在独立队列中得到验证,这些标志物的使用可能会促进个性化免疫抑制治疗。
Part 6
预防感染
在COVID-19疫情期间,免疫抑制疗法(尤其是利妥昔单抗)对疫苗后保护性抗体产生的负面影响得到了凸显。在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中,T细胞应答似乎未受影响,而B细胞耗竭预测无法实现血清转化。体液免疫反应可通过额外的加强疫苗剂量进一步增强。即使接种者体内抗刺突蛋白抗体检测不到,与未接种者相比,其发生中度或重度COVID-19的风险仍降低了五倍。PNEUMOVAS试验比较了在利妥昔单抗治疗开始时接种1剂、2剂或4剂结合型肺炎球菌疫苗(PCV13),在接种肺炎球菌多糖疫苗(PPV23)之前,对95例活动性AAV患者的效果。初步结果显示,没有任何一种策略能对所有血清型产生反应。但在按年龄分层后,接种PCV13双剂量的患者比接种单剂量或四价剂量的患者具有更高的反应概率。ACQUIVAS(NCT03514979)是一项开放标签、IIb期研究,同时也评估处于缓解期的AAV患者对PCV13和PPV23单次剂量的反应。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者与其他治疗方案患者的免疫原性将进行比较。
Part 7
CKD和CVD
在AAV患者中,心血管疾病(CVD)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升高,其中CKD患者的风险尤为高。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现已成为CKD治疗的主要手段,并用于AAV患者,尽管这些药物的获批试验要么排除了AAV患者(如DAPA-CKD试验),要么仅纳入了少量此类患者(如EMPA-KIDNEY试验)。与AAV相关的肾小球肾炎患者也被排除在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的试验之外。排除这一高风险群体会导致护理不平等和治疗被剥夺。
一项研究者发起的研究发现,缓解期AAV患者的血浆内皮素-1水平较健康志愿者升高,并与动脉僵硬度和内皮功能障碍相关,而后者已知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内皮素-1抑制能够减轻这些变化,双内皮素-1受体A和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司帕生坦(NCT05630612)正在AAV患者中进行评估。
Part 8
小结
目前,AAV的治疗方法能够实现较高的生存率和缓解率,但患者仍面临显著的复发风险和毒性负担。新兴疗法为进一步改善治疗结局提供了有前景的机会。利妥昔单抗的优异疗效促使人们对其下一代抗CD20单克隆抗体进行评估,而B细胞抑制剂(如贝利尤单抗)和T细胞靶向药物(如阿巴西普)的应用似乎效果欠佳。此外,对补体系统在AAV发病机制中重要性的认识,促成了阿伐可泮的获批。该药物有望实现糖皮质激素剂量的显著降低,并带来更好的疾病控制和更优的肾脏恢复。一个主要的未满足需求是开发一种安全、长期的AAV治疗方法;基于细胞的疗法正在迅速发展,可能为AAV患者提供治愈方案,尽管将这些疗法转化为临床实践面临挑战。此外,已确定与ANCA诱导的炎症和纤维化相关的通路为潜在靶点。改进试验终点对于证明新兴疗法相对于当前可用疗法的优越性也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除了大型全球性试验外,针对较小且同质化人群的研究可专注于机制性终点和生物标志物。过去几十年,AAV的管理已取得重大进展,并持续稳步前进。
参考文献:
1.Geetha D, et al. Am J Kidney Dis. 2020 Jan;75(1):124-137.
2.Crickx E, et al.KidneyInt, 2020,97:885-893.
3.Trivioli G, et al. Nat Rev Rheumatol. 2025 Jul;21(7):396-413.
4.Pawel-RammingenUV, et al. EMBO J, 2002.
END
点赞
收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