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人:武满彻[1] 、莲实重彦[2]
速记·雨宫雅子
翻译:Zed Noughts
全文6143字,阅读约需25分钟
—原文《撼动智识的宇宙论变容——关于<乡愁>》刊载于1984年3月31日,日本电影场刊《乡愁》·电影评论
武满: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看了两遍,第二遍的感受更好。在一个空间里看到各种色彩的蜕变,让我充分感受到了‘电影‘的本质。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满足的观影体验。第二遍观看时,我从头到尾都处在兴奋之中(笑)。
第一次看的时候,终究还是会不自觉地拘泥于其中的隐喻和象征,试图把每个元素都分析清楚,反而丢失了电影的整体感。第二次时,我更多是用一种听觉的方式去‘看‘,或者说去‘聆听‘。这样一来,我突然觉得这其实是一部非常明晰的电影。
它特别清晰,比如多梅尼科房间墙上挂着的‘1+1=1’——即使是两滴油,落下时也会融合成一滴。这是塔可夫斯基一贯的主题。那种近乎偏执的对同一性的渴望。当然,我认为其中包含了许多深刻的问题,但仅仅观看,就让人觉得已经足够了。
《乡愁》
听说很多观众认为这是部难懂的电影,但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确实,如果执意要去理解其中散布的象征和隐喻,视线被这些东西吸引的话,可能会觉得难懂。
但如果从整体来看,我认为它与其说是一部让人‘理解‘的电影,不如说是一部让人‘感受‘的电影。对我来说,就像聆听音乐一样,深受感动,心情愉悦。
莲实:似乎流传着塔可夫斯基电影艰深难懂的说法。不仅是在日本。听说,谢尔盖·邦达尔丘克[3]对他没有好感,在意大利时曾说苏联也有拍晦涩难懂电影的导演,还提到了塔可夫斯基的名字,结果这话就传遍了全世界。
谢尔盖·邦达尔丘克(左一)在《战争与和平》
但是,(这部电影)一点也不难懂。无论是空间的营造还是时间的处理,都以不辜负《乡愁》这个片名的方式精心构建。而且不仅仅是构建得隐秘,更在于存在超越那种隐秘设计的、充满电影动感的瞬间,所以即使从最通俗的意义上来说,也让人心跳加速。
黑白画面中,女孩带着大狗跑向沼泽的那个场景,它不同于好莱坞那种精心算计愉悦感的故事技巧,而是以出其不意的效果,瞬间概括了全篇。
《乡愁》
虽然故事线索还很浅,但那画面突然让四周弥漫起一股怀旧之情,之后即使闭上眼睛,也能切身感受到乡愁究竟是什么。这种直接性让人安心,不过话说回来,或许最近这些年,某种特定的艰深性、带引号的‘艰深‘,确实已经消失了。
武满:确实是少了呢。
莲实:我认为,带引号的‘艰深‘,本质上是60年代以后电影的特性。那是一个已经明确‘电影再也无法被愉快地创作、也无法被愉快地观赏‘的时代,在这种不幸的状况下,能够自觉思考如何克服电影困境,同时又能逼近电影直接性的作者,全世界大概只有四五个人。戈达尔,然后还有塔可夫斯基……
武满: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莲实:对。然后还有大岛渚。在戈达尔的同代人中,差不多就这些了。《乡愁》(Nostalgia,1983)给我的感觉,是这些作者探索的一次成功实践。这在他迄今为止的作品中,恐怕也是出类拔萃的。
武满:我也赞成这个意见。刚才列举的这几位作者,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作者(cineaste),而其中塔可夫斯基,是不是和其他人有相当大的不同?其他作者,终究还是相当重视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塔可夫斯基则更偏向于内省型。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莲实:是啊。不过,对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也并非没有苦涩的回忆。《伊万的童年》( Ivan’s Childhood,1962)这样的作品,不良的心理主义和肤浅的影像主义相互迎合,从中还显露出一种轻率的剪辑至上主义倾向。
《安德烈·卢布廖夫》(Andrei Rublev, 1966)也是一旦把握不好就可能陷入形式主义美学的作品;到了《飞向太空》(Solaris, 1972)的时候,仍然是理念先行,影像薄弱,观众需要自己去弥补那种薄弱,否则就无法达到完美的表达。所以观感上是缺乏电影性的冲击,只能靠理性去理解。
《飞向太空》
武满:《飞向太空》我倒不讨厌,但确实有种不协调的感觉,而且就摄影而言,影像的表现力也还是差了一点。这次(《乡愁》)的摄影我觉得非常出色。
莲实:我在想,在戈达尔之后的60年代作者中,或许只有那些认真处理了故乡、或者说与国籍关系的人,才能真正拍出杰出的作品。
而塔可夫斯基这个人,说不定恰恰是没有‘故乡‘的人。意大利对他而言确实是异域,但正是在这种电影环境的变化中,他创造出了与以往摄影在透明度和改造自然的力量上都完全不同的、卓越的影像。
这远不是摄影优美、色彩漂亮这个层次的问题,而是画面中充满了一种直接迫近我们感性、具有冲击力的力量。我想,这大概就是那种拥有/不拥有故乡的人进行电影创作的非凡之处吧。
《乡愁》
武满:虽然和安哲罗普洛斯明显不同,但我觉得《乡愁》的拍摄用了很多长镜头,而且非常成功。摄影机一旦跟随物体,被摄对象就会往复运动,但正因如此,能让人感觉到呼吸的变化,非常美妙。
莲实:每个场景中描绘的事物所承担的感觉性意义是不同的。水不是单一地象征某个东西,而是展现了它无限的表情。比如从车外静静拍摄浸泡在热水中的人,转眼间,又切换到干涸的水域……
《乡愁》
武满:非常厉害,那个水干涸的地方也是。
莲实:为了不让火焰熄灭而多次往返的那一段,和之前那种神秘氛围、内心之旅的感觉不同,直接袒露了肉体的试炼,或者说,是您刚才说的那种对外部关切的直接呈现。那个场景真是让人捏一把汗。
《乡愁》
武满:那种程度的张力非常了不起。
莲实:最近的电影里,很少有那样紧张感的作品了。
武满:主人公暂住的旅馆房间里,镜头正对着床,从开始下雨到雨停的那段拍摄,令人屏息。窗外墙壁仿佛有东西掉落的氛围、从灯光到声音的设计,全都棒极了。
《乡愁》
莲实:确实,火焰、雨滴这些元素,不能说没有重复使用之感,但这并非固守自己的世界,而是让人感觉自身对水(这类元素)的关切,正不断地被外部世界剥离出去。
很明显,这不是意象的电影,而是一部每一瞬间都在体验那种变容的作品,在这里,作者自身也被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容的存在。就像是自己亲手剥去迄今为止覆盖在身上的层层外壳,从而实现蜕变。
《乡愁》
武满:完全同意。剧本想必也很好吧。
莲实:是的,这里如果笨拙地使用闪回,恐怕会变成雷乃《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st Year at Marienbad,1961)的翻版;但《乡愁》用克制的摄影,通过黑白与彩色的交错来叙述,这一点显得很沉稳——想必其间也有过犹豫和试错——能感觉到一种自身与想表达的事物相互重叠的惊异。同时代能有这样的作品,是一种幸福……
《乡愁》
武满:确实如此。
莲实:……也有一种自己没能拍出来的懊恼呢(笑)。
武满:色彩处理,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中也算是最成功的吧。
莲实:这次的影像和色彩,给人一种视野突然变得清晰的感觉,让人明白‘原来他是想做这样的事,却一直没能实现‘。开头字幕结束后,俯拍的长镜头里汽车驶来,静静地横穿画面,然后又从左侧进入……
《乡愁》
武满:真是非常出色的影像。影像和色彩都让我非常佩服,但与此同时,不是音乐,而是所谓的‘效果音‘的运用,极其精细缜密。
比如,访问多梅尼科那像废墟一样的家时,雨水积在塑料袋里垂着,或者排列着接雨滴的空罐子,那水滴声在一个镜头内移动,能让人感觉到微妙的呼吸,或者说,空间的褶皱也体现在声音里。
《乡愁》
我每次见到做音响工作的人都会说,那部电影你们一定要看,虽然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但它的‘声音效果‘实在做得太棒了。制作出那样的声音,是非常不容易的。
武满:电影接近尾声时,主人公回过一次罗马。那个罗马,总觉得不是我们认识的罗马。是个有点发霉似的、不可思议的罗马。比如说,看了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对希腊的印象会完全改变。
安哲·罗普洛斯《永恒和一日》(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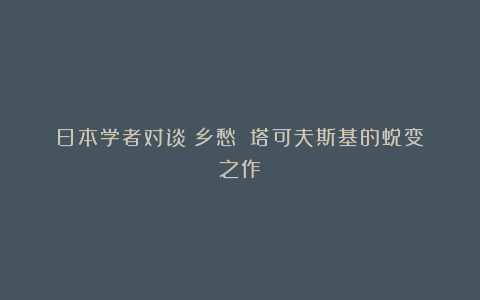
就像维姆·文德斯《美国朋友》(Der amerikanische Freund,1977)里的巴黎,和我们熟知的巴黎完全不同那样,我有种类似的冲击。您说这不只是‘声音效果‘的问题,确实,(这部电影)在那些无法用单纯视觉特效敷衍了事的地方,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比如当主人公即将出发时,来到一个像旅馆中庭、有着很长连拱廊的地方,服务生从对面走来。那个场景,绝不是只瞄准视觉效果就能做到的。
《乡愁》
武满:那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从黑暗中慢慢后退……那是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场景。
莲实:这正是电影化的空间与时间本身在直接地自我呈现。
武满:还有,我觉得人物布局的简练明了,是前所未有的。演员也是,特别是演多梅尼科的厄兰·约瑟夫森,虽然他也演过伯格曼的电影,但我觉得他在这部片子里比在伯格曼电影里要好得多。
厄兰·约瑟夫森(右一)在伯格曼《婚姻生活》(1973)
莲实:好得多。长靴的沉重感,以及逐渐疯癫的感觉,确实非常厉害。
武满:多梅尼科的关切是朝向外部世界的,而主人公安德烈,按他的说法是‘生病了‘,持续着由乡愁驱动的内心之旅。这两个人的相遇,使得他们之间,刚才提到的那些东西(的意味)显现出来。这里有一个非常动态的图式。
莲实:还有,那位女演员,多米齐亚娜·乔尔达诺,她那压倒性的魅力……
武满:真是一张像波提切利[4]画中的脸。而且她穿的衣服也非常棒。和电影的律动感很契合。
《乡愁》中的尤金伲亚(多米齐亚娜·乔尔达诺饰)
莲实:她那头丰盈头发的摇曳方式也非同一般。
武满:嗯,是位存在感很强的女演员。
莲实:另外,能让一位外国导演带着团队来拍出这样一部电影,意大利这个国家也真是了不起。
武满:是胃口大呢,还是包容力强呢。看制作人员名单,也都是鼎鼎大名的成员。
莲实:现在的意大利电影界,虽然没出什么了不起的导演,但在技术层面确实厉害。就说这位朱塞佩·兰奇(摄影师)吧,也是拍贝洛基奥电影的人,我虽然有意识地看他的作品这是第一次,但还是不禁感叹,怎么这样的人才层出不穷呢。
摄影师朱塞佩·兰奇
莲实:让人不由得高兴的是,这部电影确实有与自身严肃对决的认真劲儿,但同时,又有电影式的、某种通俗趣味的地方。
武满:对,没错。
莲实:比如说,多梅尼科在铜像上发表演说,企图自焚坠落,瞬间从画面消失,然后又爬着出现的那一段,就是一个光在脑子里想象绝对无法实现的复杂画面。
燃烧的多梅尼科
谁以什么方式藏在铜像阴影里啦,能看到在《特技替身》(The Stunt Man,1980)那种电影里也看不到的特技演员的精彩表现。那种通俗趣味,在他(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里是第一次出现吧?
武满:从这点上也感觉塔可夫斯基的格局变大了呢。有趣的地方也不少。比如多梅尼科在自己废弃的房间里,推开那扇毫无用处的门穿过去什么的(笑)。那场景让人想起德·西卡的《米兰的奇迹》(Miracolo a Milano,1951)。
《米兰的奇迹》
莲实:在通俗性这点上还有一处,就是把俄罗斯‘造‘在了意大利这个故事设定。实际上作为布景,也制作了俄罗斯的微缩模型。这某种意义上,和50年代以前的美国电影把世界上所有地方都‘造‘在好莱坞的做法非常相似。
好莱坞是以一种无比乐观主义的态度,不管是卡萨布兰卡还是哪里,都用露天布景搭出来;但《乡愁》的情况是,在已经无法再信仰那种乐观主义的情况下,却依然像变戏法一样,在意大利‘造‘出了俄罗斯。
《乡愁》
武满:原来如此。这么说来……
莲实:这么说来,我认为电影终究是进步了。虽然有人说电影已经完了,但一度死去的电影,现在是不是正以奇怪的形式开始复活了呢?
最后一个镜头,刚开始会疑惑这到底是怎么拍的,慢慢才明白是将俄罗斯风光以微缩模型的形式搭建在教堂内部,并且用只能认为是造假的方式在下雪,看到这里,我感到了电影史意义上的奇妙兴奋。
《乡愁》
在好莱坞那种能建造一切的乐观主义崩溃之后,电影的精神果然还是复苏了啊。这也是一种通俗趣味吧,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塔可夫斯基身上那种近乎冒险家的特质体现。
武满:当镜头后退,能看到全景的时候,相当令人兴奋。
莲实:虽然心里知道那是通俗的手法,但那里还是会兴奋起来(笑)。这种兴奋和拿着蜡烛行走时那种捏把汗的紧张不同,是一种即使对那段没兴奋的人也能理解的、更具包容力的力量。
莲实:我感觉,通过这部电影,塔可夫斯基或许第一次到达了这样一个创作境地:即将知性和感性分开考虑是愚蠢的。
以前他在空间性和时间性上策略稍弱,好像试图通过知性来寻求感性共鸣;而这部作品,则给人一种完全是依靠策略本身就拍出了电影的可信赖感觉。
武满:是一部甚至逼近安哲·罗普洛斯水平的电影呢。
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
莲实:那种氛围上的步步紧逼的感觉,甚至在看完电影之后还在持续涌来。但是,拍到了那个地步,不禁让人想他今后会怎么做呢。这虽然是合拍片,但已经既不是苏联电影,也不是意大利电影。这是一部超越国籍、值得全世界为之高兴的电影。
武满:嗯。我认为这是一部在电影史上也可能成为里程碑的作品。很有力量。以前总有些未能成功的文学性之类的东西,有点孱弱,但这次,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被果断地割舍了。
《乡愁》
莲实:迄今为止塔可夫斯基电影中存在的文学趣味,在这里,已经被干净利落地吸纳进电影本身而消失了。
武满:我也完全同意。
莲实:他是在以宇宙为对象进行工作啊。
武满:是啊。非常具有宇宙性。
《乡愁》
莲实:我觉得追求宇宙论意象的电影有很多,但这部作品,我认为是给出了一个关于电影如何抵达宇宙的答案。也就是说,不展现宇宙也能成为宇宙性的电影,不展现科学也能成为科幻。
这里呈现的绝望感、颓废,以及并非仅仅满足于绝望之中的、对艰难未来的摸索——乡愁绝不是沉溺于过去——这部电影的当下性得以用宇宙论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它既是电影史上的纪念碑,同时也是一部能直接作用于人类思想、促人反省的电影。
《乡愁》
不仅仅是电影爱好者,思想家也好科学家也罢,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坦率地为此片感到惊叹。我希望那些满足于二十世纪既有知识体系的人,能在这部电影面前产生动摇。
比如说,像美苏对立这样的政治前提是多么无聊,而现在出现了能够超越国籍、一举实现宇宙论翱翔的人,在持续刺激着我们——不要因为他流亡了就说苏联不行了之类的小家子气的想法——我认为,所有领域的人都应该坦率地惊叹于电影竟然能够抵达并撼动人们内心那些或许是当下文字所无法触及的地方。
《乡愁》
武满:对您说的深有同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做了一项真正伟大的工作。电影这种东西,拥有着一种能够驱策人类朝向超越单纯知性的、某种更宏大思考的力量。
莲实:这样的感性,现在的年轻女性们会如何接受呢?近来的‘艰深‘电影总感觉是男性主导吧。喜欢塔可夫斯基的女性也并非没有,但我希望她们能超越这种特定作者的名声,直接与电影交流,以自己未曾知晓的方式被动摇。不知为何,并非特定的某位女性,而是我在看《乡愁》时,强烈地意识到了与异性的交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