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没有哪类小说像中国古代章回小说这样,小说同诗词有如此亲密的关系,论部、论回,十之八九离不开诗词。
全书,有卷首诗或词,有终卷诗或词,章回,有回首诗或词,有回尾诗或词;叙述、描写、议论之中处处可插入诗或词。
看这样的小说,如果跳开这些诗词,无疑会给自己的欣赏留下憾意。因为不少的诗词不仅同情节、人物息息相关,有的本身就是情节,就是人物性格。
有不少的诗词作为通俗文学的有机体,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体与裁判体(小说者大多习惯冷眼观世),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意义重大。
一、章回小说与诗词关系中的文化渊源
章回小说最早的成果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
而历史演义小说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其体制虽有质的区别,但却是承袭话本而生演变。
话本和宝卷、鼓词、弹词一道,又是继承唐代“变文”而来。
“变文”作为唐代寺院向俗众宣讲佛经教义的“俗讲”的记录文字(底本),说白与唱词相辅相成。
今天我们看来,它不仅展示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佛教活动繁盛,也展现了当时说唱文艺的面貌。
在这些展示中,又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说与唱的结合形式正合乎民众文学艺术欣赏的需求,(白)文与(唱)词的“变文”体制便作为一种文学的体制样式流传下来。
由此可论:后来章回小说中的小说与诗词结合的体制源头,应在于此。
当然,也许此前还有更初的模式,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变文”中的“文”与“词”的比例是多少?从王重民等先生所编撰的《敦煌变文集》来看,不好“一刀切”而论。
《敦煌变文集》书封
《伍子胥变文》和《汉将王陵变》中的“文”“词”各占其半,相互交叉。《捉季布传文一卷》和《董永变文》几乎全是“词”。《唐太宗入冥记》(有缺)和《叶净能诗》(有缺)则几乎全是“文”。
而且,作为“底本”的“变文”,和尚在“俗讲”时完全可以增添。到宋元话本时,可见的是说白明显增多,已成为故事叙说形式的主体;唱词渐减,而且转以诗和词的形式为主体辅助手段。
我们看《清平山堂话本》和《京本通俗小说》中保存的宋元话本即可得知。《碾玉观音》中,“入话”部分以诗词为主,正文部分则以说白为主。
《董永遇仙传》以一首文言诗“入话“,正文以说白为主,中间仅穿插四首诗词。以诗词或唱词为主体的话本为数不多,如《张子房慕道记》和《快嘴李翠莲记》。
这说明,话本已注意到了故事的细腻描绘与叙述的生动的重要,注意到了说白更能够实现这种创作。
话本这一特征,说明了叙述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说明了当时人们审美欣赏的变化。
章回小说不仅是后来说话人的依据之一,更是阅读者的案头文字,“白文”在书中占绝对的优势已成为章回小说同说唱文学艺术的分野标志。
诗词在小说中的篇幅再次减缩,然而,也被创作者们用到最关键的位置之上。
这种安排,若用现代小说观来看,有的似乎多余,有的并不恰当,有的完全可用白文代替,但在当时,由于说唱文学欣赏与创作的传统惯性,这些诗词是说话人巧妙之处,听(读)者欣赏的必需环节。
正如《拍案惊奇·凡例》云:“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
“蒜酪”者,独特风味之调味品。缺之,淡而无味;加之,味增趣生。即从一般的文体特征而论,诗词的表现特征,并非全能由白文代替得了的,恰到好处的诗词之意境意趣,更不是白文能实现的。
这里所说的意境意趣,作为通俗文学,也当然包括那些引用俚词俗句、谚语歌词和打油诗、顺口溜、偈语的作品生发出来的艺术效果与深刻而又广泛的哲理和观念、心态。
比如《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所用以作回首诗的一首:
心安茅屋稳,性定菜羹香。
世味薄方好,人情淡最长。
因人成事业,避难遇豪强。
他日梁山泊,高名四海扬。
这首诗议论之中又切有关情节的叙述,是专就宋江刺配江州牢城而设。
前四句是由人生经验概括出来的,可谓是“格言”了。白文能代替吗?
后来,《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回“陈经济临清开大店,韩爱姐翠馆遇情郎”也用此诗置回首,前六句相差不大,后两句则改为:
今日峥嵘贵,他年身必殃。
全诗又用于陈经济得意忘形遭恶报之事,颇有深意。
《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又如《金瓶梅词话》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回首诗:
我做媒人实可能,全凭两腿走殷勤。
唇枪惯把鳏男配,舌剑能调烈女心。
利市花常头上带,喜筵饼锭袖中撑。
只有一件不堪处,半是成人半败人。
这种自报家门式的自我调侃具有浓厚的趣味,非得这种打油诗才能表现出来。一般说来,章回小说用诗词有如下几种动机:
一是提纲挈领,如书首、回首之诗词。
二是总结前文,如回尾、书尾之诗词。
三是引出下文,如回首、回尾之诗词。
四是起承转合,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的回首,回尾之诗词即是。
五是描写人物心理。
六是描摹人物外貌。
七是突出人物性格。
八是描景状物渲染气氛。
九是议论评判。
十是作为人物交际工具。
章回小说中的诗词并非作品的主体,但由于章回小说篇幅较长,多则百万字,少也有二三十万字,因此,诗词的总数还是不少的。
这样众多的诗词,或直接引用前人诗词(相异之处,可能是传抄刊刻讹误,也可能是撰写者引错),或集用若干诗人词家的句子,或引用俚语俗谚、格言警句,也有撰书人自己的创作。
有的诗词几经传用,竟成了多种小说的常用诗,有的作品只是根据情节不同略改一二而已。
所以我们往往会在几部小说中发现多首相差无几的诗词。这应是由民间传说加工成章回小说和书会才人、说书艺人撰著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
章回小说发展到清代,与诗词的关系在一些作品中发生了较大的演变。
诗词由原来的辅助性作用转变为叙述主体的有机组成,由作者的插入性转变为人物的表达性,由结构意义转变为情节意义。
《儒林外史》除第一回回首和书尾(见五十五回本)各用一词作议论外,不再用诗词作为结构和议论手段,少量的诗词也是由人物说出,是情节和人物的内容。
《红楼梦》则完全把诗词作为人物和情节的有机体,使诗词与小说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结合。
当然,还有部分章回小说,仍保持过去的用诗词作为结构与议论、描写的方法。
《古代白话小说中的诗词韵文研究》孙步忠 著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二、《金瓶梅词话》诗词文化特征
《金瓶梅词话》全书用诗词四百余首(曲和其他韵文不计),除少数几首诗词略显文雅,绝大多数无“雅”可言,尽是“俗”。
俗字俗词,俗语俗句,读起来通俗,理解下去也不困难,皆是俗情俗理俗事,有的简直俗到了“不可耐”的程度。
即使是谈禅论道,叙礼说仁,辨是明非,劝善戒恶,也都深入浅出,至于叙事抒情,描人写性,更是用百姓日用之事物、妇孺皆知之情理来打比方。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俗”之中,蕴含着比“雅”更广泛更深刻的文化意义。
在一个人口数千万(明代)乃至上亿(清代)的泱泱大国之中,还有什么比积淀在民众头脑中的观念更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现实的呢?还有什么比形成为百姓的心态更能展现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意蕴呢?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世情巨著,作者改用了在他前面已出现的演史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中曾用过的诗词,又创作了合乎自己作品的诗词,这些诗词与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一道,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剖面。
如小说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有一首《西江月》:
柔软立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
青史几场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巧安排,守分而今见在。
此词赞成的是人生在世应具柔软之性,莫使刚强之气,无争无竞,安分守己,一切听从命运安排。
这样一种人生观,实是几千年来,民众之生不如狗彘的历史归结。它积淀在民众心中,便构成了一种现实心态。
这种心态的外化,便是人的惰怠并导致社会的保守与停滞不前。这种心态当然不止在《金瓶梅》的世界里。
《水浒传》第七十九回“刘唐放火烧战船,宋江两败高太尉”中有同样的引用:
软弱安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
钝斧锤砖易碎,快刀劈水难开。但看发白齿牙衰,惟有舌根不坏。
这里以牙舌之比,十分生动,不过还有更早表明这种心态的人,南宋大词人辛弃疾一首《卜算子》将此心态夹于戏谑之中:
刚者不坚牢,柔底难摧挫。不信张开口角看,舌在牙先堕。
已阙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第三回“王婆定十件挨光计,西门庆茶房戏金莲”的回首诗是:
色不迷人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亏。
精神耗散容颜浅,骨髓焦枯气力微。
犯着奸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药难医。
古来饱暖生闲事,祸到头来总不知。
这首诗首联之意远不只在于反驳女色损财害命败家亡国之论,明代小说戏曲中常用这么两句: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这实是佛家修心养性说教在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结果,它强调的是人们自身的决定意义。
尾联所谓“古来饱暖生闲事”却是被中国各层人土都说烂了的“安贫守道”之论的诠释。
真可谓是中国人生定了的穷命饿运,尤其是芸芸民众,一生劳作,却难以饱暖。而统治者盘剥压榨和为了更长久的盘剥压榨,总不让民众饱暖。
穷困饥饿之时,口中常念“古来饱暖生闲事”是最好的“充饥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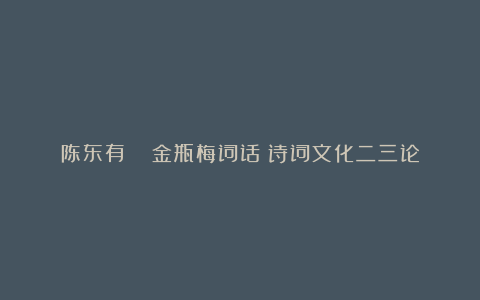
《金瓶梅诗词解析》孟昭连 著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月楼,狎客帮嫖丽春院”用的是这么一首诗于回首:
日坠西山月出东,百年光景似飘蓬。
点头才羡朱颜子,转眼翻为白头翁。
易老韵华休浪度,掀天富贵等云空。
不如且讨红裙趣,依翠偎红院宇中。
全诗的思想意趣可用“人生叹命短,何不秉烛游”来概括了,同刚才所讲的“色不迷人人自迷”观念相反,却是劝人尽情享乐,莫负春光。
无疑,这是生活在商镇、河埠、京都中那些商人富民的心态的反映,此类情趣的诗词还有:
紫陌春光好,红楼醉管弦。
人生能有几,不乐是徒然! (第十回)
归去只愁红日短,思乡犹恨马行迟。
世财红粉歌楼酒,谁为三般事不迷。(第十八回)
在《金瓶梅词话》的诗词中,与作者创作动机相一致,不少诗词将议论批判的矛头指向酒、色、财、气。
不过,这种批判具有以形象和情理论说的特征,有的来自于人们口头或历来传统的谚语成语或格言警句,有的则本身也形成了这样的形式,因此,从形式到内容都可发现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轨迹。
下列数首,权作一斑:
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
纣因妲己宗祀失,吴为西施社稷亡。
自爱青春行处乐,岂知红粉笑中殃。
西门贪恋金莲色,内失家麋外赶獐。(第四回)
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
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
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
邓通饥饿死,钱山何用哉!
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
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
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第七十九回)
人生切莫将英雄,术业精粗自不同。
猛虎尚然遭恶兽,毒蛇犹自怕蜈蚣。
七擒孟获恃诸葛,两困云长羡吕蒙。
珍重李安真智士,高飞逃出是非门。(第一百回)
有些诗词,就社会现实发出议论与感叹,反映出人情冷暖和社会凉热,其文化意义足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引起今人的共鸣与同感:
吃食少添盐醋,不是去处休去。
要人知重勤学,怕入知事莫做。(第十三回)
富贵自是富来投,利名还有利名忧。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第十四回)
巧厌多劳拙厌闲,善嫌懦弱恶嫌顽,富遭嫉妒贫遭辱,勤怕贪图俭怕悭;
触事不分皆笑拙,见机而作又疑奸:思量那件合人意?为人难做做人难!(第二十二回)
闲居慎句说无妨,才说无妨便有方。争先径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
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第二十六回)
人生虽未有十全,处事规模要放宽。
好事但看君子语,是非休听小人言。
但看世俗如幻戏,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与知音女娘们:莫将苦处认为甜。(第八十六回)
上面所举诸例,都是议论性的诗词,这类诗词在小说所用的诗词中占大多数。
小说中也用了一些描叙性的,有的同样揭示出文化的意蕴。
小说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的回首诗以第一人称自报家门的形式描绘媒婆(引诗见前文),不仅滑稽有趣,也叙说了当时当地的风俗民情。
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应伯爵替花勾使”回首诗是:
脉脉伤心只自言,好姻缘化恶姻缘。
回头恨骂章台柳,赧面羞看玉井莲。
只为春光轻易泄,遂教鸾凤等闲迁。
谁人为挽天河水,一洗前非共往愆?
诗意用来指西门庆此时的恍然醒悟,怨恨妓院无情,无颜再见一心为夫的妻子。展现出当时社会有妻室之男子在妓院受气之后的尴尬心态。
《金瓶梅词话》中有一部分诗词的“俗”到了“庸”的地步。比如全书百来处性行为描写,有不少是用诗词描摹男女情态和状写男女性器官的,可谓是“庸俗诗词”。
但如果把它们作为文化考察的对象,仍然可以发现传统文化中关于性和性行为的观念,揭示出当时人们的有关心态。
因为作者一旦把小说作品创作出来提供给社会,其意义就不止于作者一方面了,还有接受者,而通俗文学的接受者往往是相当广泛的,作者的创作动机和社会的需要相辅相成,就通俗文学来说,社会的需要往往是前提,是原因。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三、与《红楼梦》诗词之比较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关系十分密切,《红楼梦》的创作在很多方面受《金瓶梅》的影响,二者可谓是“木石前盟”(“梅”有木旁,《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又可谓是“金玉良缘”(《金瓶梅》之“金”与《红楼梦》中之“玉”)。
但是若论及诗词,二者有关系吗?正如前文所论,《红楼梦》的诗词由于全是作者个人的创作,又改变了过去章回小说中诗词的性质,把诗词同作品的人物、情节完美地结合起来。
于是我们看到,《红楼梦》中的诗词在文化层面上成了《金瓶梅》的相对面,皆是可登大雅之堂的“雅”品,非大家闺秀、才子文士不能写出,
可谓是字字珠玑,句句优雅,即使是凤姐这位斗大字识不得一箩的文盲,在“即景联句”时,以“一夜北风紧”开篇,被众姐妹称作为“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似俗却雅。
即使是那“跛足道人”的《好了歌》,通篇俗语俚词,也包含着无限雅韵,这才有甄士隐颇具夙慧的《好了歌》注解词,更何况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等才女才子们的《白海棠诗》、《菊花诗》,《柳絮词》,林黛玉的《葬花辞》,薛宝琴的《怀古七绝十首》等等。
文化分析的层面角度是多种多样的。若从人们生活的氛围来看,可分成“雅”层次和“俗”层次。
《金瓶梅》描写的对象是运河经济文化氛围中的市民商贾,即使是西门庆,虽然既是富商,又是中级官僚,但其本质仍然是一个市民商贾,只不过发了财、走了运而已。诸如应伯爵、常时节、韩道国等人,更是下层市民了。
《金瓶梅》又是写给俗民百姓看和听的,它的创作本身,便是市民生活的一种需要,所有的一切,都尽可能“随俗”,而不必故作高雅,也不可能去附庸风雅。
“一书俗气”(“俗气”二字排除贬意)是对来自于俗文化层次又为俗文化层次所欢迎的《金瓶梅》艺术特征的最好概括,其所用诗词当然在内。
《红楼梦》则不同,它描写的对象是封建皇亲国戚大家贵族中的公子小姐、老爷夫人。
这是以“高尚”、“优雅”(时代伦理道德标准)生活为特征的人物,即使是不安分的少男少女,比如贾宝玉,这位从不愿正经看书作文的“混世魔王”,也有着一种“雅”的文化氛围——书香门第、文人墨客、才情极丰的姊妹。
而“俗不可耐”的“呆霸王”薛蟠在酒宴上的谈吐和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的乡音俗语只能成为周围人的笑料。
《红楼梦》并不是写给普通俗民百姓看的,否则,作者不会化那么大的脑筋设计一通“假语村言”而将“真事隐去”。
它的读者应该是有中等以上文化知识的读书人,否则,作者丰厚的才情、高雅的意趣、特殊的痴味、荒唐的辛酸将是对牛弹琴。
作者在艺术上又有着如同今日我们论之的探索性创作意图,决无返俚随俗之为。
所有这一切,都可标上一个“雅”字。
这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两部作品中的诗词雅俗之别的关系了。但是,二者又有联系。
这种联系至少是在创作构思上,《红楼梦》受到了《金瓶梅》的启发。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应是受《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潘金莲兰汤午战”中吴神仙为西门庆及其一妻五妾、女儿、春梅相命后说的断语诗的影响而构思的。
它们都隐含着人物将来的命运归宿,都借助一种令人不可捉摸的力量。
只不过,曹雪芹借太虚幻境和警幻仙姑之口,“兰陵笑笑生”则是请出了一位铁口相命先生,前者从表现形式到内容皆雅,后者则俗;前者含蓄,颇费咀嚼,后者浅显,易解易懂。
文化层面的雅俗不好用“好”与“坏”来鉴定评比,因为二者都是文化的合成因素,都是一定的文化相辅相成相较相生的两个方面,俗中有雅,雅中有俗。
更何况文学艺术不宜以好坏判之,只可以工拙议之;文化也不能以好坏判之,只可以先后论之。
《金瓶梅》中的诗词因初创之始及描写对象和读者群的种种原因显得粗拙,《红楼梦》诗词则因后续成熟及描写对象、读者群、作者水平和创作意图种种原因更为工巧别致。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俗”,才使得人数更多的接受者有了可接受的审美对象;正是因为有了俗的粗拙,才有发展成工巧成熟的可能。
《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增订本)陈东有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附 记:
上述几点看法是两年来研究《金瓶梅词话》诗词的体会中的一部分,欲作为《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一书的序文,以请教大方。
一九九〇年二月,在南京开完“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之后,有幸同林辰先生同车去上海,又同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创作楼。
林先生爱喝酒,我爱喝茶,酒茶之间,林先生对我的研究给予了鼓励和指导。
五月,我又去北京拜访王利器先生,向他请教有关古代小说与诗词关系问题并请求《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一书序文。
王先生不吝赐教。六月,王先生又将他的研究心血写成短文,赐寄给我,作为序文。
恩师罗元诰先生也慷慨赐序,给我以热情的鼓励。
这都是令我难以忘怀的,谨此深表谢意。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本文作者 陈东有 教授
文章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原文为陈东有著《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代自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