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丧父、靠庶母纺线活命,穷得只剩一支笔,竟一路写到直隶总督,却在民国成立当天关门写旧诗——陈夔龙这命,到底算赢还是输?
1948年8月17日,上海法租界一栋老洋房里,91岁的老爷子把笔搁在《花近楼诗存》最后一页,咳了两声,对厨子说“今天不煮粥了”,躺下就再没醒。床头还摊着一张没写完的小楷:“宣统三十七年……”那年,其实早就叫民国三十七年了。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我头一回听这名字,是去年在杭州南山坡闲逛,看一块修得过分精致的墓碑,旁边导游对一群穿汉服的妹子喊:“这是西湖新十五景,清朝最后一个总督,大诗人!”我心里翻白眼:总督?怎么不课本里见。回来翻资料,越翻越像看爽文反转:穷孩子→进士→封疆大吏→亡国→躲进租界写诗→复辟失败→混成文化地标。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裂缝上,咔咔作响。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他起点低到尘埃。贵阳老宅是租的,父亲早亡,庶母姜氏靠纺线供他读书,夜里怕费油,就借月光背书。1875年乡试中举,1886年进士,同届里有康有为。别人搞维新,他守旧;别人要废科举,他写折子哭谏:八股若亡,人心必散。慈禧看完只批仨字——“知道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他任顺天府尹,城门楼子被轰烂,别人跑,他凑钱、募工、自己监工,三个月把正阳门修好,顺带把使馆区洋人的屎尿也安排人清走。上边夸他“能干”,下边骂他“汉奸”,他统统折起来塞袖筒,回家继续写“同光体”小哀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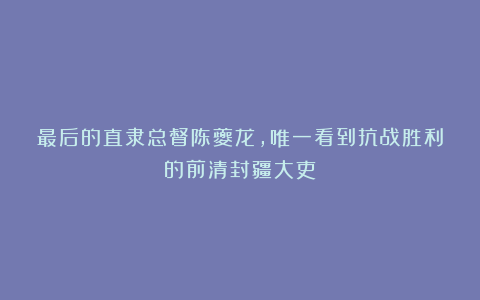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1909年,他52岁,升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人管半个北中国,人生顶流。可顶流才两年,武昌枪响。他上折子称病,把总督大印往桌上一扣,溜了。上海租界里置洋房,门口挂“庸庵”俩字,翻译过来就是——废宅。废宅每天干的事:抄古书、印贵州乡贤残稿、请客吃腊肉饭、听京戏。有人拉他去民国政府当官,给月薪八百大洋,他笑说:“我一条辫子在,脑袋去不了。”1917年张勋复辟,他连夜剃胡子进京,被封弼德院顾问,结果复辟12天散伙,他又把胡子留起来,继续当遗老。遗老们组“逸社”,轮流做东,酒令必须押“平水韵”,输的人掏钱给溥仪汇生活费。这一掏就掏到1945年,溥仪早成伪满傀儡,他们还在上海弄堂里凑份子。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我算过账:他后半生零收入,全靠前半任上攒的养廉银、卖字、卖收藏。最阔时,一副对联能换二十袋洋面粉;最惨时,家里厨子偷腊肉去黑市换香烟。可他把钱撒得心甘情愿:印郑珍诗集倒贴三千两;修杭州祖坟花掉五根金条;给落魄翰林买药煎人参,眼都不眨。有人骂他败家,他说:“银钱生不带来,诗卷可死而同穴。”后来果然,陪葬就一套《梦蕉亭杂记》手稿,别的全被子孙抵债。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1949年后,他坟被铲平,碑当台阶石;2005年西湖景区翻新,又把他请回来,描金描玉,成打卡点。导游词里说他“民族诗人”,没人提他反对废科举、反对共和。历史像抹腻子,一刮一涂,光滑得能照镜子。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可我还是觉得,这老头活得像一面裂缝镜子,照见读书人的软和硬:软在不肯剪辫子,硬在给家乡印书砸锅卖铁;软在复辟做梦,硬在穷也不给日本人写字。他知道自己可笑,临终诗里写“庸庵负手看残棋”,一句负手,把尴尬全揽怀里。棋输了,人散了,他还在原地整理棋子,怕乱了图谱。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今天,我们人人喊“上岸”,他却主动跳船,抱着一块叫“旧世界”的木板,在新浪潮里漂成孤岛。岛很小,却足够放下一张书桌、一盏油灯、一条不肯剪的辫子。值不值?他懒得回答,只把问题留给后来人:你敢为一句“我喜欢”穷一辈子吗?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