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左海军副研究员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钱庄的汇划体系逐步取代票号的汇兑体系,是近代中国钱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金融结构演变的重要内容之一。明清以来,中国钱业的核心业务,先后经历了货币兑换、存放款、汇兑、信用发行等发展阶段。在不同历史阶段,钱业发挥的主要金融功能,取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结构复杂程度。开埠以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钱业的金融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各项金融功能融合互补,从而为工商业提供更高效的资金融通和结算服务。与票号相比,近代钱庄体系具有更复杂的经济网络,庄票等信用票据在商业往来中被广泛接受,以汇划制度为核心构建了多层次的结算体系,这些优势使钱庄以转账、划拨为基础广泛参与贸易结算。清末民初,钱庄逐步取代票号是钱业内部核心金融功能与制度的迭代发展,在本质上最终体现为融资方式、融资效率的差异。
关键词
钱庄;票号;信用发行;汇划结算;金融功能;迭代发展
钱庄是中国传统金融业研究中的重要话题。钱庄起源于明中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才逐步退出市场。钱庄既存在于进出口贸易发达的上海,也广泛分布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万千村镇。在业务上,近代各地钱庄大致均以“存、放、汇”为基础,但是由于所处市场层级不同,以及在获利方式上存在差异,各类钱庄在形态、业务以及制度上又存在显著区别。近代钱庄自身的复杂性,导致对其进行定性研究的难度较大。因此,如何认识与理解近代中国传统金融业的发展,成为学术界关心的重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洪葭管、黄鉴晖、张国辉等围绕票号、钱庄资本属于“货币经营资本”还是“借贷资本”的问题开展了较为系统的讨论。此外,学界还从推动进出口贸易发展的角度讨论了钱庄的“买办性”与“民族资本主义性质”。近代钱庄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郑亦芳认为近代上海钱庄的性质与现代商业银行类似,与国家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票号。马俊亚、戴鞍钢、朱荫贵等学者的研究证明了钱庄在促进贸易发展,开拓国内外市场,以及早期工业化发展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整体来看,学界对近代钱庄的认识仍有局限。其一,对钱庄发展持肯定意见者,主要着眼于钱庄在贸易往来中的积极作用,而对中国传统金融业自身的发展演变关注较少。其二,部分观点对钱庄的评价较低,认为钱庄“规模小”“不设分号”,是“旧式”“地方性”的信用机构,其金融功能弱于票号。其三,学界对中国近代金融转型的研究,更重视银行的影响,对中国传统金融业自身的发展关注不够。
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中国传统金融业的业务、结构、功能必然有所调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金融结构中不但引入了银行制度,传统金融业也完成了从票号“汇兑体系”到钱庄“汇划体系”的新陈代谢。钱庄不但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且根据不同的金融需求发展出各类细分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关系的货币化、信用化。晚清至民国时期,钱庄业的金融功能逐渐完备,兑换、存款、放款、汇兑等已经成为基础业务,同时还发行银钱贴、庄票为商业往来提供交易媒介,组织汇划公所便于同业票据交换,钱业公会附设各类专业金融市场以满足市场资金融通、投机获利、套期保值等深层次金融需求。本文仅侧重讨论近代钱庄的核心金融制度创新——信用发行与汇划结算,以管窥近代中国钱业金融功能的发展。
杨端六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一、中国钱业发展与金融功能演进
钱庄起源于明代中叶,据史料记载,其名称除“钱庄”外,还有“钱铺”“钱肆”“兑店”等。明代,钱庄的主要业务是经营制钱、私钱与白银之间的兑换。银钱兑换的活动早就存在,但是钱铺的出现,使银钱兑换成为由商人专门经营的一种生意。唐代的金融机构,如抵店、柜坊等,其业务庞杂,侧重钱财的存放及保管。宋代,柜坊因多与赌博有关而屡遭禁止。明代出现了专业钱商,这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中是一次重要进步。明正统年间,大明宝钞信用下降,取消用银禁令,银钱公开合法流通之后,货币兑换作为一种金融业务获得持续发展。明代钱商经营银钱兑换业务已经产生较大影响。嘉靖六年(1527)十二月,户部尚书邹文盛奏言钱法时,明确提出严禁私贩铜钱。嘉靖十五年有人再提严禁豪商巨贾私贩铜钱,导致当时“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货翔踊,其禁遂弛”。为了对抗官府的不利政策,经营银钱兑换的豪商富贾有意识地控制市面银根松紧,操纵物价,借以要挟,最终导致政府的禁令废止。这说明当时银钱兑换业颇具规模,而且与社会商品流通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密。明中后期至清初,作为货币经营业的钱庄还发展出一系列的技术性业务,比如白银成色的鉴定与重量的称量,成串铜钱的整理与拆分等;部分银铺、银楼也从首饰加工与零售等活动,开始转向为官府倾销税银。整体来看,直到明末清初,货币经营性业务是钱庄经营的重点,其金融功能尚较为简单。
明末,在货币兑换的基础上,钱庄率先发展出放款业务。彭信威对明末钱庄放款业务的出现评价很高:“到了(明朝)末年,钱庄已成为一种近代的金融机构,不但可以兑换铜钱和金银,而且积极地揽作放款,对顾客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钱庄放款业务具体始于何时,很难考证,但是一般而言,频繁发生的货币兑换活动,容易使钱庄与客户之间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客户偶有支绌,钱庄代为垫款,符合常理,因此钱商逐渐将放款取息发展为一种重要的获利方式。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明末清初钱庄的放款业务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放款对象更青睐有特殊身份的个人,如被政府铨选的官员;放款时所获得的高额利息,又使这些放款从属于高利贷的范畴。以明末为历史背景的《醒世姻缘传》记载:山东武城县秀才晁思孝选了华亭县,身份的变化使钱铺对其态度发生根本扭转,“昔日向钱铺赊一二百文,千难万难”,晁秀才选了华亭县之后“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指望他使银子,只要一分利钱,本银足色纹银,广法大秤称兑”。这些铨选官员借“京债”赴任的情况在唐宋时期已经非常普遍,但是当时参与放京债的人员主要是“富户”或者“豪僧”。到了明代,出现了一个较为显著的变化,即作为金融机构的钱庄开始参与放京债。高额的利息负担虽然影响吏治清明,但是京债的出现,使放款取息被纳入钱商的业务视野,成为中国传统金融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
清中期,账局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放京债。账局起源于中国北方的北京、张家口和山西汾州、太原府等地。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为乾隆之前或雍正、乾隆之交,早期开展放款业务可能与山西商人参与中俄贸易有关。但是,京债的经营对账局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乾隆年间,钱商放京债的活动影响很大,已经为统治者所注意并要求严禁。乾隆二十三年(1758)御史史茂上奏说:“月选各官,借贷赴任。放债之人乘隙居奇,创立短票名色,七扣八扣,辗转盘利,请严行禁止。”京债息重,影响吏治,遭到清政府禁止。但是,京债作为一种借贷业务,推动了金融机构的发展。乾隆时人赵翼的《陔余丛考》记载:“至近代京债之例,富人挟赀(资)住京师,遇月选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远近,缺之丰啬,或七八十两作百两,谓之’扣头’,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此处“放债之人”“富人”虽未明言是账局,但是从业务形式来看却与账局高度一致。乾隆时人李燧在《晋游日记》中记载:“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赀(资)入都,开设账局。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如九扣,则名曰一千,实九百也。以缺之远近,定扣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复加月利三分。以母权子,三月后则子又生子矣。滚利叠算,以数百金,未几而积至盈万。”可见,针对具有特殊融资需要的个人开展高息放款,是账局发展早期的重要业务内容之一。
赵冀著《陔余丛考》
与明末的钱庄不同,清中期账局在京债之外,还广泛拓展对工商业的放款,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金融业的缓慢发展。明清时期的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同时也因为人口众多,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商业规模的扩大,使商人自有资本出现严重不足,遂产生融资需求。据王茂荫记载,咸丰三年(1853)北京“盖各行店铺自本者,十不一二,全恃借贷流通。若竟借贷不通,即成束手,必致纷纷歇业,实为可虑”,“而借贷日紧,则由银钱帐(账)局”之款收而不放。当时北京的账局规模很大,“各行帐(账)局之帮伙,统计不下万人”。账局对工商业的放款在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账局款项的收放,足以影响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咸丰初年,受时局影响北京经济状况不佳,各行生意日微,市面银根日紧。王茂荫认为影响市面金融的主要原因是“(账局)各财东自上年(1852年)以来立意收本,但有还者,只进不出,以致各行生意不能转动”。账局的放款形式较为简单,王茂荫对此有详细描述:“闻帐(账)局自来借贷,多一年为期。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奇,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帐(账)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这段史料说明账局的放款存在以下特征:其一,放款取息是账局的主要获利方式,且所放款货币为现银;其二,账局放款侧重在时间上融通资金,且放款周期较长,多以一年为期;其三,账局尚未系统开展汇兑业务,因为借者要将现银本利措齐送到局中;其四,账局尚未发展到通过发行“纸币”或使用票据来扩张信用。虽然如此,账局开展的商业放款与经营高利贷性质的京债相比,仍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票号的汇兑业务,是清中后期中国传统金融业发展中又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票号诞生于道光初年,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正式以汇兑为专营业务的山西票号。票号发展的基础是明清以来日益扩大的埠际贸易。商品的长途贩运,使不同地区之间产生了大量债务清算和资金平衡的需求。起镖运现风险大、成本高、效率低,已经不能适应日趋频繁的异地债务清算需要,汇兑显然比运现更具优势。汇兑的原理并不复杂,唐代的“飞钱”与宋代的“便换”本质上都是汇兑,明清时期商人之间也普遍使用“会票”结算货款。但是,票号的出现本身意义重大,说明汇兑作为一种金融功能,已经能够独立支撑一个新的金融行业。票号一经创立,就获得了迅速发展,汇票的使用改变了贸易往来中钱款的结算方式。江苏巡抚陶澍在道光八年(1828)四月初八日奏章中说:“苏城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借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甘等处,每年来苏置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与市廛钱价相平,商民称便。近年,各省商货未能流通,来者日少,银价增长,然每银一两亦不过值钱一千一百六十七文至(一千)二百余文不等。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俱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银运到。因此银价顿长,钱价愈贱。”可见,道光八年的苏州正在经历汇兑业务发展带来的变化,各地商人以汇兑方式结算货款,明显影响了苏州白银的流入,造成银贵钱贱的价格波动。
陶澍像
明清时期,中国钱业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兑换、存放、汇兑等各项金融功能不断发展完善,并且相继在不同历史阶段展现出主导地位,钱铺、账局、票号的本质是各阶段主体金融功能的有形外化。近代开埠以后,随着贸易的发展,商业活动中对支付结算的效率与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信用活动的发展,使付款人与收款人之间的中介机构变得更加重要,商业结算成为金融机构重要业务方向。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商业结算需要,中国传统金融业的各项金融功能出现了融合发展的趋势。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各大商埠的钱庄均获得显著发展,其业务更加复杂,金融功能更加完善。钱庄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金融业数百年发展而来的兑换、存放、汇兑等基本功能,还凭借自身信用发行银钱贴、庄票,为社会经济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交易媒介,扩大了商业资金来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转账、汇划形成了非现金结算体系。信用发行与票据交换的结合,是推动钱庄成为商业结算中枢的关键性金融制度创新。近代钱庄行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商业结算体系,其中包括作为记账、清账、结账机构的钱庄自身,包括以庄票、汇票为核心的结算工具,也包括庄内过账、同城票据交换、埠际期票买卖等多层次结算网络。钱庄的汇划体系代替票号的汇兑体系,本质上是商业结算机制的迭代发展。
张国辉著《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二、近代钱庄发展与结算中枢地位的形成
清中期前后是钱庄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存放款业务为基础,钱庄开始与商业活动接近,进而发行银钱贴用于市面流通。过账和票据交换的活动也相继出现,一些信用卓著的大钱庄开始通过发行庄票辅助商业结算。当票号的汇兑业务如火如荼之时,钱庄凭借在商业结算中的金融创新逐步扩大影响。与账局、票号相比,钱庄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且创造性地将信用发行与票据交换结合在一起开展商业结算,在适应近代经济发展方面,钱庄的汇划活动比票号的汇兑业务更具发展潜力。
近代钱庄的发展首先体现为数量众多,广泛分布于通商口岸、区域中枢城市以及县域城镇。这一点与账局、票号均有不同。账局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其中以山西晋商开设为主,业务上主要经营信用放款,设立分号的情况较少。票号较账局更为进步,分号的开设逐步打破地域限制,经济发达与否,成为票号延展网络覆盖的决定因素。19世纪后半期,山西票号发展步入黄金时期,分支机构遍及全国,票号的字号最多时为30余家,总、分号总数约为500余家,分布于全国95个城镇。国内偏远地区以及国外的重要城市,票号的汇兑业务均可达到。对外通商口岸城市,由于经济发达,为票号所重视,1875年上海有票号24家,数年之后增加到40家。1881年,仅汉口一地就有票号32家。账局、票号的分布不可谓不广,但是和钱庄的数量、密度以及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黄鉴晖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近代钱庄的精确数字统计难度较大,现存文献多为估计数值。1924年6月,民国政府农商部发表《第九次农商统计表》,其中对1912年—1920年的全国钱庄进行了统计。据载,1912年至1920年九年间全国官钱局、银号、钱庄、其他四项合计,其总数分别为4 611家、4 761家、4 589家、4 470家、3 585家、3 538家、3 377家、2 939家、2 300家。其中,1920年的分省统计,2 300家钱庄分布于312个县域城镇。从区域范围来看,各主要省份、城市、县治及重要城镇均有钱庄分布。1933年,据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记载,安徽等12省份规模较大的钱庄总数为1 121家,察哈尔、绥远16家,东三省111家,香港22家,全国总计1 270家,实收资本约6 710.3万元。1934年,安徽等14省合计1 158家,绥远20家,东三省84家,全国总计1 262家,实收资本约7 750.2万元。据《全国银行年鉴(1935)》统计,江苏、浙江、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河北、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绥远、东三省所属的101个主要城市共有钱庄1 264家。以上这些统计偏重于城市中的钱庄数据。刘克祥对20世纪初全国农村钱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在其所有调查的1 061县中,630县有钱庄,即全国接近60%的县开设有钱庄。其中,大部分省区50%以上的县设有钱庄,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商业活跃省份有钱庄的县占总数的80%以上,其中江苏、山东,山西更超过90%;福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7省,有钱庄的县占50%—60%左右;其他省份有钱庄的县则在50%以下;云南、贵州、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钱庄的分布则较少。这些数字虽然都属于不完全统计,但是大体上也能反映出钱庄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各级城镇的事实。
《中国近代金融史》
其次,钱庄的发展还表现为类型多样,在业务上出现了各类细分市场。晚清民国时期,各主要商埠的钱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经营货币兑换门市钱庄;其二,经营存、放、汇的汇划钱庄;其三,经营各类证券、贵金属、期货的投资钱庄。其中,汇划钱庄的数量和资本额在各埠钱业中所占比例最大,经营最为稳健,在各埠钱业中具有主体地位。上海钱庄按照是否参加钱业公会分为“大同行”与“小同行”。“大同行”钱庄亦称“入园者”或“汇划庄”,一般资本较为雄厚,经营范围较广,互通汇划,同业收解不用现金,概在汇划总会转账。“小同行”钱庄资本较汇划庄薄弱,经营范围也不如汇划庄。“小同行”钱庄按其业务规模之大小,又分为“元”“亨”“利”“贞”四类。汉口钱庄分为“门面”与“字号”,“字号”钱庄资本雄厚,不营小宗存放款及兑换业务,依托信用作大宗交易,且不设门面于闹市或正街,俗称“巷子钱铺”;“门面”钱庄则恰与之相反。此外,长江流域的杭州、南京、南昌、景德镇、九江等地,钱庄等级也大体分为汇划钱庄、钱店、兑换店等三类。天津银号主要分为“折交”“现事”“门市”三类。“小规模的是门市,大规模的是内局”,内局银号作折交即主要经营商号及外客存放款,“现事”即买卖公债、老头、足金、关金,门市钱庄则主营货币兑换及买卖外省票、残洋,卖马票等。北京银号在业务上分为专营存放汇兑、主营有价证券兼存放、专营兑换银钱及买卖外国货币三类。福州钱庄分为出票店、钱样店和排钱桌三种。其中出票店的性质相当于上海的汇划钱庄。厦门的钱庄分为甲、乙、丙三种等级。甲等钱庄拥有雄厚的资本,营业地点设于楼上,主要经营上海、香港等处之汇兑及存放款。乙等钱庄资本相对较少,除经营汇兑及存放款外,还兼营外国货币、黄金、银元之买卖。丙等钱庄资本微弱,一般仅数百元,系专营门市兑换业务。汕头的钱业主要分为汇兑庄、收找业。汇兑庄主要经营香港、上海及汕头本地的汇票买卖。收找业的营业范围有找换铜钱、铜仙、毫银、毫券、银元、大洋、纸票、各港货币、公债票券、已倒闭庄号纸币、次银和旧金等,还经营当地或外港汇兑,或发行七兑票、保证纸等纸币。1920年,汕头收找业的投资已不亚于汇兑庄,因此正式成立银业公所。银业公所与汇兑公所成为并驾齐驱的两个钱商组织。可见,近代各埠钱庄逐渐出现了细分市场,且钱业内部结构趋同,反映出近代各埠钱业在金融功能上的进一步发展成熟。民国时期,学界对钱庄的细分市场已有认识。1936年,王子建、赵履谦在讨论天津银号时提及正式银号与门市钱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严格言之,银钱号不属于银号范围,因两者之间并不发生金融上之联系,且前者在系统上属于兑换业同业公会,与后者之属于钱业公会者,截然二事也。”
其三,近代钱庄对中国金融制度发展的核心贡献是结算方式的创新。与票号的汇兑不同,钱庄辅助商业结算活动的核心制度是信用发行与票据交换,这一点在清中期已经初现端倪。清乾嘉时期,中国钱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与票号源于晋商资本不同,清中期前后,各埠本地资金组织的钱庄开始获得新的发展。这些钱庄与本地商业极为熟稔,广泛开展针对本地商人的存放款业务,并以自身信用为基础发行银钱贴用于市场流通。这是因为日益扩大的商品交易,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提供更多安全且便于流通的交易筹码,以弥补市场流通中现金的不足。过账银、银钱贴,以及后期的庄票,本质上都是以钱庄信用为担保的交易媒介。这些交易媒介具有彼此方便冲销的特性,这是大规模贸易结算的必然要求。就目前研究来看,清中期以后,宁波、上海、营口等商业繁盛之地相继出现了“过账”“汇划”“抹兑”等信用结算制度。钱庄的核心功能开始转变为商业结算活动的机构载体,参与商业结算的记账、算账、结账等活动。按照钱业惯例,每年开市之初,钱庄照例将存折送交与其素有往来的商家。钱庄与商家之间开写庄票、代收汇票、支票等都以此活期账户为基础。为了便于记账和清算,各地先后发展出了区域性货币——虚银两。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上海的规元银、汉口的洋例银、天津的行化银、营口的过炉银等。与此类似,在很多内陆重要商埠也出现了用于记账的标准银,如盖平的抹银、沈阳的抹兑银、锦州的抹兑银、芜湖的拨账银、张家口的拨兑银、沙市的拨兑银、山东周村的拨账银、山东龙山的抹账银、芝罘(烟台)的拨兑银、宁波的过账银等。实际流通中的银两、银元需要按一定比例折算成标准银,以进行登账和拨兑活动。以过账的方式辅助商业结算,使钱庄获得迅速发展。据秦润卿记述,乾嘉时期上海南北贸易往来繁盛,“其货款交割,概用九八豆规银为之。厥后全市通行九八豆规银,遂成上海一埠之记帐(账)本位币,而钱庄即为九八豆规银收解之总汇”,“上海之规银筹码,完全握于钱业之手”。1858年,上海城内和租界地区约有钱庄120家,其中约有70家较大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织品等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给与资金周转的便利。汉口钱庄的主要业务也经历了由兑换到存放,再到商业收交的转变过程。“最初汉埠工商业尚在发轫之时,需要金融调剂者甚少。故钱庄初创,规模极简。在光绪初年,仅有浙绍帮同字号十家左右,他若江西帮、徽帮、汉帮约有小钱铺二三十家,其营业专以兑换为主,代各商号兑换生银制钱,借以维持,徐图发展。迨工商业日趋进步,虽有票号之设立,然其职务,专司汇兑,对于工商业之调剂,每难兼顾。遂有吉安帮大钱庄七八家代兴,办理各大商号收交事务,以补票庄之不足。更因票号之殂落,汇兑将有停滞之虑,而同时出进口商业,日臻兴旺,钱业更大肆活动,兼办汇兑,营业发达,愈加迅速。故浙江、江西巨商,纷纷组织大规模钱庄,几继票号而为汉埠金融界之盟主。民国十一年时,竟多至百五十二家,是乃钱业之黄金时代也”。可见,清末汉口大钱庄已经具备接替票号办理各项商业结算业务。天津银号的发展路径与上海、汉口类似,经营存、放、汇为主要业务的“西街银号”在行业中占主要地位。西街银号资本较为雄厚,在业务经营上侧重存放款、汇兑、贴现、收兑白银、代客办理收交申汇和买卖银元等业务,经营风格稳健,不做投机性的业外经营,市面上称为“做架子”或“折交”。此类银号以“做架子”标榜其业务扎实,自诩殷实可靠、作风正派。折交银号与本地商人极为接近,营业稳健,在天津钱业中的势力较大,钱业公会历届会长多由西街银号中选任,如朱馀斋、张云峰、王晓岩、焦世卿、范雅林、王西铭等都出自西街银号。1931年,《中央银行旬报》刊载了对天津银号的业务统计,其中业务为存放的银号有16家;存放兼营汇兑的有28家(其中存放兼申津汇兑的有21家);存放兼营实业的有5家;存放兼营“现事”业务的有7家;存放、汇兑兼营“现事”的有1家;存放兼兑换的1家;“现事”、门市兑换兼少量存放的2家;“现事”业务兼营实业的有1家。这些数据表明,近代在上海、汉口、天津等重要口岸城市以及内陆的商业枢纽,以经营存、放、汇为主要业务的汇划钱庄已经占据优势地位,其主要功能定位是辅助商业结算。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
三、以庄票为核心的结算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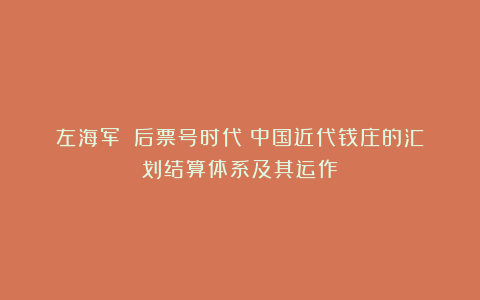
庄票,是近代钱庄为便利商业往来而发行的一种商业票据。潘子豪认为,“庄票为钱庄所出之凭券,允许到期兑款于持票人之票据”。从形制与发出方式角度看,杨荫溥提出“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从票据性质角度论,魏友棐指出“庄票者,钱庄以自己名义不附条件约付之票据也,故其性质同于本票。又以凭票付款,不载受款人姓名,其性质又同于银行兑换券”。根本上来说,庄票就是以钱庄信用为基础的商业票据。与银行兑换券主要用于市场流通不同,庄票则侧重商业支付,其主要运用方式是转账。与票号的汇票相比,与钱庄信用紧密联系是庄票的主要特征。
票号的汇兑业务,多数是以现银收交,形式上以顺汇为主。道光二十七年,蔚泰厚苏州分号收会银211 793两,交会银314 192两;道光三十年,日新中京都分号收会银607 460两,交会银425 721两。票号收汇与交汇的数额较为接近,说明其汇兑业务多数为现银收交。此外,因各地商情不同,收交有时难以平衡,为平衡两地资金,票号非常重视“抽疲转快”,通过汇水的调整平衡各地分号的存银数量。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日升昌总号给汉口分号第六十四次信中写道:“再,至广东交之票,往后无论何处,俱要竭力收会,皆因彼处收项极多,交项稀少;且彼为了交项,收会别处之项甚为有利。”这些都说明票号的汇兑业务中存在大量的现收、现交的情况。相较于异地运现,汇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贸易的结算效率,表现为既提高了资金流动速度,也降低了资金运送成本。但是,不得不承认是票号汇兑仍存在不足。其一,多数情况下,商人要提前准备好现金,才能从票号开立汇票,票号对一般商人的信用支持较为有限;其二,汇票或号信通过民信局送达,仍需视道路远近耗费不等时日;其三,汇票如为迟期,多数需到期才能取款;其四,票号各分号之间收交差额,尚需依赖总号统一结算,收交平衡问题影响资金运用决策。整体来看,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仍有不足。
孔祥毅、王森主编《山西票号研究》
与票号的汇票相比,钱庄庄票最显著的特征是依靠信用发行。一般而言,流通中的庄票数额要远超钱庄的现金储备,甚至超过钱庄的资本总额。庄票的使用方式主要是转账而不是取现,钱庄间通过票据交换完成清算。
庄票起源于早期银钱贴,其所具有的信用特征是由中国传统商业发展的内驱力逐步塑造形成。中国民间私帖的确切起源难以考订,但是至迟在明代已经出现以私人信用为基础,以白银或制钱为本位的私帖,分为“银帖”与“钱帖”。与政府发行的官票、宝钞不同,民间私帖不依赖官府行政强制力推行,而是依靠商人的私人信用维持运转。明清时期,民间私帖主要是由信用卓著的钱庄、银号、典当以及各行商号发行,多在本地流通,大多数见票即兑,部分“期票”需订期兑现。私帖最初大致是钱铺、商号为了便利与其有经济往来的客商取款或提货,而发出的具有收据性质的纸票。由于信用卓著,在市面辗转流通,因此具有了货币的性质。早期民间发行私帖,主要是为了解决金属铸币的携带方便与安全问题,由于兑现准备充足,其性质属于代用货币。到清代,中国部分地区甚至长期以竹签代替银钱。
伴随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商品交易总量增加,金属货币供给不足问题日益突显,商人遂以资产或商品作为准备,依赖私人信用,发行小区域流通纸币。嘉庆时期,银钱贴的使用已较为普遍。山西巡抚申启贤谈及南北银价时曾提到,“嘉庆八九年间,每银一两易钱八九百文,彼时钱票流行已久”。道光以后,中国广大地区普遍使用银钱贴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据清人王瑬《钱币刍言》记载:“今京师民间市易,自五百以上皆用钱票。安徽省若滁、凤、庐、颖诸处皆用钱票,且一处之钱票,可携之于二三百里之外,向钱庄取钱者,较京师之钱票止在京城中用者,更为流通。又闻盛京及山东地方亦俱用钱票。”银钱票的使用不但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交易媒介,还直接扩大了商业资本的来源。清代王瑬指出:“今贾人出钱票,其始皆恃票取钱无滞,日久人信其殷实不欺,于是竟有辗转行用至数十年不回者,并有竞不回者。黄河两岸,致富者莫不由此。”部分私帖长期辗转流通,推进了私帖的信用化进程。因为受利润驱动,商人必然挪用此项积存现金进行商业投资,谋取额外商业利润,该部分被挪用兑现准备金的银钱贴,则变为依赖私人信用的信用货币。商人意识到发行银钱帖能够直接或间接带来财富的事实,又进一步促使其扩大信用发行的数量。各地当铺、钱庄以及各行商号竞相发行能够在本地流通的私帖,到清中期前后私帖超发的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人民银行总参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
就目前史料所见,中国民间私帖的信用化发展大致起源于清乾隆时期,盛于道光以后,到光绪年间则积弊已深。道光以后,东北、京津、山陕等地,因银钱私帖过度发行,引起银贵钱贱、物价上涨等问题而受到清政府的广泛关注。如,辽南盖平(今营口)作为东北“财货通衢”,道光以前“商民等以银钱贸易,或凭帖取付,向听其便。自道光八年盖平各钱铺起意开始兑买银货之票,诓买银粮,军民虽不得钱,其票尚可兑买银货。迨至道光十年、十二年,该处士民有控钱铺将银粮货物故设高价,顶兑票张,不付现钱……无如天兴等五号巧诈百出,复商同互相磨票,自立五大磨名色,辗转磨兑……迄无实钱”。盖平的情况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盖平钱铺发行只能购买银货而不能兑换现钱的“票”,其起始时间是在道光八年。盖平钱铺发行的私帖,大部分系依赖信用发行,至道光十年、十二年此票已出现通货膨胀,造成银货价格上涨。其二,天兴等五家钱铺之间“互相磨票”的实质是票据交换,即五号以彼此开出的钱票互抵互消,以清理债权债务关系。此项制度设计增加了其银钱票的流通速度。另一方面,五家钱铺的钱票互认、互收、互兑,进一步增强此项钱票的信用,使其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延及金州、复州、熊岳、岫岩等处”。南盖平的情况说明,信用发行与票据交换作为一种金融制度创新在清中期前后已经出现。类似的金融演进不是偶然发生的,道光至光绪年间,中国其他地区的钱庄大致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进程,如绥远的记账货币“谱银”与“拨兑”,高邮的“戳票”,福州的“城钱票”“台钱票”“七钱台伏票”“台棒票”等,均具有类似性质。
钱庄庄票系由银钱贴演变而来,主要是为了适应规模较大的商业结算需要。两者相比,庄票一般数额较大,面额不固定,主要用于商业往来时划转清算;而银钱贴一般数额较小,后期多为定额票,主要是在日常交易中流通市面。清末,在私帖挤兑与政府限制的双重影响下,各地钱庄逐渐减少银钱贴,而以庄票为信用发行的主要工具。这一转变过程在汉口、福州等地皆有体现。近代汉口钱庄发行的纸票分为两种,一种是约兑券,一种是钱票。汉口钱庄发行的钱票,俗称“花票”,“每张票面一串文,凭票兑换”,在市场流通,作为现金使用。早期钱票信用卓著,汉口万镒钱庄发行的钱票“甚至缴厘金关税都可以通用”,早期钱庄利用发行钱票为其资金周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到清末,汉口钱庄发行钱票的情况逐渐减少。“因没有官厅监督,(汉口钱票)任性滥发。到光绪三十四年,三怡钱庄破产,一般人始稍注意。所以宣统元年,汉关道有严禁钱票的明令,宣统二年,度支部划一币制,咨行各省,所有钱票,一律限六个月收回。汉口各钱庄发行钱票一致收回,从此就没有钱票发现”,“今所行用惟约兑券一种而已”。福州也有类似情况。1929年,福州“流通多属钱庄庄票。兹因兑现困难,各庄陆续将一、二、三、五元花栏票收回,向用之向单,则加盖’此单专作转账’字样,面额至少五十元,乃不兑现纸币之变相”。近代汉口的“约兑券”与福州的“向单”由于主要用于转账汇划,其性质均与上海钱庄庄票类似,主要发挥转账结算的金融功能。
《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武汉钱庄史料》
由于进出口贸易量巨大,上海钱庄在处理商业结算活动中较早使用庄票。上海钱庄庄票大致起源于清乾隆年间。1863年,上海钱业公会在一份公启中谈及“上海各业银钱出入行用庄票盖已百余年矣”。1841年,监生徐渭仁等在上海开设“钱庄生意或买卖豆、麦、花、布,皆凭银票往来,或到期转换,或收划银钱”。可见,至迟在道光时期,钱庄庄票已经普遍用于钱庄的信用放款以及商品交易结算,庄票可以到期换票或者直接收账。整体来说,为了满足客商的短期资金需求,在商家提出请求的基础上,钱庄以自身信用为基础发出庄票。钱庄与商家往来,每年正月开市,钱庄跑街即挨家挨户分送折子,以表示继续往来之意。商家收到折子之后,“除长期借款等另做交易外,其余一切往来收解等情,均须随带折子,以便钱庄即时录入,故折子不啻为彼此往来收解之总录也”。折子即为商家在钱庄开立的“户头”,在折子的基础上,钱庄还为商家提供联票簿。“联票簿之性质,犹如银行之支票簿”,但是又和支票簿不同,银行的纸票簿“非有存款,银行绝不凭空而发给”,但是由于钱庄注重信用,商家在收到联票簿之后“可随时出票,向钱庄支用”。商家将日常经营中收到的零散票据按期交到钱庄收账,遇到需付款时,则开出支票从账户支取。但是,商家开出的支票远没有钱庄庄票信用卓著,“支票因只能代表出票人之信用。如出票人信用未孚,或有透支等情形,钱庄即可到期停止付款。故收款人咸愿收入钱庄本票”。更有甚者,如洋行出货除庄票外“他票不收”,“付款者不得不向钱庄打取。于是备折附条,载明所打银数,及期限等,往钱庄打取。钱庄即缮就本票一纸,交与来人,并在折上录入,届时钱庄负责照解也”。庄票的本质是钱庄对商家交易往来提供信用。商人交易时,从钱庄借一张迟期庄票支付货款,卖货方可持此庄票要求钱庄到期兑现或收账,而买方则只需要按照约定日期向钱庄偿还本金及利息。在此期间,商人如将货物转售,收回货款即可以与钱庄该项庄票冲抵。对于购货商家而言,庄票为其减少或免除了资金占用,使其获得商业利润;对于出货商家而言,钱庄庄票提供的信用支持,扩大了商品销路;对于钱庄而言,在不额外占用资金的情况下,仅凭借信用开写票据,即获得了利息与手续费。一般情况下,钱庄提供的信用周转方式使商家与钱庄获得共赢。
伴随贸易量的增长,信用票据的使用显然是必要的。票据代替现金,本质上是解决商品交易中结算筹码的数量、效率与安全的问题。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在1864年—1894年的三十年中,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从9 400余万关两逐步增加到2亿9千余万关两。1867年—1894年,上海直接对外贸易进口值自0.42亿关两增至0.97亿关两,出口值自0.36亿关两增至0.58亿关两。庞大的贸易量,必然需要包括庄票在内的大量交易媒介参与结算。1919年上海“钱庄发出之庄票,年约80万枚(平均每家出票1万号)……大约每庄发出票面金额每年最少者约1 500万两,最多约3 500万两,平均约2 000万两,其总额约十六七万万两”。到20世纪30年代初,包括钱庄庄票在内,上海市面流通中的各类票据约在20亿两以上。1932年12月,上海全市的票据收付数字,银行只有2亿2千余万元,而钱庄则达12亿2千余万元。在1933年票据交换所成立之前,上海钱庄通过汇划制度控制着整个上海华商金融业的票据清算,进而掌握着洋厘、拆息,控制着资金市场、利率市场,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巩固了钱庄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魏友棐对庄票的评价很高:“庄票在上海商业社会上流通之广,为各种票据所仅见。”
樊果编著《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
四、多层次结算体系:过账、票据交换与外埠期票交易
钱庄参与的商业结算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庄内客户之间的收交转账;其二,钱庄同业之间的同城票据交换;其三,钱庄通过买卖外埠期票,完成异地商业结算。根据商业活动复杂程度,钱庄均可以适当方式为其提供结算。
清中期以后,过账逐步成为商业结算的制度基础。过账,简而言之就是将账目由甲账转入乙账。商人因交易产生货款收付时,不以现款结账,而是通过钱庄由账面划拨完成结算。当交易双方均在某钱庄开户时,过账手续较为简便,可以直接划转。如交易双方分别在不同钱庄开户,则各自在开户钱庄处登记,次日再由两家钱庄进行彼此结算。两家钱庄对账后,以彼此收交进行冲抵,其差额以现金找齐,商人应收、应交款项各自登入账户,至此该项结算活动才最终完成。过账制度以宁波钱庄最为典型。宁波各行商铺一应交易款项,多是通过钱庄“过帐”的办法划拨清算。“(宁波)各商店过帐,统于当天晚上抄录清单,第二天一早,由进帐(账)钱庄向出帐(账)钱庄校对,收付相抵,甲庄应解付乙庄的,就开出庄票一张,也就是欠人发出庄票,人欠收入庄票。多缺轧抵后,由各庄自行拆借,或解交现金”。就目前研究来看,学界普遍认为过账制度是宁波帮于清中期前后创设。据宁波钱庄会馆碑文记载:“当乘前清咸丰之季,滇铜道阻,东南患钱荒,甬市尤甚,市中流转之钱庄大减,民生日困,洶洶(汹汹)谋为乱。有谋以善其后者,法令钱[庄]凡若干家,互通声气,掌银钱出入之成群,商各以计簿书所出入,出界(畀)某庄,入由某庄,就钱庄中汇记之。明日,各庄互[出]一纸,交相稽核,数符即准以行,应输应纳,如亲授受,彼此羸绌,互相为用。自此法出,数月而事平,厥后市场交易,遂不以现银相授受,一登簿录,视为左券,亦不虞其他也。”过账制度不仅使商业结算手续大为简化,更重要的是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往来交易中现金不足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当贸易规模扩大,市场中现金不敷周转时,过账成为一种常态化的金融制度设计。宁波钱庄过账有账簿过账、经折过账、信札过账、盖印过账、同过账(两存户在同一家钱庄)、轧字过账等多种形式。商人之间的业务往来,通常使用账簿过账,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过账方式。个人存户则通常采用经折过账。各乡镇与宁波之间的往来采用信札过账,信札成为过账的凭证,已经初步具有票据的涵义。清中期前后,钱庄过账成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制度创新,其作用不但扩大货币供给,同时提高商业结算效率,遂成为钱庄实现新发展的重要契机,使被称为“过账码头”的宁波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宁波钱庄的过账,作为商业结算的一种方式,其创新性仍略显保守。首先,商人要首先在钱庄存款,然后才能过账;其次,过账依赖账簿、经折,因此参与结算的区域受到限制。再次,票据方面的创新不足,钱庄信用在商业结算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天津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天津银号代客转账不是直接过账,而是通过一种不完全的票据——拨码,开展商业结算活动。拨码是“天津钱业同行间用以支取存款或透支款项所开之划拨凭据也”。拨码作为银号间转账清算的票据,为近代天津钱业所独有。银号日常代客户划拨款项进行资金清算,互相开出拨码用于计数,晚间对账无误之后,其差额会于次日以现金或银行支票进行冲算。拨码的性质与支票类似,但与支票不同的是拨码不需要预先在同业存款,基于同业信用,银号间均得代为转账。为了保障拨码的信用,拨码不能取现,即使收入对方账户后亦不能即时取现,需要待次日银号之间用现金或银行“番纸”(支票)进行轧账之后,转账程序才最终完成。因此,拨码是一种不完全的清算手段,主要用于银号同业间往来拨账计数。拨码诞生于光绪初年,在此之前,天津银号应收应交款项例须“过现”。光绪初年,银号为避免彼此结算时银色、平砝差异,以及零星数额找兑繁琐,故创设拨码互相冲抵,后较大数额为避免“过现”,也使用拨码。“行之既久,驯至以一纸’拨码’,代替通货,准备之是否充实,非所过问”。拨码遂变成了银号同业间凭借信用发行的结算工具。拨码的用途主要有两种:“其一,凡商号凭折向其有往来之银号支取存款或透支存款时,银号大率给以拨码,以代现款。其二,同业间彼此无川换,而有款项往来时,辄借’拨码’以为转账之用。”可见,天津银号用拨码开展结算是建立在转账基础上的。无论是“拨交码”还是“收账码”,其区别只是开给对象不同,本质上都是用于过账。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
与宁波过账制度、天津拨码制度相比,上海的汇划制度最为完备。首先,上海钱庄的庄票性质是“本票”,是钱庄信用的有形外化。因此,上海钱庄庄票信用卓著,在市场交易中等同于“现款”。其次,上海钱庄设立汇划公所,开展集中汇划,其功能类似于现代的票据交换所。上海汇划总会虽然成立于1890年,但是上海钱庄之间用“划拨”的方式进行商业结算的活动早就存在。在汇划总会成立之前,各家钱庄间的票据划拨冲销是分散进行的,“各家划账的人并没有集会的地方,时常夹着’总汇簿’在路上寻或在弄堂口等,以便寻到或等到别家的’汇银子的’进行轧汇”。汇划总会成立后,钱庄间开始以公单方式计数进行集中清算。“公单者,为钱庄用于互相冲销彼此收解款项之一种凭单也。惟得上公单之银数,必以五百两为上额,名为’汇头’。成’汇头’之款,收付均以公单,欠人发出公单,人欠则收进公单。所有公单,至晚全在汇划总会互轧,彼此抵销(消),然后凭总会划条以事收解,缺则向他庄拆进弥补,多则拆与他庄,以便轧直”。汉口钱庄的结算模式与上海极为类似。汉口钱庄的庄票早期以现银兑付,交割非常不便。1890年,汉口创立了汇划所,开始进行票据交换。汇划制度的创立使钱庄成为武汉金融业的结算中心,在1948年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展票据交换之前,汉口钱庄控制着全埠金融业款项的收解。
晚清至民国时期,各埠钱庄大都采取集中清算制度。如,近代福州钱庄间的同业清算实行归坪制度。福州钱庄发行纸币和本票,十元以上的大额纸币作为本票,“只供商业之间同业之间划拨转帐,不在市面行使,晚上归坪回归本庄”。福州钱业在鼎盛时期,城台(内城与南台)钱庄有五十多家,划分为五路:直路(中亭街)、横路(三保、潭尾街)、城内(南街)、大街(上下杭街)、桥南(观音井、大岭下)。发行票张估计在500万元左右,为相互监督,公议各路每日“行坪”一次。五路每晚将行坪清算结果,汇集于上下杭街三家清算中心。这三家即泉裕、恒和、祥康,三家中尤以祥康为核心。清算包括所有票据,清算结果,短额的庄号必须以现洋支付归坪支现。与此类似,汕头钱庄实行“换纸”制度。为了避免汇兑庄同业滥发纸票,汕头汇安庄陈春波提出“换纸”(或称“抽纸”)办法,即每日行档内的一家庄号轮流为司事,其他庄号于收付终结后将所存同业纸票提交司事,由司事按庄号分别算出存、欠款数。存、欠数额由司事分别配置合圆后,欠者应于第二天早晨备款向其配定的存者换回纸票,如无款换回须按当天市场利率贴还存者利息。可见,同城票据交换在当时已为常态。
与外地的资金往来,各埠钱庄主要是通过买卖期票完成异地资金结算,这也导致在商业往来中直接汇兑的重要性逐渐降低。钱庄买卖期票的活动将借贷、汇兑、结算等金融功能融合在一起,具有较高的融资效率,是适应贸易快速发展需要而产生的金融创新。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申汇”买卖。申汇又称为“上海头寸”,同一城市在同一时间,有人需要买入申汇,有人需要售出申汇,因此形成了市场交易。钱庄通过庄票、汇票、客票等金融工具长期掌控申汇市场。申汇在商业往来中的作用,学界早有关注。杨端六在《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中对申汉棉花交易中利用期票进行结算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剖析。“上海花号向汉口购买棉花。号客去汉口时,并不带现,以带现颇为风险;亦不由上海汇款去汉,借以省却汇水。号客欲用款时,普通即多利用钱庄的汇票以资周转”。上海花号如拟“赴汉口办货”,“可以向素有往来之上海钱庄,开具迟期兑付之汇票(俗称申票,多数为期票)”。“号客既到汉开始办花,可将该票卖与当地钱庄或银行(即贴现)取得现款,向花行收花。钱庄则将该项申票加价卖与赴沪办货之庄号,俾其持票赴申进货,或邮寄抵欠。有时钱庄收得申票后,即给与本庄庄票,号客取得庄票,如歉(嫌)期限太长,可向银行贴现。庄票信用素著,贴现利率颇轻,遇银根紧时,此种办法,颇为流行”。晚清民国时期,钱庄经营的此类期票买卖异常发达。在不能直接通汇的两个城市之间,还能通过第三方转汇。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汕头钱庄在银根紧迫时,通常卖出长期申票,获得资金用以周转。在该项申票即将到期之时,再购买香港电汇,再由香港电汇至上海,以此电汇款项支付到期申票。这种模式需要钱庄同业在汕头、香港、上海建立较为稳定的汇兑往来关系。举例来说,汕头有一银庄甲号,香港有一钱庄乙号,上海有一钱庄丙号,三者有汇兑往来。今汕头甲号于3月1日因资金紧迫,需款2万元,卖出向上海丙号承兑之申票2万元,票期为5天,加上邮寄时间4日,9日后由上海丙号承兑。3月7日,甲号购买2万元香港即期汇票,邮寄至香港乙号,8日中午到达乙号,乙号再电汇2万元至丙号,9日可达上海丙号。此时,恰逢申票持票人将前往丙号兑款,丙号可将此电汇所收2万元支付给持票人。另一种结算方式,上海丙号也可通过卖出汕头甲号承兑期票的方式,以资付款。丙号可利用见票后的犹豫时间,卖出2万元由汕头甲号承兑的5日期票,以此所得付款给持票人。9日后,汕头甲号需兑付此期票,亦可如法炮制,再卖出丙号承兑的期票,以此付款。可见,钱庄利用票据在商业结算中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钱庄的优势来源于信用方式与内汇网络。与票号相比,钱庄首先是具有较强的信用特征。庄票、汇票、客票等金融工具大多依赖信用发行,客观上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交易媒介,为商业活动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另外,钱庄以内汇网络为支撑,利用庄票、汇票等短期信用工具构建了短期货币市场,该市场具有期限短、风险小、流动性强的特点。钱庄对于商业经营的主要意义是保持资金的流动性,以便能随时随地获得货币资金用于日常周转。
李权时、赵渭人著《上海之钱庄》
结语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货币化与信用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金融的形态、结构与功能,金融则通过货币、储蓄、投资影响市场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因此,无论是新式银行的出现,还是中国本土钱业的发展,本质上都是金融功能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动力来自社会经济发展对融资方式与融资效率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钱业开启了有序发展的序幕,金融需求造就了金融功能发展,并塑造了与其相匹配的金融业态。伴随贸易形式与规模的变化,货币兑换、存放款、汇兑、信用发行等各种金融功能相继出现并逐步完善。与之对应,钱业组织的外在形态逐渐从钱桌、钱铺、兑局,经由账局、放账铺,转变为票号、汇兑庄,最终发展成为业务具有一定现代性的钱庄。虽然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但是明清时期中国钱业发展大致遵循了这样一条宏观轨迹。钱业组织及其主要业务的变化只是外在表现形式,其本质是核心金融功能的发展演变。
杜恂诚著《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北洋政府时期》
钱业是商业性金融机构,而不是普遍为社会经济提供服务的大众金融。钱业的本质是商业活动为解决资金融通问题而发展出的行业性方案,这就决定了其主要任务是处理商业往来中货币、资金的流通与供给。明清时期,官方在货币金融制度供给中缺位,白银、铜钱和民间私人纸币长期并存,互补流通。商业活动中,各类货币需要频繁的鉴定、清点、称量、兑换,货币经营性业务是钱业发展的起点。但是,钱业的发展方向是更高阶的信用发行与汇划清算。作为货币的白银与铜钱,不仅存在携带成本高、安全系数低的缺陷,更主要的是金融货币供给的有限性与不断扩大的国内商品总量之间存在矛盾。交易规模与频次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金融业提供支付便捷、清算效率高的结算方式。
近代钱庄与票号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其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金融业数百年发展而来的兑换、存放、汇兑等基本功能,还通过信用发行私帖、庄票,为社会经济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交易媒介,扩大了商业资金来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转账、汇划形成了非现金结算体系。信用发行与票据交换的结合,是推动钱庄成为商业结算中枢的关键金融制度创新。近代钱庄行业逐渐发展为一个商业结算体系,其中包括作为记账、清账、结账机构的钱庄自身,包括以庄票为核心的结算工具,也包括庄内过账、同城票据交换、埠际期票买卖的多层次结算网络。钱庄的汇划体系代替票号的汇兑体系,本质上是商业结算机制的迭代发展。
本文作者著《近代天津银号与华北区域金融市场化研究(1900—1937)》
虽然,近代钱业获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但是亦有明显不足。其局限表现为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趋势不相匹配。从明清到民国,钱庄的定位始终是商业金融,而不是为国家财政与产业经济服务。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趋势是逐步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国家公共信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即走国家干预下的产业经济发展之路。近代中国金融结构的完善与优化超出了钱庄业的承载能力。因此,清末袁世凯、鹿钟霖、李宏龄等多次尝试将票号改组为银行,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同样,20世纪30年代学界与社会舆论一致呼吁钱庄改组银行,亦鲜有实质性的进展。这绝非仅仅由于钱庄业墨守成规,而是钱庄业的商业定位与政府构建财政金融体系的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钱庄业在商业领域发挥的金融功能所闪现的“现代性”,是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决定了金融的多层次供给。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作者:左海军,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