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乔治·爱略特
我们在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天才雷普利》系列中也能看到一种同情,作者将其赋予到杀人犯的身上,并且指望我们也会相信同情是后者应得的。我们会震惊于这位天才的(也即是说勤奋的)、特立独行的女作家将读者玩弄于鼓掌之上的能力,因为看到故事的结尾,尽管理智告诉我们杀人是十恶不赦的罪行,我们对雷普利不但恨不起来,反而像他一样开始庆幸,他庆幸收获了好运,我们庆幸幸亏他收获了好运。
一种同情的纽带将海史密斯的悬疑小说一把拉到了经典文学的殿堂,没有什么类型小说的划分,悬疑或者科幻(正如《黑暗的左手》或《使女的故事》)一样可以成为经典,只要他们不自以为能够愚弄或者看低读者的智商。正像不是电影塑造了影迷,而是后者纵容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潮流,因而爆米花电影的充斥正是他们应得的一样;读者和作者同等程度的肩负着文学义务,读者的义务也许比重更大,因为如果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但丁或者普鲁斯特在流行,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所谓文学作品就会被扫进书店的角落,是读者而非作者决定了何种现实性应当更加合理。
俄国人的观点
“我们对于契诃夫作品的初步印象,不是朴实无华而是困惑不解。它的意义究竟何在?他为什么要把这一点写成一个短篇小说?当我们读了他的一篇又一篇作品,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他们分手之后又相逢,最后他们俩谈论他们的处境以及用什么方法才能从’这可怕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
“⋯⋯然而,如果曲调是陌生的而结尾的音符是一个问号,或者仅仅表示那些人物还将继续谈论下去,就像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那样,我们就需要一种非常大胆而敏锐的文学感受能力,来使我们听清那个曲调,特别是使那和声显得完整的最后几个音符。或许我们要读过大量的短篇小说才能如此感受,而这种感受能力对于获得我们满意的结论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把小说的各个部分归纳拢来,我们就会发现,契诃夫并非文笔散漫、毫不连贯,而是有意识地一会儿奏出这个音符、一会儿奏出那个音符,其目的是为了完整地表达他的作品的思想意义。”“结果,当我们阅读这些完全没有结论的小故事之时,我们的眼界开阔了,我们的灵魂获得了一种令人惊奇的自由感。”
“的确,灵魂就是俄国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它几乎没有幽默感,而且完全没有喜剧感。它是无定形的。它与理智关系甚微。它是混乱的、噜苏的、骚动的,似乎不能接受逻辑的控制和诗歌的格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波涛翻腾的旋涡、飞沙走石的风暴、会把我们吸进去的嘶嘶作响、沸腾滚泡的排水口。它是完全纯粹用灵魂作原料来构成的。违背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身不由己地被吸了进去,在那里面旋转,头昏眼花,几乎窒息,同时又充满着一种眩晕的狂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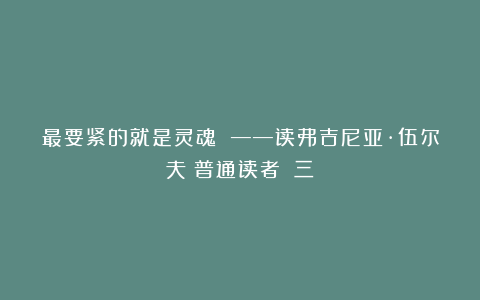
“我们的灵魂,受折磨的、不幸的灵魂,它们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谈论、揭露、仟悔,从肉体和神经的伤口中把那些在我们心底的沙滩上蠕动者的难以辨认的罪恶抽曳出来。但是,当我们倾听他们的谈话,我们骚乱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一根绳索向我们扔了过来;我们抓住了一段独白;我们用牙齿咬住绳索,被匆匆忙忙地从水里拖过去,我们狂热地、疯狂地不断往前冲,一会儿被水淹没,一会儿露出水面,在这一刹那间看到的景象,比我们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理解得更加清楚,并且获得了我们通常只有在生活的压力最沉重的时候才能得到的那种启示。当我们飞快地前进,我们在无意之中看清了所有这一切——人们的姓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原来他们是住在罗里敦堡的一家旅馆里,波丽娜和德·格里·乌克斯侯爵一起卷入了一场阴谋——但是,和灵魂相比,这些是多么次要的事情!最要紧的就是灵魂,以及它的热情、它的骚动、它的美丽和邪恶相交织的惊人的大杂烩。”
灵魂或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整个俄国文学致力于抵达的中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我们对作为杀人犯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作为白痴的梅诗金公爵、作为堕落的老卡拉马佐夫镜像的德米特里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同情。很难解释清楚,疑问同时出现在这些或罪恶或无辜的人物以及我们读者身上,或许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魅力所在。“人们同时是恶棍又是圣徒;他们的行为既美好而又卑鄙。我们热爱他们,同时又痛恨他们。我们惯常所说的那种善恶之间明确的分界线,是不存在的。我们所最钟爱的人往往就是最大的罪犯,而那最可怜的罪人往往使我们感动,以至于产生最强烈的赞赏和爱慕。”
“不论你是贵族还是平民,是流浪汉还是贵妇人,对他说来全都一样。不论你是谁,你是容纳这种复杂的液体、这种模糊的、冒泡的、珍贵的素质——灵魂——的器皿。它洋溢、横流,与其他灵魂融汇在一起。⋯⋯那人类的灵魂——它热气腾腾地、滚烫地、混杂地、惊人地、可怕地、令人压抑地翻腾满溢,向着我们滚滚而来。”
或许厌恶和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由都是基于这个“我们是灵魂的容器”的结论而出现的。反对者同样相信这个结论,他们不能忍受的仿佛是人物的喋喋不休,仿佛小说偏离了文学性,向着哲学性的方向如离弦的箭一般疾驰而去,而这是文学不但力所不及、更加不应当过分触及的。喜爱者的理由可能恰恰相反,作家可以在不丧失文学性的前提下触及哲学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翘楚当中的翘楚。正因为“我们是灵魂的容器”,所以拉斯柯尔尼科夫们反映的其实是我们的真身,所有的行为都是灵魂的质料——无论对错——必须在矛盾性中接近灵魂,以此获得生存之正当性的理由。
“⋯⋯但是,总是存在着一种恐惧之感,它使我们像玛莎一样,想要逃避托尔斯泰注视我们的目光。这是否那种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扰乱我们心境的感觉——感到他所描写的幸福过分强烈因而不会持久,觉得我们正处于一场灾难的边缘?或者,是否感到我们强烈的喜悦不知怎么有点儿可疑,并且迫使我们和《克莱采奏鸣曲》中的波兹涅谢夫一起问道:’但是,为什么要生活?’生活支配着托尔斯泰,正如灵魂支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那些光华闪烁的花瓣儿的中心,总是蛰伏着这条蝎子:’为什么要生活?’在他的著作的中心,总有一位奥列宁、皮埃尔或列文,他们已经取得了所有的人生经历,能够随心所欲地对付这个世界,但他们总是不停地问,甚至在他们享受生活的乐趣之时也要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又应该是什么。能够最有效地驱散我们的各种欲念的,并非牧师僧侣,而是那位自己也曾熟悉它们、热爱它们的人。当他也来嘲弄它们,整个世界的确就在我们的脚下化作一堆尘土、一片灰烬。就这样,恐惧和我们的喜悦交织在一起;而在那三位俄国作家之中,正是托尔斯泰最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也最强烈地引起我们的反感。”
“然而,我们的思想从它的诞生之处就带上了它的偏见,毫无疑问,当它涉及俄国文学这样一种异己的文学,必定离开事实真相甚远。”伍尔夫审慎地表明自己的评价一定存在着局限性,因为“英国人的思想诞生于英国的传统文化,必然会带上它的偏见,因此难以客观地评价一种异己的文学”。
人最可贵的就是自省、自知,什么时候我们能将那种常常以时间长短为度量标准的本民族的文化自豪感稍稍降低一些,就像将对待外国观念性的东西的态度跳出明贬实褒、明褒实贬、阴阳怪气、全盘否定这些自我封闭的池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从偏见的迷雾中稍稍走出来一点。正如伍尔夫的反思,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反思,那种肤浅的自豪感(我的都是好的,他们的都是坏的)很可怕,就像一个人光不溜秋走在大街上,以为自己穿着世间最华丽的衣服,以为众人所以为的和他以为的是同一个东西。时间是个好东西,它会在某个节点,扇出那个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耳光。
评价: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