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一名伊拉克儿童穿过满目疮痍的街道,走在丢弃着垃圾的排水沟边。
自由摄影师李亚楠,因工作需求和个人意向,在多年间往返中东各个地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约旦、沙特……
他曾深入游客难以抵达的战争后方,也曾探访古老文明的遗迹,他用真实的文字和图像资料,记录下了他所见到的中东:关于人、关于事物、关于生活、关于建筑和废墟、关于文明和历史,关于战争与和平。
这一次,他将带领我们前往叙利亚与伊拉克,踏上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讲述“新两河流域”的故事。
Ⅰ.
幼发拉底河沿岸
那些令人心碎的叙利亚伤痕
荒野的夜色深邃,更加难以辨认方向,我们开始返回代尔祖尔的军营。隔着遥远距离,我看到废弃炼油厂那团还在燃烧的火焰。那是整个黑压压的现实里,最明亮的一朵花火。
冬季是美索不达米亚多雨的季节。
在叙利亚东北部哈克塞省的小城卡姆什利,我和一群人挤上车,朝着东南方向出发。伴着淅淅沥沥的雨幕,汽车行驶在被无数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上, 一车人都是国际记者,有来自VII图片社的,有来自美联社的,大家一路闲聊,不时被颠簸打断。司机拿着通行证,给路过的每一个检查站士兵检查,这是战乱地区最普通不过的行进方式。
突然雨停了,天空的一半被乌云遮挡,阳光从另一半倾泻下来。眼前的街道上没有完整的建筑物,也没有完整的路面可言,磕磕绊绊地驶入一栋看似民居的建筑物,防爆墙和沙袋在周围垒出了一个院子。不一会儿,里面出来一行人,手里都拿着一把AK-47,腰间别着几个装满子弹的弹夹,简单打过招呼之后,他们跳上了一辆丰田皮卡车,于是两辆车结队,继续驶入市中心。
终于在一条河边停下车,河上有简单的渡船,所有车辆都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往河对面。我盯着眼前的河水,温柔清澈,反射着天空的湛蓝色,是一片难得的安详,像极了小时候家门外可以嬉闹的河流。但抬起头再看周围,便会瞬间从这种“不真实”的安详里抽离出来:身旁是一座被炸毁的桥梁,河岸两边的建筑物基本都布满弹孔和爆炸痕迹,满目疮痍,人们用简陋的毛毯遮盖住“门窗”,继续在里面生活。
这便是著名的幼发拉底河。我所在的这座小城叫做拉卡,在2013年之后,这里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邪恶之都。在某极端势力最猖獗的一段时间,他们控制住了包含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土地,就将这里视作“首都”。直至2017年10月之后,库尔德武装夺取拉卡,我们才能较为安全地前来。
当时,极端势力对占领的拉卡进行了破坏,再加上历经多次残酷的战争,更是让这座小城支离破碎。我爬上了一座摇摇欲坠的楼房房顶,站在上面俯瞰拉卡。下方是一个路口,中央有一个圆形的转盘,现在被改造成了具有宗教特色的小广场,此前,极端势力将这里作为实行极端律法的审判广场,上演了无数场暴行。
不远处,拉卡的古城墙仍然围绕着这座城市,透露着中世纪的古老气息,掩护着一些只剩水泥框架的简易楼体。这就是拉卡的全部,让人唏嘘。而幼发拉底河此刻雨后初晴,看上去像一幅未精修饰的艳俗美丽风景,还透漏着一丝野味。午后不久,我们一行人调头卡姆什利,在夜幕降临前回到驻地。
又一个清晨,一路沿着断断续续的哈布尔河向正南行驶,来到幼发拉底河边。在两条河流相交的地带,有一座巨大的废弃炼油厂,被库尔德武装改建成了军营,我和一众国际记者都要在此待上几天。
在这几天里,雨水彻底告别了美索不达米亚,她恢复了日常的干瘪。在灰暗或土黄的大地上,只有零星点缀着的浅草,天空也是淡淡的蓝色。军营里,士兵们百无聊赖地摆弄着手里的步枪,墙角的装甲车和皮卡车没有规矩地随意停放着。我吃着军营的餐食,手机没有信号,打开地图很久才获得定位,就着加载不全的地图界面,才知道自己正身处叙利亚的代尔祖尔。
某一天,我们坐上皮卡车队出发,在一望无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疾驰。平原上没有公路,只有一条条被轮胎碾形成的车辙,我同士兵们坐在皮卡车后面,一路颠簸难耐,大风和荡起的尘土模糊了视线,也遮蔽了说话的声音。偶尔会路过一些战壕,里面的士兵和我们打着招呼,除了这些战壕,周围没有任何参照物,完全无法辨别所处的位置。看着终于加载出来的地图,我才发现司机已经驶入了伊拉克的国界线,而这时他也发现车辙变少,立马掉头返回,寻找更多的车辙。由此可见,国界线的概念在这里多么虚无。
终于到了目的地——还是一片荒地。具体位置我至今都没有弄清楚,只知道这里是幼发拉底河边,临近叙利亚与伊拉克边境。车队停了下来,几个士兵把皮卡车后马槽的遮布拉开,露出里面的重型武器,开始对着远处的一个土坯房射击——这算是他们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我观望着四周,看见几株零星的油菜花,阳光带着暖意,另外一些士兵躺在草地上看着天。
所有人就这样等待着,直到暮色来临,才开始行动起来。士兵们将皮卡车排成一排,然后打开大灯,一条条明亮的光柱直射远方,有种电影片场的仪式感。他们在对讲机里不断交谈着,远处也传来了卡车的轰鸣声。在残阳西坠的背景衬托下,驶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卡车车队,伴随着尘土激扬,车队来到跟前,所有人严阵以待。
在车灯的照射下,卡车车厢的大门依次打开,陆陆续续有人从车上下来,挨个接受士兵的安检。他们正是某极端势力的武装分子,经过数年的战争之后,先是龟缩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小镇巴古兹,再逐步向库尔德武装投降,被卡车运到这片荒地进行安检后,进行遣散和交由军事法庭进行裁决。
失去了武器之后,这些武装分子都面无表情,沉默寡言,目光近乎呆滞,记者上前拍照,他们便深深地低下头;有的受了伤,下车后无力而痛苦地趴在地上;还有一部分人是戴着罩袍的女性,甚至还带着孩童——这些是武装分子的家属,只能完全依附于男性,却无法决定自身的命运,等待着她们的,将会是遣返或安置……
荒野的夜色深邃,更加难以辨认方向,我们开始返回代尔祖尔的军营。隔着遥远距离,我看到废弃炼油厂那团还在燃烧的火焰。那是整个黑压压的现实里,最明亮的一朵花火。
沿着幼发拉底继续向南,来到伊拉克如今的首都巴格达附近。在这里,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相守相望,两条河距离最近时只有20多公里,但很快地,她们再次分道扬镳,在两河之间形成一片较为开阔的区域,这一区域被绿洲铺满,种植着一望无际的椰枣林和农田——这是当代伊拉克腹地典型的景观。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对于这句歌词,中国当代的年轻人都不陌生,这是周杰伦单曲《爱在西元前》的第一句歌词。
而当真正站在古巴比伦城面前时,拿一首现代歌曲去构想古巴比伦则显得有些荒谬,因为现实的古巴比伦城,会打破儿时对这里的所有幻想。没有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也没有黑色玄武岩上刻着的汉谟拉比法典;没有辉煌宏伟的神殿,也没有“思念像底格里斯河般的蔓延”。真实情况是,空中花园早已不复存在,黑色的汉谟拉比法典在法国卢浮宫,湛蓝色的伊始塔尔门在柏林帕加马博物馆,就连古巴比伦城也不在底格里斯河边,而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一条微小的支流旁边。
更令人争议的,发生在曾经萨达姆掌握伊拉克命运的时代,他为了私人爱好和欲望的满足,在古巴比伦城原址上复建了巴比伦城。崭新的砖块垒砌成一面面墙体,在地基上拔地而起,形成了既颓废又不美观的石砖建筑群,看起来充满塑料感,就像一个活脱脱的“中古时期主题乐园”。在复建了古巴比伦城之后,他还命人在新的砖墙上刻一组文字:“此墙由尼布甲尼撒二世之子萨达姆·侯赛因所建,光复伊拉克之荣耀。”用来神话其虚假的所谓“高贵血统”。
古巴比伦城西侧有一个不高的土丘,在土丘顶上,还有一座残破的宫殿。爬上土丘进入宫殿,能看到那些已被毁坏但仍然难掩其奢华的装饰,这就是萨达姆众多的行宫之一——巴比伦行宫。
站在一个房间废弃的露台,我望着不远处的古巴比伦城。不禁联想到,曾经的某个清晨,萨达姆或许就站在这个位置,俯瞰着自己亲手复建的古巴比伦城,当太阳渐渐升起,金光打在他的脸上,他嘴角上扬泛起微笑,欣赏着他亲手构建的一切。而现实是,独裁者早已被绞刑,他的宫殿也成了人民泄愤和报复的目标,遭到破坏和践踏。
在古巴比伦附近的幼发拉底区域,还有两座阿拉伯帝国兴盛之后的历史名城,卡尔巴拉和纳杰。这两座城都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由于卡尔巴拉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节日,伊拉克全国的什叶派穆斯林都要徒步前往参加这场盛会,我只得前往纳杰夫。纳杰夫除了拥有伊玛目阿里的圣墓之外,还有全世界最大的一片墓地,由于地处一片低洼地,还人们称为“和平谷”。这片墓地的规模之大,几乎堪比一座城市,目前已经埋葬了超过200万人,面积却还在不断扩大当中。
被战乱折磨得满目疮痍之后,如今的伊拉克虽然仍然算作战乱国家,但较数年前已经相对平和许多。在泥沼中挣扎了数十年,幼发拉底沿岸写满了支离破碎与颓废贫瘠,但更显而易见的,还是日益正常化的生活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拉卡,一辆军用装甲车停在街头
在河中心的汽车和人。这种简单的渡船,是当地的过河方式。
一位男性站在幼发拉底河岸边。
几名妇女走在回廊。
废墟屋顶。钢筋水泥凌乱而赤裸地延伸突兀着。
拉卡,一片废墟。
拉卡的街头,站着聊天的人们。
苏塞,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正聚在一起。
苏塞,写有标语的墙面,几根高耸的巨大立柱。
拉卡,一名妇女满面愁容地站在废墟中。这里或许是她曾经的家。
平原上,一名男子用摩托车载着他的同伴经过。
在代尔祖尔军营,拍摄下库尔德武装的女兵。她们的平均年纪很小,大多身处和平国家的同龄人,应该正在学校读书拿笔,而她们却不得不拿起步枪。
在等待俘虏送来的期间,士兵们百无聊赖地在平原上架起机枪,朝着“敌人”扫射,这是他们打发无聊的方式。
一名俘虏,紧闭着眼睛痛苦地躺倒在地上。等待着他的,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
复建的古巴比伦城,充满塑料感,犹如一座主题乐园。
街头简陋的礼拜场所。
纳杰夫和平谷,实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墓地。
Ⅱ.
底格里斯河沿岸
废墟深处的伊拉克哀歌
沿着茂密芦苇所形成的自然水道穿行,穿过一座铁架桥,看到大量当地小海在桥上嬉闹,他们快乐地跳入水中,溅起水花,再爬回桥上,周而复始。
悲伤的故事不仅写满幼发拉底,同样写满底格里斯。
在伊拉克北部的底格里斯河东岸,有一片遗留了土坯城墙的废墟,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尼尼微。3000年前,尼尼微是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最重要的古老政权——亚述帝国的首都,曾拥有无限的辉煌灿烂。而如今,在尼尼微遗迹外,已满是当代低矮的楼房,这些楼房密聚在底格里斯河两岸,组成了一个现代伊拉克的重要城市——摩苏尔。
在近十年中,摩苏尔是伊拉克最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之一。2014年,某极端势力攻占摩苏尔,直到2017年伊拉克政府军才重新收复,且收复之战打得极为惨烈。在长期的战乱中,超过70%的城市建筑物和道路遭到完全破坏,前后逃离的居民超过90万。
快进入摩苏尔市中心的时候,我看到路口边一栋四层楼房坍塌成了三层,二楼几乎不复存在,唯有临街的一层,弯折的几根立柱在勉强支撑,整栋楼房呈现扭曲,岌岌可危。可即使这样,一层却还亮着灯光,开了一家仍在运营的饭店。人们若无其事地从这栋楼前走过。当我不断深入市中心,跨过底格里斯河来到摩苏尔老城时,意识到这种景象竟是常态。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在战争废墟中选取还勉强可以使用的房屋,对它进行简单改造,让生活在废墟中挣扎着恢复平静。
我想起内战后的叙利亚霍姆斯和阿勒颇,这两座城市的整体建筑规模和密度更大,楼房更高,同样几乎全城沦为战争废墟。街道上空空如也,所有楼房可以自由进入,在瓦砾之间穿梭,能看到无数戛然而止的生活。用一个不恰当的形容,就是那两座现代战争废墟城市,要比摩苏尔看起来更为“壮观”。那些巨大的楼房布满弹孔,立柱残破颤颤巍巍,楼板被扭曲的钢筋牵连悬挂在半空中。它们静默在大地上,有一种无声的“纪念碑”般的震撼,展现着战争的残酷。
我爬上摩苏尔的一座高楼,对面有一座巴格达酒店,已经人去楼空,东南角的楼板坍塌下来,二楼的招牌残存了几个字母。在老城废墟中,还有一些小卖部,一家卖可乐的店主,是一位身着长袍的白头发老大爷,坚持不肯收我的钱,结果旁边路过一个货车司机,看到我这个外国人,便慷慨地请客了。在战争废墟中感受到这种好意,不由得让人心头一暖。
从摩苏尔出来,沿着伊拉克1号公路南下。路边渐渐出现了绿洲,说明公路重新回到了底格里斯河岸边。一个向东的转弯后,到达了伊拉克历史名城萨迈拉的所在地,这里拥有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我最喜欢的建筑物——萨迈拉旋转塔。
虽然我一向不热衷于专门去看所谓的“地标性建筑”,但当我面对萨迈拉旋转塔的时候,还是会被这种远古的气息震撼到说不出话来。它静静地矗立在美索不达米亚,近1000年来,几乎都享有这片土地上最高建筑的美誉。它那不容辩说的美感,那可以一直盘旋而上、直至塔顶的阶梯,无疑是人们幻想中“巴别塔”的现实样貌。
萨迈拉旋转塔的造型既远古又科幻。不得不说,古人真是“笨拙”得可爱,在平坦到无边的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对于登高这件事不知所措,因此决定采用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建筑层层垒高,然后一圈一圈盘上去。这样的形态,让它看起来如同一座未来建筑,虽形式极简,却由内而外散发出不凡的气息,既附着了过往神圣的意义,又指向了幻想中不可触及的未来。当站在它面前时,我才真实地触摸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浪漫。
巴士拉位于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南端,已经是波斯湾的前沿。在此,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各自的故事即将走向终结,两者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新的河流“阿拉伯河”,最终汇入了海洋。
实际上,伊拉克占有的波斯湾海岸线很少,大部分都属于邻国伊朗和科威特。巴士拉向南有一条连接科威特的80号公路,也正是大名鼎鼎的“死亡之路”,30年前的某场国际战争中,在这条公路上的溃败成为了伊拉克部队的梦魇,大量废弃的重型武装至今仍散落在公路边上。
巴士拉的街区充满了一种“美国式”的落寞感,低矮的房屋,破败的街道,随意搭建的电线和散落地面的垃圾,都让我产生一种模糊感,仿佛不是在伊拉克,而是置身五大湖边、美国“锈城”底特律的郊区。一直走到阿拉伯河边,河上有两座桥梁,一座是高大巍峨的现代桥梁,另一座是低矮的铁桥,充满老式的工业气息。
站在铁桥上看阿拉伯河的中心,有一艘侧面倾倒躺在河床上的沉船。走得近一些,能看到船舷上已经生锈的文字“AL-MANSUR”,这艘被叫做曼苏尔的豪华游艇,当年同样属于萨达姆私人所有,如今却只能破败地躺在阿拉伯河中。
沿着阿拉伯河从巴士拉出发,北上30多公里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古尔奈,便能亲眼看到两河在此交汇。在两河交汇的三角区域,有一片我认为最接近古时美索不达米亚地貌的区域,这里的居民至今保留着原始的生活方式。这里便是“伊拉克大沼泽”,它拥有与苏美尔文明相同的年龄,在干旱的中东腹地里,是一片难得的湿地。
包一条小船,精瘦的阿拉伯小伙子坐在狭窄的船尾,把马达拉开,我们开始在湿地里探索。沿着茂密芦苇所形成的自然水道穿行,经过一座铁架桥,看到大量当地小孩在桥上嬉闹,他们快乐地跳入水中,溅起水花,再爬回桥上,周而复始。在河道两边,偶尔能看到他们的传统房屋,那种由芦苇编制而成的茅草屋,看起来像个半圆形的圆筒,在芦苇丛之间若隐若现,充满波西米亚般的野趣。偶尔又被水牛阻挡去路,只能减速等它慢悠悠地通过。
这个湿地终于描摹出我脑海中远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形象,她如今的荒凉实在配不上她远古的辉煌。而在这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曾拥有的繁荣历史,不是干瘪的文字记载,不是空洞的考古复原,它们是实际存在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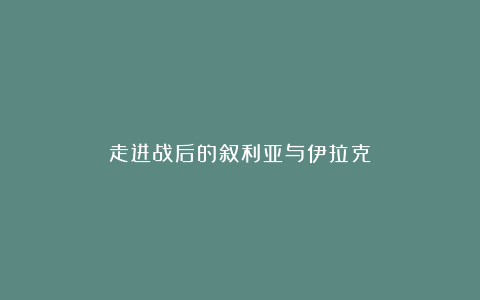
这里并没有萨达姆的行宫。他占据了幼发拉底,占据了底格里斯,甚至自建私人湖泊,但他唯独不喜欢大沼泽。他曾表示,人类就不应该在沼泽那种环境里生活,应该将当地居民全部赶出来,然后将沼泽的水排干。这样的行为给大沼泽带来了灾难,在短短几年内,大沼泽的水域面积缩减了一大半,直到他倒台之后,大沼泽才稍有恢复。
在大沼泽的贪玩让我忘了时间。我实在是享受这份真实的远古美索不达米亚,以至于错过了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只能在巴士拉暂住一晚,第二天沿着1号公路返回。
巴格达,是我在伊拉克最熟悉的城市,也是每次来伊拉克的起点和终点。无论去往哪里,都将从巴格达出发,回到巴格达。在经历过战争之后,底格里斯河西侧的首都核心区域被圈起了一大片地,用防爆墙进行封锁,这一片区域就是著名的绿区。绿区的内外是两个世界,外部是水深火热的巴格达市井生活,绿区内部便是所谓的安全区,戒备森严,名副其实的城中城。
离开绿区,去往巴格达老城的拉希德大街,就会回归真正的巴格达市井生活。几十年来,那里的一切几乎都未曾改变,除了每周五之外,每天都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人们在这里汇聚,购买所需的日用品。进入这里,会立马陷入这种日常生活带来的麻痹感,感叹于这种“平常”是多么珍贵。
就在拉希德大街的旁边,便是静静流淌千万年的底格里斯河,站在河边观望,不免有些悲伤。如今,底格里斯河与巴格达的生活非常脱节,她孕育了这里的一切,而如今的巴格达却一副将她抛弃的模样。河上没有运输的船只,没有任何生活迹象,甚至连钓鱼的人或游船都没有。长期战乱带来的界限感,让底格里斯河与巴格达硬生生地割裂开来,她就像一条城市的排水沟,突兀地出现在这里。
其实对于巴格达,我有很多想要诉说的,那就以内心的细微感受作为结束吧:巴格达,作为一个曾经战乱国家的首都,她是一座在全球化进程中转型失败、整体上肮脏混乱的城市,但我却在接近她,每次沿着破败的高架桥跨过底格里斯河时,就会倍感亲切和放松,接受她所有的缺点和真实。我想,把自己打碎并溶解在这片混沌、浑浊里,或许就能分辨出我内心深处,最细微的那份共情。
摩苏尔街头,随处可见的建筑废墟。
摩苏尔,仍在固执还原生活的面貌。
建筑废墟的内部。
依旧是摩苏尔。建筑物的顶层几楼已然被炸毁,但底部却仍有人开张店铺,继续经营生活。
从远处观看迈萨拉旋转塔,有人沿着它层层盘旋而上去往顶端。
另一个角度的萨迈拉。
巴士拉的路边,人们的帐篷。
举着旗子在街头的人们。
巴士拉的夜景,依稀仍有现代城市的氛围。
沉没在阿拉伯河中心的游艇,它曾经属于萨达姆私人所有。
在这片大沼泽中,芦苇茂密而肆意地生长。自然分出的河道变成了主要的交通道路。
乘舟在河道中穿行。
泡在河道中的牛。
在巴格达街头,还有现代城市的繁华气息。
巴格达伊玛目卡齐姆清真寺外, 一群嬉戏的孩童。
巴格达的建筑。
一片荒地上。穿着一黑一白的两名男性正在交谈。
一辆积满灰尘的汽车,旁边的建筑墙体上布满了弹孔。
走过花下的少女。
本篇文章发表于《环球人文地理》2021年12月刊
-END-
撰文/摄影:李亚楠
排版/编辑:水星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