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后一个花瓶在我脚边碎成一地青花瓷片时,我出奇地冷静。满屋狼藉,我精心设计的简约风新家,此刻像是被龙卷风扫荡过的垃圾场。酱油泼在刚刷好的白色墙壁上,像一幅诡异的泼墨画;沙发被划开了几道大口子,棉絮争先恐后地往外涌;电视屏幕上是一个硕大的窟窿,边缘还挂着方便面调料包的碎屑。
我资助了七年的七个“贫困生”,此刻正像七头被激怒的野兽,喘着粗气,用通红的眼睛瞪着我。为首的那个叫郝强,他手里还攥着半截砸烂的椅子腿。
我的妻子孟婉缩在角落里,吓得浑身发抖,眼泪早就哭干了。
我没理会他们的咆哮,也没去看孟婉,只是平静地掏出手机,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他们大学班主任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我用一种不带任何情绪的语调说:“王老师,新年好。跟您说个事,从今天起,我对您班上那七个学生,郝强、李明、张伟……对,就是他们七个,所有的资助,全部永久性停止。一分钱都不会再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屋子里的咆哮也瞬间卡壳。那七张年轻又狰狞的脸,在听到“永久停止”四个字后,齐刷刷地凝固了,愤怒和嚣张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滑稽的、不可置信的呆愣。
而这一切,都要从我十年前,去参加恩师郑老师的葬礼说起。
01
说起这事儿,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心不足蛇吞象。
十年前,我还是个刚在建筑设计行业崭露头角的小设计师,远没有现在的家底。我的恩师,郑卫东老师,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也是把我从一个乡下野小子领上正道的人。他一辈子清贫,住在学校分的破旧筒子楼里,却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了学生身上。我考上大学的学费,还是他偷偷塞给我的,那皱巴巴的五百块钱,是他省了小半年的工资。
郑老师无儿无女,走的时候很突然,心脏病。葬礼上,我哭得像个孩子。料理完后事,律师交给我一封信和一个存折。信是郑老师留给我的,存折里有二十万块钱,是他一辈子省吃俭用,加上学校后来补发的一些补贴,攒下的全部家当。
信里,郑老师的字迹还跟以前一样,刚劲有力。他说,他一直关注着我,为我的成就感到骄傲。但他心里,始终惦记着他老家那座大山里的孩子们。他一辈子没能走出去,他希望他的学生能走出去。这二十万,他委托我,用这笔钱,在他老家的中学里,寻找一个像我当年一样,虽然穷,但有骨气、有志气、懂得感恩的孩子,资助他读完大学。等这个孩子大学毕业,如果品性依然贵重,就把剩下的钱,连本带息作为他的创业基金,让他能有机会改变命运。
郑老师在信的最后写道:“俞任,我知道这事儿难,识人比识图纸难。但老师相信你,你是个好孩子,眼光不会差。记住,钱是小事,选对人,才是对老师最大的慰藉。”
我捧着那封信,感觉重若千斤。这是恩师最后的嘱托。
为了不辜负恩师,我没有声张。接下来的几年,我每年都亲自去一趟郑老师的老家,那个叫石窝村的偏僻山村。我联系了当地中学的校长,以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爱心人士”身份,悄悄观察着那些品学兼优的贫困生。
可人心这东西,隔着肚皮,实在太难看透。我看了好几届学生,总觉得差点意思。有的孩子成绩好,但为人过于精明,甚至有些自私;有的孩子老实,但又缺了点闯劲和灵气。
时间一晃就是三年。我怕再等下去,会耽误了孩子们。于是我改了主意,我跟妻子孟婉商量,郑老师的二十万我先不动,我自己出钱,把范围扩大。我不再只寻找“那一个”,而是决定同时资助一批孩子,把资助期限拉长,从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用时间来考验人心。
就这样,我从那一届的尖子生里,选了七个家庭最困难的孩子。郝强、李明、张伟……他们七个,就是第一批。
我给他们定的标准是,每人每年学费全包,另外再给五千块钱的生活费。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这笔钱足以让他们在学校里过得体面,可以专心读书,不用为生计发愁。
最开始的那几年,一切都跟我想象的一样美好。
每年我收到七封感谢信,信里满是质朴的感恩和对未来的憧憬。郝强在信里说:“俞叔叔,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像您一样当个有用的人,回报社会。”李明说:“俞叔叔,我用您给的生活费给奶奶买了药,她让我一定要给您磕个头。”……
那时候,我常常看着这些信,觉得心里特别暖。我觉得,郑老师在天有灵,看到这一幕,也一定会很欣慰。我甚至开始计划,等他们大学毕业,就把郑老师那笔钱连同这些年的利息,平分给他们七个,也算是完成了恩师的遗愿。
可我忘了,人是会变的。尤其是当钱来得太容易的时候。
02
事情是从他们考上大学,离开那个闭塞的山村开始起变化的。
大城市的花花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染色缸,把他们原本质朴的底色,染得五彩斑斓,也面目全非。
最先露出苗头的是郝强。他考上了省城一所不错的大学。大一刚开学没多久,他就给我打电话,语气不再是以前的小心翼翼,而是多了一丝理所当然。
“俞叔叔,我们同学都用苹果手机,老师上课有时候也用APP点名签到,我这个老掉牙的按键机,实在太不方便了,也……也给您丢人不是?”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倒不是心疼钱,一个手机而已。而是他话里那句“给您丢人”,让我觉得特别刺耳。我的资助,什么时候和我的面子挂上钩了?
但我没多想,只当是孩子刚进大学,有点虚荣心也正常。我给他转了八千块钱,让他自己去买。
结果,这口子一开,就再也收不住了。
没过两个月,李明也来了电话,说要报个英语口语班,要六千八。紧接着,张伟说要考驾照,又是五千。其他人也以各种名目,比如“参加社团活动需要置办行头”、“跟同学搞好关系需要聚餐”、“买专业书籍”等等,开始频繁地向我索要额外的钱。
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接一个。
我的妻子孟婉最先看出了不对劲。她是个心思细腻的女人,掌管着家里的财务。有一次她对账,皱着眉头对我说:“俞任,你看看这个月,光给那七个孩子打的钱,就超了三万块。这都快赶上咱们家一个月的开销了。你这是资助,还是供养啊?我怎么瞅着,像养了一群白眼狼。”
我当时还替他们辩解:“孩子刚到大城市,需要适应,花销大点正常。咱们多帮衬一把,让他们别因为钱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孟婉叹了口气:“我不是心疼钱。我是怕你这番好心,最后养出了他们的贪心。斗米养恩,担米养仇,老话总是有道理的。”
现在想来,她的话真是一语成谶。
真正让我感到寒心的,是那年国庆节。我正好去郝强所在的城市出差,就想着顺便去学校看看他,关心一下他的学习生活。我没提前通知,想给他个惊喜。
结果,我按他给的地址找到他们宿舍,舍友却说他跟女朋友出去旅游了,去了邻省的著名景点,听说住的还是五星级酒店。我给他打电话,他支支吾吾,说是在跟“老乡”做兼职。
我在他桌上,看到了他随手丢下的几张消费单。最新款的耐克球鞋,一千八。一部最新款的单反相机,快两万。还有一张游戏充值记录,三个月就花进去五千多。
我站在那间凌乱的宿舍里,看着那些刺眼的单据,心里第一次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恶心。我给他的钱,是让他安心学习,改变命运的,不是让他去挥霍,去跟人攀比的。郑老师的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他的血汗钱,换来的是这些,该有多失望?
从那天起,我留了个心眼。我不再对他们的要求有求必应,而是开始“打太极”。我说公司最近项目紧,资金周转不开,让他们先自己想办法,或者去申请学校的助学贷款。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他们不再写感谢信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他们的七人小群里(我后来才知道有这么个群)对我的抱怨和谩骂。他们觉得我变了,小气了,不像以前那么“大方”了。郝强甚至在群里说:“他一个大老板,住那么好的房子,开那么好的车,随便漏点出来就够我们吃喝了,现在居然跟我们哭穷,真是越有钱越抠门!”
这些话,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另一个受我资助、但良心未泯的学生那里听说的。那个学生后来退出了他们的圈子,悄悄把这些告诉了我。
我当时没发作,只是心彻底凉了。我终于明白,我的善意,在他们眼里,已经变成了理所应当的责任。我不是他们的恩人,而是他们的提款机。
我决定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也是对郑老师的一个交代。那就是今年春节,我让他们一起来我家做客。我想当面看看他们,看看这几年大学生活,到底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如果他们中,哪怕还有一个能表现出最初的淳朴和感恩,我都会继续履行对郑老师的承诺。
可惜,我还是高估了人性。
03
大年初二,他们七个,穿得人模狗样地来了。
每个人都提着点不值钱的礼品,脸上挂着虚伪的笑,一进门就“俞叔叔、孟阿姨”地叫个不停,亲热得好像我们才是一家人。
孟婉准备了一大桌子菜,忙前忙后。我则坐在沙发上,冷眼看着他们。
我发现,他们看我家的眼神,已经不是最初的敬畏和羡慕,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嫉妒和贪婪。他们打量着我的房子,我的家具,就像在估价一样。
饭桌上,酒过三巡,郝强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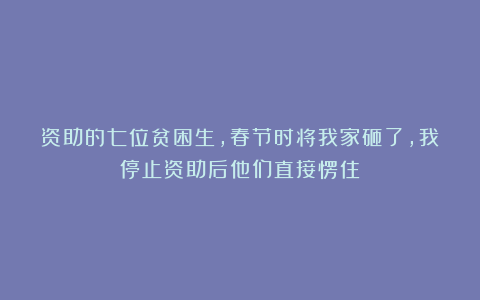
他端起酒杯,站起来说:“俞叔叔,我们几个都敬您一杯。这些年多亏了您的照顾。我们眼瞅着就要毕业了,您看,我们这工作还没着落,家里的情况您也知道,我们几个合计了一下,想请您再帮我们最后一把。”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哦?怎么个帮法?”
郝强嘿嘿一笑,搓着手说:“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七个,您就帮我们在省城,一人付个首付就行。一套房子,对您来说,不就是九牛一毛嘛?我们有了房子,工作就好找了,对象也好谈了。等我们将来出人头地了,肯定忘不了您的恩情!”
他这话一出口,其他六个人也纷纷附和。
“是啊俞叔叔,您就当提前投资了!”
“有了房子,我们就是城里人了,您脸上也有光啊!”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因为酒精和贪婪而涨红的脸,气得都笑了。
我问他:“郝强,你觉得我凭什么要给你们买房?”
郝强被我问得一愣,随即理直气壮地说:“凭您有钱啊!凭您资助了我们这么多年啊!有始有终嘛!您总不能帮到一半就不管了吧?那我们这大学不成白读了吗?”
“白读了?”我冷笑一声,“我给你们学费,给你们生活费,是让你们来读书学知识的,不是让你们来找我要房子的。你们把我的善心,当成什么了?摇钱树吗?”
我的话像一盆冷水,把饭桌上虚伪的气氛彻底浇灭了。
郝强的脸瞬间就挂不住了,他把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酒都洒了出来。“俞叔叔,您这话就没意思了。我们是穷,但我们不是来乞讨的!我们也是有尊严的!你今天把我们叫来,不会就是为了羞辱我们吧?”
“尊严?”我站了起来,指着他,“你们一个月花着我给的几千块钱,买名牌,去旅游,玩游戏的时候,怎么不谈尊严?你们把我的资助当成理所当然,变本加厉地索取的时候,怎么不谈尊严?现在,跟我谈尊严了?”
我的话,显然是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七个人脸色都变了,恼羞成怒。郝强一脚踹翻了身后的椅子,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姓俞的!你别给脸不要脸!你那点破钱,打发叫花子呢!你以为我们稀罕?要不是看你还有点用,谁愿意叫你叔叔!今天你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没完!”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
接下来的场面,就彻底失控了。他们像是疯了一样,开始在我家打砸。嘴里还骂骂咧咧,说要把这些年的“委屈”都发泄出来。
孟婉吓得尖叫,我把她护在身后,第一时间报了警。
混乱中,我看到郝强举起了客厅墙上的一幅镜框,那是我特意装裱起来的,里面是郑老师唯一留下的一张照片,和他亲手写给我的一幅字:“德才兼备,方为人上人。”
“住手!”我冲了过去,但已经晚了。
“啪”的一声巨响,镜框被他狠狠地砸在地上,玻璃碎裂,郑老师的照片和那幅字,被一只踩着名牌运动鞋的脚,狠狠地碾了过去。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犹豫、愤怒、失望,全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冰冷的、死寂的平静。
我知道,这个考验,结束了。他们,全都交了白卷。不,是交了负分的白卷。
所以,当警察赶到,控制住场面,看着这一片狼藉的时候,我才会那么冷静地,拨通了那个电话。
0.4
停止资助的电话打完,世界清静了。
警察把他们七个带走,做笔录,定损,拘留。我这边,则开始不紧不慢地走法律程序。故意损坏财物,金额巨大,够他们喝一壶的。
最先撑不住的,是学校和他们的家长。
王老师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语气从最开始的震惊,到后来的恳求。“俞先生,您看,孩子们马上就要毕业了,留个案底,这辈子就毁了。您大人有大量,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我只回了一句:“王老师,毁掉他们前程的不是我,是他们自己。机会我给过,不止一次。”
接着,是他们的家长。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只在电话里听过声音的朴实农民。他们操着浓重的乡音,在电话里哭天抢地,求我高抬贵手。有的说家里就这么一个大学生,是全村的希望;有的说愿意砸锅卖铁赔偿我的损失,只求我能撤诉。
我一概拒绝了。我对其中一个父亲说:“大叔,我理解您的心情。但今天我放过他们,明天他们就会去坑害别人。我是在帮社会,也是在帮他们,让他们知道,做错了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最精彩的,还是郝强他们的反应。
从拘留所出来后,他们发现,我不仅停止了资助,还真的把他们告上了法庭。他们彻底慌了。
郝强第一个给我打了电话,电话一接通,就是一通咆哮:“姓俞的,你真够狠的!我们不就是砸了你点东西吗?至于要毁了我们吗?你信不信我们把你的事捅到网上去,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为富不仁的资本家是怎么欺负穷学生的!”
我静静地听他说完,然后轻笑了一声:“哦?是吗?我等着。记得把你们怎么要求我给你们一人买一套房,怎么把我的家砸得稀巴烂,尤其重点说说,你们是怎么把我恩师的遗像踩在脚下的,都原原本本地写上去。看看网友们,是骂我,还是骂你们。”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足足半分钟,郝强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没了刚才的嚣张,带上了哭腔和颤抖:“俞叔叔……我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那天是喝多了,一时糊涂……您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我们给您磕头了,给您赔偿,我们去打工,一辈子给您还债……”
“晚了。”我打断他,“郝强,你知道吗?我资助你们,从来不是因为我钱多得没地方花。”
郝强愣住了:“那……那是为什么?”
我一字一句,清晰地告诉他:“因为,这是我的恩师,郑卫东老师的遗愿。他把他一辈子的积蓄,二十万,托付给我,让我寻找一个品德高尚的家乡子弟,资助他,并且在他毕业后,把这笔钱作为他的创业基金。你们脚下踩碎的那张照片,就是他。”
电话那头,我能清楚地听到倒吸冷气的声音。
我继续说:“我找不到那个唯一的人,所以我扩大了范围,我用我自己的钱,资助你们七个,就是想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机会,也是想通过时间,来完成郑老师的嘱托,看看你们谁,配得上这份传承。那笔钱,连本带息,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万了。它本来,是为你们当中最优秀,最懂得感恩的那个人准备的。”
“你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你们七个,没有一个是那个人。你们砸掉的,不是我的家,是你们自己的前程。你们踩碎的,不是一张照片,是你们通往未来的唯一一座桥。现在,桥断了。”
说完,我挂了电话。我能想象,电话那头的郝强,会是怎样一副面如死灰的表情。他以为他砸掉的是几万块的家具,却不知道,他亲手砸掉了几十万的未来,和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就是他们“愣住”的真正原因。他们不是为自己的恶行后悔,而是为自己错失的巨大利益而震惊,而追悔莫及。
0.5
后面的事情,就没什么悬念了。
法庭判决下来,七个人因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数额巨大,分别被判了缓刑,并且要赔偿我所有的经济损失,总计十二万余元。缓刑,意味着他们的档案里,将永远留下这个污点。这对即将毕业找工作的他们来说,是致命的。
我听说,学校也给了他们处分,毕业证都差点没拿到。曾经作为全村骄傲的七个大学生,如今成了反面教材。
他们后来又托人找过我几次,哭着喊着求我原谅,说愿意给我当牛做马。我一次都没见。有些人,不值得原谅。我的善良,很贵,不能喂给狗。
至于郑老师留下的那笔钱,我没有再用它去进行下一场人性的考验。人心,经不起考验。
我用那笔钱,以郑卫东老师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助学基金,交由专业的基金会进行管理。我制定了严格的章程,不再一对一资助,而是以奖学金的形式,奖励给那些真正品学兼优,并且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的学生。申请和审核,全部公开透明,不再掺杂任何个人的情感和判断。
我觉得,这才是对郑老师最好的告慰。他的善意,应该像阳光一样,普照更多的人,而不是被几棵烂掉的树苗,耗尽所有的养分。
我的家很快就重新装修好了,比以前更漂亮。孟婉再也没提过那件事,只是有时候看着我,眼神里多了几分心疼和理解。
人到中年才明白,善良是种选择,但善良也需要锋芒。你可以选择去帮助别人,但你更有权利在被伤害的时候,收回你的善良,并让对方付出应有的代价。
大家评评理,我这么做,过分吗?如果换了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