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上午,随团走进神秘的、位于北外滩的“世界会客厅”。
漫步于世界会客厅清水砖墙之间,指尖掠过那些历经百年风雨的砖石纹理,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的话语浮现脑海:“建筑物以双重方式被接受:通过使用和对它的感知。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触觉和视觉的方式被接受。”
真正的建筑,是那些能够将历史沉淀为空间形式的作品。
这座由扬子江码头蜕变而来的建筑群,恰如一本摊开的立体史书,每一页都记载着上海从被动开放到主动拥抱世界的沧桑历程。
有知名建筑家曾言:“建筑应当像树木一样,从历史的土壤中自然生长。”世界会客厅的改造,正是对这种“有机更新”理念的最佳诠释——不是抹去过往,而是让历史在新的语境中重获新生。
一、砖石记忆:码头肌理中的城市年轮
世界会客厅原址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扬子江码头。该码头原为上海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码头,又称三菱码头,主要建筑有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办公楼(现港务局办公楼位置)、1号仓库、2号仓库和3号仓库等建筑。其中2号仓库和3号仓库两座建筑始建于1902-1903年,以清水青砖与清水红砖为特征的外立面,体现了特有的历史风貌。在漫长岁月中,两座仓库经历多次改建,周身被灰色水泥包裹,外观形态“平平无奇”,蒙上了一层历史的尘埃。
站在复原的2号仓库红砖墙前,不禁想起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在《不安之书》中的观察:“城市是人类的第二层皮肤,而建筑则是这皮肤上的皱纹。”这些1903年的砖块,见证了黄浦江上各国商船往来如梭的繁华,也亲历了民族资本在这里奋起抗争的峥嵘。
建筑史学家柯林·罗在《拼贴城市》中指出:“伟大的城市应当像地质层一样,保留各个时代的沉积。”世界会客厅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它完整保留了码头仓库的工业骨骼——那些粗壮的木梁、斑驳的砖墙等,都在无声诉说着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港的往昔荣光。
美国城市学家曾赞叹:“水岸是城市最初的会客厅。”扬子江码头作为近代上海“水岸会客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造没有选择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推崇的“白板式更新”,而是采用了意大利修复理论家布兰迪主张的“批判性保护”——既修复历史肌理,又坦诚展现岁月痕迹。
这种“修旧如旧”的哲学,与中国传统书画修复中“全色不掩破”的智慧不谋而合,让参观者既能感受建筑原初的工艺美学,又能体味时光流转的沧桑诗意。
二、艺术新生:传统语汇的当代转译
走进世界会客厅内部,展厅、廊道随处可见各类艺术作品。
其中有三幅作品创造了三个“中国之最”大世界吉尼斯纪录,分别为国内最大的琉璃多媒体艺术装置墙《江南印象·绿水青山》、国内最大的室内风景油画《日出东海》和国内最大的花卉主题马赛克镶嵌艺术作品《满园春色》,超大尺幅极具视觉冲击力,蕴含着独特的中国文化神韵。
步入中央大厅,《江南印象·绿水青山》琉璃墙前,日本物派艺术家关根伸夫的理论浮现脑海:“材料本身具有记忆,艺术家的使命是唤醒这种记忆。”
这件融合传统琉璃工艺与多媒体技术的装置,让人想起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法”——琉璃的透光性创造出“高远”“深远”“平远”的立体空间,电子元素的流动又赋予其当代韵律。
这种创新,恰如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所描述的“经由他者返回自身”的文化路径——在技术语言的转换中,反而更深刻地抵达了江南美学的本质。
在《日出东海》巨幅油画前,俄罗斯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理论获得新的诠释:最写实的风景,往往蕴含着最抽象的精神。
画家以法国印象派的光影技法,表现中国山水“澄怀观道”的哲学意境,让人想起林风眠当年在《东西艺术之前途》中的预言:“调和东西艺术,可能产生时代的新艺术。”
而《满园春色》马赛克镶嵌则实践了西班牙建筑师高迪的理念:“自然中没有直线”,数十万块彩色瓷片构成的流动曲线,既呼应了宋代《百花图卷》的细腻工笔,又展现出敦煌壁画般的装饰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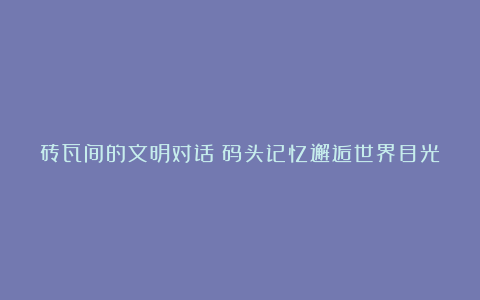
遗憾,这次参观没有看到实物。
三、厅堂之问:公共性的现代诠释
参观“世界会客厅”后,感到这“会客厅”的功能定位需要有新的审视。
第一,这“世界会客厅”属于“一江一河”范畴,遵循“把最好的资源让给人民”,也应最大限度吻合时任市委书记李强2019年4月16日视察黄浦江两岸提出的“世界会客厅”理念;第二,“世界会客厅”应纳入博物馆、图书馆等的公共文化资源范畴,参观可以预约,但不宜收费;第三,这“世界会客厅“虽然投资建设是国企,但运营管理拟可移交公共文化管理部门,按专业化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第四,这“世界会客厅”的会议厅等功能可以按照上海全过程民主理念,全力打造市民论坛等;第五,这“世界会客厅”应逐步消除“神秘性”,增强“开放性”,成为上海民间社会组织国际交流合作的主要窗口和平台。
面对世界会客厅的运营命题,加拿大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警告犹在耳畔:“如果明天的市中心会看起来像今天大多数正在规划的重建项目的话,那它将沦为一个纪念碑式的无聊。但市中心是可以生机勃勃和激动人心的——而且并不难发现如何做。”单一功能的纪念碑式建筑,终将成为城市活力的墓碑。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在此显现价值——真正的公共空间应当是由市民日常实践共同塑造的“生活剧场”。
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舒兹的“场所精神”说更启示我们:建筑是赋予人一个“存在的立足点”的方式。
只有当建筑功能与集体记忆产生共鸣,空间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曾区分“活文化”与“存档文化”的差别。
世界会客厅要避免成为后者,或许可以借鉴东京六本木之丘的“垂直都市”模式——地下层设市民文化中心,中层为专业展厅,顶层作国际会议空间,形成文化民主的立体架构。
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提出的“拥挤文化”概念也颇具启发: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排期,让专业活动与公共参与在时间维度上和谐共存。
四、黄浦江畔的文明互鉴
离开世界会客厅时,倚靠江畔栏杆远眺。
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的洞见愈发清晰:“文明的活力,在于其吸收与转化的能力。”
世界会客厅恰如一面棱镜,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光谱折射融合。
许多国际学者曾将上海比喻为“现代性的实验室”。上海的海派建筑印证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判断:真正的相遇,是让两种文化在接触中各自发现自己新的可能。
文化的意义,在于不断提出问题而非给出答案。
世界会客厅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开启了关于城市记忆、文化认同与国际对话的持续思考。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了一种对话式的方法来理解一切事物,而不是孤立的解释。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的核心在于不断寻找真理,这需要通过对话来实现。理解始终是一种对话过程。
在北外滩8号这座由码头蜕变而来的文化空间里,砖瓦与光影、历史与当下、本土与世界,正进行着一场永不落幕的文明对话。
2025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