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诗意”是山水画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审美诉求。
从文本上看,“山村诗意”似乎与传统文人山水画所追求的山居图,乃至“小桥流水”的文人田园寄情并无太大差别;但从图像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启的“国画改造运动”,则将“山村”内涵改变为具有现代农耕生产特征的诗意图景。这里描写的“山村”并不是文人山水画想象性营造的远离官场宦海并可静心读书的竹篱茅舍,而是充满了被作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的农民如何在农耕生产中获得丰收的喜悦以及由此生成的现实生活的淳朴诗意的场景。这里的“山村”并不渲染其“心远地自偏”,而是试图描写山乡村民辛勤劳作或收工归途呈现出的某种欢快心理。这些“山村”无不体现了画家对现代生活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兴,正像印象主义画作对巴黎美好时代的描写,光彩闪烁,充满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拥抱。
张际才山水画的研习,起步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水画现代变革之中,他以赣南基层美术工作者的身份深刻感悟了这种时代变迁,并力图把这种山村巨变浓缩在山水笔墨之中。这无疑成为贯穿他一生的现代山水画求索的审美内核。他的山水画极少出现西北荒漠,也鲜涉猎冰川雪岭,而是锁定他最熟稔的赣南或岭南,以平湖水塘为镜,倒映田畴远山,其间,飞鸟绕村、牛犬埂走,出工或晚归的乡民茶农斗笠点点,一派悠然祥和的景象。
这种“山村诗意”还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焦点统一的现代性视觉经验。画作往往以四尺斗方的方形构图,呈现截景的视窗边界感。不论“金字塔式”“回字形式”,还是“抛物线式”“S形式”,其构图所制造的形式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艺术样式。在今天看来,这种样式虽不乏装饰性,但这种视觉的整一化也为“山村诗意”提供了清新而明澈的现代视觉质感。与此相应的笔墨,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既非“马一角”“夏半边”的幽微邈远,也不似倪瓒之枯简、“四王”之干皴,而是汲取了李可染的积墨、傅抱石的散皴,并在此基础上增添了那个年代对水墨渗化趣味的探求,将水彩画的大水法与笔墨相结合,创造了湿笔韵墨、灵动秀雅的个性风貌。
应当说,张际才在水色运用上发掘颇深。过多用水,必然会降低用笔的写意性,使水墨画成为水彩画的副本。他的山水虽用水较多,但极少晕染,而多以笔去“破”、去“化”。所谓的“水破墨”“墨破水”或“浓破淡”“淡破浓”,抑或“色破墨”“墨破色”等,无不以笔为中介,用笔收得住、合得拢、积得厚,才使水色的融混在千变万化之中富含笔墨的意蕴。作为那一代从基层走出的画家,张际才始终以生活为创作源头,这也形成了他的画作较少山水的笔墨概念,而以山村诗意充盈其内的特征。可见,山村活水才真正赋予了他的笔墨魂灵。
(本文为“星湖流韵 岭南精神——张际才山水画展”前言)
张际才 《青松颂》 中国画 139cm×68cm 2007年
张际才 《晚归》 中国画 62cm×34cm 1987年
众家评张际才山水画
孙克(中国画学会创会副会长、美术理论家): 张际才的作品,我觉得真的很好。他是一位非常有才气的画家,可惜我们相识太晚了一点,他跟刘勃舒还有过一段渊源,但是当时我们都错过去了。他的山水画,看似是写生,但又不完全是按写生的路子走下来,还是有很多自己发挥出来的笔墨意境。中国的山水画不是风景画,不是风景照片,也不是西方印象派那种光色的画法,而是中国人对诗的意境、诗的追求、诗的感触,然后通过自己的笔墨画出来的笔墨意境。没有好的笔墨,画的景观再美也不行。有好的笔墨,好的书写的感觉、下笔的感觉,且画家在其中达到一种个性的表达,才是真正的能够流传下去的好的中国山水画。不理解中国的书法、不理解中国的笔墨,那其绘画的骨头、绘画的神韵是不行的。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这张际才做得非常好,每张画都有自己的想法,构图的处理、意境的安排,确实很厉害。
他在赣南生活了很长时间,在北京也待过,现在到了广东肇庆,真正好的画家不都是完全依靠地方风物。他画的是南派山水,画的植被很丰富,不同于北方山水画大山大水的表达。但重要的是,他在艺术处理方面还是有他自己的个性,没有好的笔墨个性,一个画家的作品是流传不下去的。山水画近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李可染之后,我们始终在追求山水画的意境和山水画的个性表达,真正有自己的语言特点,从这点上说,张际才是很好的,相信他会越画越好,因为他在艺术的追求、形式风格、造型感觉上都很有天分。同时,他又在笔墨上有相当的领悟。
我们用中国传统来看画中的笔墨、书写性、线条,其中包含了不同的审美意识。我比较欣赏张际才的画,是因为他作品中有很多笔墨是自我的“笨”方法,比如树干想粗就粗、想细就细,他会进行写生景观的主观处理。另外,他的技法也是比较丰富的,笔墨大块面上用不同的墨色渲染出来的效果有现代的意识,这是现代性。可以说,他是江西走出的名家黄秋园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山水画家。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美术理论家): 张际才的山水画总体来看很有他本人的特色。这个画展体现了张际才从基层一步步进入专业画家行列的历程,表征出一种艺术创作的“际才精神”。他的写生、创作、教学是环环相扣、互相生发的,因此也成就了他一种相对独特的山水画风格。
他的《当代写意山水画技法新编》一书编得很好,既涵盖基本的技法,包括树法、石法、云法、水法,还涉及了怎样取景、构图,怎样把写生的内容取舍、剪裁到创作中,怎样从写生进入创作,体系比较完备,为初学者构建了一条从技法训练到艺术创作的完整路径。
在具体艺术表现方面,我最欣赏的是他画的松树。与黎雄才注重松枝细节的岭南画法不同,其松树造型呈现出独特的“际才式”审美特征:在笔墨处理上,通过干湿浓淡的对比,形成苍劲与柔美的辩证统一;在设色方面,淡花青色与点苔技法的诗意化处理,赋予松树意象从容典雅的气质。这种艺术语言的形成根源,可追溯至其扎根江西的长期写生实践,他2005年创作的《庐山古松》即为典型例证。
基于现有艺术成就和丰厚的传统水墨画的基础,张际才的创作尚有值得深化的方向:首先,他可以尝试将标志性的松树意象与简澹山水背景结合,构建更具辨识度的主题系列;其次,写生经验可拓展为系统性的地域美学研究,形成“岭南山水”的当代诠释范式,创作出新时代山水画的新意境、新图式。
赵力忠(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专业委员会研究员、美术理论家): 第一点,我说一定要来看张际才的画展,因为他是基层文化馆工作者出身,我在1965年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分配到山西省群众艺术馆。上班不到一个月,馆里就组织我们打铺盖下乡,一走就是十个月,所以我对基层文化馆工作者辛苦的工作和他们取得的成就很有体会。文化馆的同志什么工作都得干,多是“杂家”,画画、捏泥人、面塑都得学,甚至春节演出时锣鼓点少个人,馆里的同志都要随时补上去敲两下。可以说,基层文化馆的干部能够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从这点来说,我对张际才表示祝贺。
第二点,我想从张际才名字中的“际”字去分析下他的作品。“际”字在汉语词典中有“边界”之意。我认为,张际才的很多作品都处在多重“边界”的平衡状态中:其一,介乎传统与写生之间。纵观中国山水画发展脉络,20世纪50年代倡导写生,80年代转向创新,90年代回归传统。张际才的作品未偏执于任何一端,而是游走于传统程式与写生间,以生活体验为根基,将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实践积累转化为艺术语言;其二,介乎南北之间。张际才作品中有黎雄才的痕迹,黎雄才的创作于岭南画派中兼有北方山水的味道,在这点上,可以说张际才与其是一致的。他既吸收了北方大山大水的灵魂,同时又把南方意蕴的灵气秀美融入其中。张际才在水和墨之间把握得比较好,他“以墨代水”“以水破墨”的技法,也较好地呼应了南方气候的氤氲特质;其三,介乎写情与写景之间。山水画历来有“写景”与“写情”的分野,写生派、写实派往往注重写景,文人画注重写情,张际才的山水画则情与景都占到了,没有偏重于哪一边,情与景交融,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其四,介乎潇洒与敦实之间。张际才的笔墨我很欣赏,他的笔墨有潇洒的成分,可是没有纯玩笔墨,而是把这种潇洒和敦实的品质融合在一起,既洒脱又敦厚,这和别人不一样;其五,介乎书房(雅趣)与农舍(烟火)之间。他的作品于书房与农舍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或者说一种表现方式,既没有庸俗化,也没有僵化。他的作品很活泼,尤其后期的创作,用笔用墨很熟练, 但熟而不油、由熟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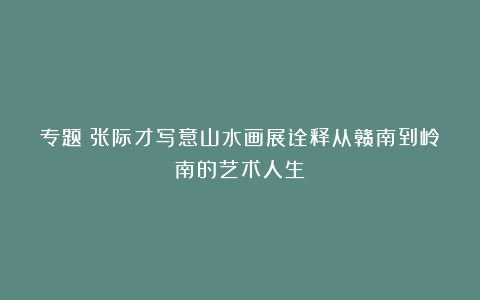
高天民(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20世纪中国美术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古代的传统,另一个是20世纪创作的传统,也就是新传统。展厅里第一次看到张际才的画作,我立刻就想到了黄秋园。很显然,张际才和黄秋园不是一回事。黄秋园更多的是上追古代的传统,而张际才明显属于现代传统的路径。这一点从他作品的表现方式上就可以看出,特别是方形构图,这种构图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创新和流行样式。因为要用西方的风景视角来介入中国的山水,改变传统山水立轴式的构图,这样的画法在那时影响很多人,所以张际才还是在大的中西融合的视野之中往前走的。这种中西融合容易陷入西方风景画的形式中,但风景不等于山水,并且引入风景这个概念后,作品容易变得俗气、小气。我看张际才的作品没有掉进这两个陷阱,有他独到的地方,讲究从空间、景色中纵深进去。
张际才作品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花鸟为笔墨来入山水,很多地方就不再是描摹,而是写意了,靠笔墨写出来的,不是重复一个景色或者一个物象,而是用笔墨本身把质感、体积、空间表现出来,就使画面生动起来了,不再是风景本身吸引你,而是变成了画本身吸引你、笔墨来吸引你,这是一个很新鲜的思路。正是因为这样一点,使他的作品和一般的新传统风景式的作品拉开了距离,这方面也区别于岭南画派,不仅是南北画风的问题,我觉得有他自己的视角和艺术面貌,这是我对他的一个基本判断。这样一种风景式的山水或者他用花鸟式的笔墨来进行的山水画改造是有成果的。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张际才山水画展在《中国美术报》艺术中心开幕,首先体现了京城美术界对于张际才创作的肯定。基于这个展览本身的地域性特点,如何从山水画笔墨发展的角度体认张际才山水画的价值,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看张际才作品的第一个感受是他重视笔墨,重视墨和色的运用。流韵溢彩同时墨色相融,因此,我觉得展览主题用“流韵”概括他的艺术风格是非常恰当的。张际才有在多个地域写生创作的经历,在他的画面里,山水的结构和笔墨的塑造中确实有岭南画派的影子,这个影子是对于山水画色彩的呈现,他将写实性的表达融入了光影的表达之中,在光色表现层面丰富了岭南画派的现代性表达。他的四尺斗方等小品颇见功力,于方寸间呈现了墨色流变的多重层次。
在今天学院派的体系中,在山水画不同的地域中,他的画法从样式创新或者题材创新的角度并不是特别让人眼前一亮,但正是在这种戴着镣铐的画法之中才见功力。他的皴法力图突破程式化桎梏,以具有书写性的笔触构建山石肌理,其远山处理借鉴水彩晕染技法,近水表现则化用夜景水墨的朦胧意境。一方面让我想到近现代名家宗其香的夜景画里面一些对于夜景水墨的描绘,另一方面他充分结合了南方气候氤氲多雾的特质进行创作,可以说,在“色墨不碍”的角度上,张际才有创新性的表达,这些都凸显了其山水画的个人特色。
张鹏(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际才的山水画创作颇为注重人物点景形象的描绘。自南宋以来,宏阔山水与精微点景人物相融合的图式传统绵延至明清及近现代。张际才作品中的点景人物虽具传统形式,却在画意传达与主题构建层面展现出新的艺术维度,正如尚辉对其论及的“山村诗意”,实则是通过人物活动与生活情境的精心刻画得以彰显。
整体观之,张际才的艺术探索延续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画变革的重要脉络,即在山水画中注入生活体验与真情实感。这种创作理念在当下仍具启示意义:当诸多当代山水画家弱化人物表现时,其作品中人物与景物的互动,既保持了传统笔墨韵味,又拓展了形式语言的表现力。尤其在方形构图的经营中,通过对近景竹楼、曲树等物象的细致刻画,中景民居的意象化处理,以及远景的虚化表现,构建出极具张力的空间关系。这种视觉逻辑既暗合中国画“三远法”的传统法则,又通过枝柯交错的分割线与岭南芭蕉、竹林等地域性符号的创造性运用,形成独特的视觉韵律。
在技法层面,张际才将水墨皴染与矿物颜料巧妙融合,朱砂、三绿等传统颜料的运用既保持写意精神,又强化了画面构成感。值得关注的是,作品中蕴含着深刻的地域文化基因:江西民居的质朴厚重与岭南风物的温润秀逸,既延续了八大山人的孤傲风骨、黄秋园的苍润笔墨,又折射出傅抱石等金陵画派的革新精神。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并非简单摹古,而是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渗透在笔墨结构中。
从美术史维度审视,张际才的创作实践实际上构成了20世纪彩墨画革新运动的当代回响。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将地域文化特质转化为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艺术语言,如何在坚守笔墨本体的同时实现当代性转化,这些课题都在其艺术探索中得到了富有价值的回应。
薛良(北京画院美术馆负责人) :张际才的山水创作呈现出清晰的地域文化演进轨迹。早期作品深植江西山水基因,以沉厚笔法构建山体骨架;中期加入北方山水的皴法和强劲笔力;后期融合岭南风物特质,通过丰茂植被与水汽氤氲的笔墨处理,形成“北骨南韵”的艺术气象。这种跨地域的文化交融在树木造型中尤为显著:虬曲盘结的枝干承袭江西山石的苍劲,而湿润淋漓的墨色晕染则透出岭南雨林的生机。
在构图范式层面,张际才突破传统竖幅程式,大量采用方形构图强化近景叙事。这种视觉革新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契合现代空间展示需求,通过压缩景深适应当代审美;其二,以框景式构图增强观者代入感,虽弱化“三远法”的空间层次,却强化了情感共鸣。水墨技法方面,既承续岭南画派“水破墨”传统,又创新性融入浓彩点染,在《鼎湖山印象》中,朱砂与石绿的碰撞为北方山水注入灵秀气质,形成“北派南化”的独特视觉语法。其编著的技法教材显现出体系化探索,尤以“疤痕皴”与“镂空法”最具突破价值。前者通过断续皴笔模拟树皮质感,后者以负空间营造表现枝干穿插,两种技法共同拓展了传统树法表现维度。
观其近年创作,已在意境营造与形式语言层面取得双重突破,建议在以下维度深化探索:其一,强化图像互文性,通过题跋与画面的隐喻关联构建新意境;其二,拓展题材边界,在田园诗意之外探求现代山水的多元表达;其三,深化地域文化研究,将赣粤文化基因转化为更具当代性的视觉符号。岭南地区特有的开放性与实验精神,或可为其突破地域风格局限提供重要契机。其后续发展值得持续关注。
魏祥奇(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张际才的绘画艺术呈现出一定的审美品格与时代印记。观其近年展览,作品整体气韵畅达,笔墨挥洒全无滞碍,这种创作状态源于其数十年的艺术积淀。我认为,张际才的艺术特质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维度:
在地域文化表达方面,作品虽具南方山水的共性特征,但岭南文化的浸润尤为显著。在肇庆的写生系列中,氤氲水墨与朱砂、三绿的设色碰撞,既捕捉了鼎湖烟雨的湿润气息,又暗合岭南彩墨传统。这种地域特质并非简单图式的移植,而是通过《春风春雨》等作品中的云雾意象与民居符号,将文化记忆转化为视觉诗性。值得注意的是,其乡村小景创作虽源自写生,实则重构了传统文人画的桃花源意象——梯田、竹楼等现实物象经过笔墨提纯,升华为承载隐逸理想的精神图式。
在艺术语言层面,展出的作品可以清晰辨识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创作轨迹变化。早期如《晚归》《青山颂》等作,延续了新中国山水画的叙事传统,通过繁密细笔与严谨构图传递山岳精神。而近年作品则转向对笔墨本体的探索。这种转变既折射出从社会叙事向艺术本体的时代转向,也彰显了艺术家对形式语言的自觉建构。
在写生与创作关系处理上,张际才的实践具有其启示价值。他的写生不是简单的对景描摹,而是强调“目识心记”后的意象重构。“肇庆”系列中烟雨迷蒙的视觉效果,实为长期观察后的笔墨提纯,这种创作方式既避免了现场写生的表象局限,又保持着鲜活的现场感受。正如关山月“不动就没有画”的箴言,他艺术生命力正源于写生观察与画室创作的良性互动,在记忆重构中实现传统程式与现代体验的转化。
置于当代山水画发展语境中,张际才在图像化创作盛行的当下,坚守笔墨本体价值,将山村诗意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审美体验。这种创作路径既区别于学院派的技法至上,也与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主题先行模式保持距离,是通过生活感受与形式语言的深度融合,开辟出传统山水画的当代转化通道。尽管在历史叙事深度与风格多元性方面尚有拓展空间,但其艺术实践确为化解“图像时代”的创作困境提供了有益参照——在保持笔墨精神内核的同时,通过地域特质的当代诠释,实现了传统山水画的生命力延续。
张际才
艺术家简介
张际才,1940年生,山水画家。1958年毕业于江西省赣州师范学校。1958年至1969年先后执教于江西省崇义县上堡、杰坝、扬眉中学。1970年至1985年先后任江西省崇义县文化馆副馆长、馆长。1986年至1999年,任职江西省崇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在此期间,兼任江西省赣南画院画师。曾多次被评为江西省先进文化工作者。退休后,只身抵京求索艺术精进,在多个机构从事美术教学工作。2016年至广东肇庆,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和教学工作至今。2010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张际才山水画》;2017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怎样画写意山水》;2022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当代写意山水画技法新编》。
编辑 | 闫 君
制作 | 杨晓萌
校对 | 安亚静
初审 | 李振伟
复审 | 马子雷
终审 | 金 新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