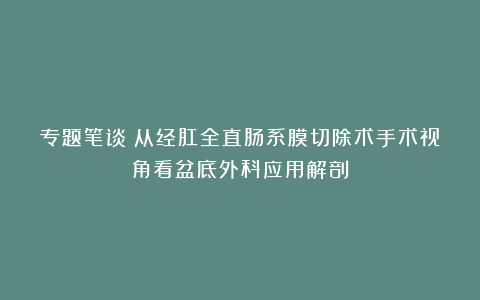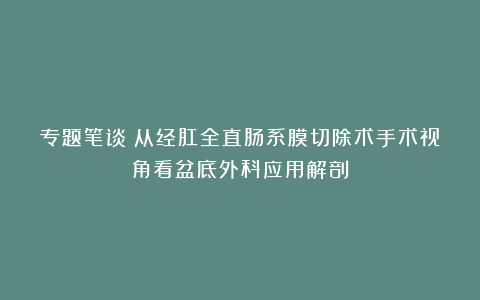作者:赵智成 刘彤
文章来源:国际外科学杂志, 2019,46(8)
结直肠癌在我国是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低位直肠癌的Miles手术后腹壁造口影响着患者的生存质量。通过各种技术改良、器械应用,在保证肿瘤学安全的前提下,减少实施Miles手术能显著改善低位直肠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情绪。
1 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
1982年,Heald等发表了其进行全直肠系膜切除(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手术的成果,革命性地将直肠癌的局部复发率从40%降到了10%。随后,Buess等尝试了经肛门内镜手术(Transanal endoscopic microsurgery,TEM),并顺利完成了中、上直肠息肉或早癌的切除,为保肛手术提供了新的技术。2011年,Sylla和Lacy将2项技术结合,完成了第1例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aTME)。
近年来,TaTME这项技术更是我国结直肠外科领域的热点,但局部应用解剖的详细梳理文献并不多见。中华医学会推出了《直肠癌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专家共识及手术操作指南(2017版)》,明确了TaTME是利用TEM平台,采用’由下而上’的操作路径,并遵循TME原则而实施的经肛腔镜直肠切除手术。腹腔镜辅助TaTME手术可以发挥经腹和经肛入路的各自优势,分别完成各自的操作部分,学习曲线更短,更易实施和推广。
TaTME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低位直肠癌可做到最大限度的保肛手术,而且便于确定肿瘤的远切缘,也为外科医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盆底的解剖。
2 肛管的解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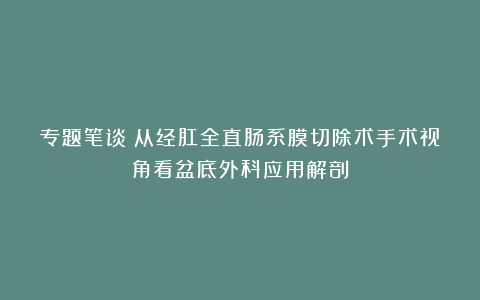 手术入路对于任何外科手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入路的改变可以将同一手术操作的面目焕然一新。肛门是人体的一个重要自然腔道,对于直肠疾病无疑可作为一个良好入路,弥补了经腹入路对于下段直肠暴露不足的缺憾。括约肌间切除术(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ISR)原是直视下进行的肛提肌下方经肛门入路。
由于部位的特殊性,肉眼直视下确认肛门内外括约肌间正确的层面并向口侧解剖一向被认为是此项技术的难点。随着腹腔镜时代到来,由于手术野的放大,完美的解决了上述问题。ISR应该是TaTME的一部分,犹如从不同的楼层进入会有不同的风景,但可用的解剖标志更为有限。
肛提肌和肛门外括约肌无论在解剖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可认为是一个喇叭状的整体,其与直肠的关系类似于’套筒’。两者间的联系就是联合纵肌。TaTME手术开始的关键在于由内而外全层切开直肠壁并辨认各个层次:
(1)含有车辐状的血管的黏膜下层;(2)颜色稍显苍白的直肠环肌;(3)呈放射状的联合纵肌。初学者由于紧张或过于保守,此时往往不能做到’全层’切开,直接导致在直肠壁内的某一疏松平面内向口侧潜行,始终无法找到下一解剖标志,造成该手术在初期便无法继续。若切缘低于肛门直肠环,切开环形肌和联合纵肌后,无法进入肛提肌上腔,则不能见到骨盆内筋膜。实际上ISR阶段也只能看到下探的裸露的肛提肌。
手术入路对于任何外科手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入路的改变可以将同一手术操作的面目焕然一新。肛门是人体的一个重要自然腔道,对于直肠疾病无疑可作为一个良好入路,弥补了经腹入路对于下段直肠暴露不足的缺憾。括约肌间切除术(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ISR)原是直视下进行的肛提肌下方经肛门入路。
由于部位的特殊性,肉眼直视下确认肛门内外括约肌间正确的层面并向口侧解剖一向被认为是此项技术的难点。随着腹腔镜时代到来,由于手术野的放大,完美的解决了上述问题。ISR应该是TaTME的一部分,犹如从不同的楼层进入会有不同的风景,但可用的解剖标志更为有限。
肛提肌和肛门外括约肌无论在解剖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可认为是一个喇叭状的整体,其与直肠的关系类似于’套筒’。两者间的联系就是联合纵肌。TaTME手术开始的关键在于由内而外全层切开直肠壁并辨认各个层次:
(1)含有车辐状的血管的黏膜下层;(2)颜色稍显苍白的直肠环肌;(3)呈放射状的联合纵肌。初学者由于紧张或过于保守,此时往往不能做到’全层’切开,直接导致在直肠壁内的某一疏松平面内向口侧潜行,始终无法找到下一解剖标志,造成该手术在初期便无法继续。若切缘低于肛门直肠环,切开环形肌和联合纵肌后,无法进入肛提肌上腔,则不能见到骨盆内筋膜。实际上ISR阶段也只能看到下探的裸露的肛提肌。
3 直肠前壁的相关解剖
较腹腔镜入路,经肛入路在直肠前壁的暴露有着先天的角度优势。全层切开直肠壁后,直肠尿道肌是前壁最早的重要解剖标志。前方的剥离始于10点和2点方向,有疏松的结缔组织。对于男性患者来说,钝性分离后可以看到有被膜覆盖的前列腺后壁。
直肠正前方12点方向,可以看到相对粗大的白色平滑肌纤维,这就是连接直肠和尿道的所谓’直肠尿道肌’,其前方便是尿道膜部(见封三,图1)。女性患者直肠与阴道间的间隙更为菲薄,解剖时更需要仔细耐心。如不能正确识别解剖平面,对于男性患者将导致尿道膜部的损伤,而对于女性患者虽然没有以上顾虑,但考虑到TaTME必然的直肠低位吻合,损伤阴道仍是术后经久不愈的直肠阴道瘘的危险因素。若不幸发生且伤口较大,除了应修补阴道,必要时需游离大网膜对直肠吻合口与阴道伤口间进行隔离。
会阴体的概念一直有所混淆,不同的外科医师及解剖学家对此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它位于肛门与尿道球部之间,是由平滑肌及骨骼肌共同包绕疏松结缔组织所形成的结构。
笔者认为,简单来说,会阴体就是直肠尿道肌在尾侧的延续。正确理解这一结构,才能避免损伤尿道球部,也是顺利找到直肠尿道肌的关键。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尝试使用TaTME的装置进行腹会阴联合直肠切除术。此项技术带来精细化解剖的同时,更要求术者在不依赖触觉的情况下仍能正确剖开会阴体并向头侧游离。
Denonvilliers筋膜最早于1836年由法国外科医师Denonvilliers在解剖男性尸体时提出,认为此筋膜有悬吊固定中轴器官,并与神经血管相关。在组织学上,Denovilliers筋膜由2层腹膜融合而成;但在肉眼下包括腹腔镜皆无法分辨2层结构。
Denovilliers筋膜的后叶在解剖上并不存在,实际上是直肠固有筋膜。Heald最初提出TME时,提倡一并切除Denovilliers筋膜,但目前更倾向于选择在Denonvilliers筋膜内侧解剖,这样有利于神经血管束(Neuro-vascularbundle,NVB)的保护。
切开直肠尿道肌,宽阔的前列腺后间隙便能显露。继续向头侧推进,可以看到Denonvilliers筋膜在前列腺后壁的附着处。Denonvilliers筋膜在前列腺后壁的附着处是第2个重要的手术解剖标志(见封三,图2)。此附着非常紧密,切开后便进入下一个疏松间隙,12点方向开始看到精囊腺。继续向头侧游离,可以看到表面有细小血管的瓷白色腹膜返折(见封三,图3)。切开腹膜,盆腔的手术野就会与腹腔镜组术野相通。
由于腹腔镜多采用脉冲式气腹装置,一旦两者相通,便会发生’盆腔呼吸’的现象,盆腔术野会随充气周期性不停摆动。对于TaTME这种要求精细操作的手术影响是巨大的,在肛侧TaTME手术操作完全结束前不要轻易联通2个术野。
4 直肠后壁的相关解剖
直肠后方剥离的首要解剖标志是Hiatal韧带,也叫作直肠尾骨肌,其本质是联合纵肌在直肠后壁6点方向的增厚。广义上说,包括直肠尿道肌在内的环绕肛提肌裂孔1周的平滑肌都可以称为Hiatal韧带。后壁剥离开始后,很快即可见到白色的肌纤维,应选择先由较为疏松的4点和8点方向突破,再切开6点方向的Hiatal韧带比较清晰(见封三,图4)。切开后,宽阔的直肠后间隙得以显露。由于TaTME是由肛侧向口侧推进,切开线实际往往处于骨盆内筋膜的深面。
手术操作至此时应重新确认以下3个解剖结构:(1)直肠固有筋膜;(2)肛提肌;(3)肛提肌表面的骨盆内筋膜,确保始终走行在直肠固有筋膜和骨盆内筋膜之间的正确层面。一旦迷失解剖标志,不但会造成直肠后壁的游离向深面偏离,损伤骶前静脉丛造成难以控制的大出血;更会影响对后续侧方游离层面的判断。
继续向头侧前进,便进入疏松的’神圣平面’。直至S3~S4附近(距肛提肌口侧3~5 cm)会遇到Waldeyer筋膜,也叫作直肠骶骨筋膜或直肠后筋膜。此处也是’L’型骨盆腔的拐点,疏松结构突然转为相对致密(致密程度因人而异)的地方。Waldeyer筋膜并不是连接骶前筋膜和直肠固有筋膜独立存在的结构(见封三,图5),其间不含有任何血管神经结构。
此’筋膜’的形成,可能的原因是下腹神经前筋膜增厚,并且直肠固有筋膜、下腹神经前筋膜及骶前筋膜在此处结合较其他位置更为紧密。无论经腹还是经肛,在此处都容易误入更深的层面造成骶前血管的损伤。手术中不妨将此处作为直肠后壁游离经腹和经肛的汇合点,发挥各自的角度优势,避免损伤。
5 直肠侧壁的相关解剖
盆神经丛由腹下神经(交感神经)和盆内脏神经(副交感神经)构成,为一扁平状的神经丛,总体来讲盆神经丛分为前支和后支。前支与前列腺或阴道旁的血管等构成神经血管束(Neurovascular bundles,NVB),损伤前支可导致排尿和性功能障碍。后支则走行于直肠两侧及侧后方,分布到直肠和肛管,损伤后支导致肛门内括约肌功能不佳,肛门静息压下降,造成肛门控便能力受损。
TaTME最大的陷阱便是突破盆丛,误入盆腔侧方的疏松间隙,造成盆丛神经、髂内血管及其分支乃至输尿管、尿道的损伤。为了避免此类损伤的发生,首先在直肠后壁的剥离时,一定要正确识别平面,并平稳过渡至侧方。其次,足够强的对抗牵拉是正确识别直肠固有筋膜和盆神经丛两者间隙的关键,这点经肛与经腹入路是同样的。
直肠中动脉由髂内动脉或分支发出后穿过盆丛,两者伴行分布向直肠,该结构被称为’直肠侧韧带’。无论延直肠的纵轴还是环周,均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不是纤细菲薄的结构(见封三,图6)。由盆丛发出支配直肠的内脏神经是直肠侧韧带的恒定组成部分,而直肠中动、静脉出现的概率仅有22.2%,双侧同时出现的概率更低。
直肠侧韧带是直肠固有筋膜和盆神经丛两者之间的联系。在理解其构成后,借助腔镜的放大作用,可以分辨出呈放射状排列的神经及血管,在其行程的稍外侧作为切除线,便可以兼顾肿瘤根治和神经保护。
NVB也由盆丛发出,层面上位于Denovilliers筋膜的外侧,于尿道/阴道-直肠间沟持续向肛侧走行。TaTME手术过程中在游离过程中截石位的10点及2点方向容易出血,就与NVB仍有向直肠的分支有关(见封三,图7)。
另外,NVB的直肠支与直肠侧韧带间存在1个潜在的疏松间隙,此处的手术操作技巧与直肠侧韧带的游离类似,过于偏向外侧就会有损伤NVB之虞。笔者认为,在直肠癌手术日益强调神经保护的今天,将盆神经丛-直肠侧韧带-NVB作为统一的整体看待也许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
6 小结
TaTME是ISR及Miles手术会阴侧操作的延续,由肉眼下操作转为镜下操作,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对于直肠癌,腹腔镜技术将开腹手术中的不可见变为可见,而TaTME将腹腔镜手术中的不可见变为可见,是直肠癌手术历史发展的延续。
外科学源于解剖学,对不同结构的分类、命名贯穿于外科学发展的始终。TaTME给了外科医师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盆底,丰富了对于这些解剖结构的认识。希望本文能给初学者提供些许指引,为大家的交流带来共同的解剖语言。
参考文献【略】
文章来源:国际外科学杂志, 2019,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