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微风读书会”可以订阅哦
父亲和他的烟锅
没有烟火的世界是一个冷清的世界。
没有烟火的寺庙是一个凄凉的寺庙。
不食烟火的人,是什么样的呢?不好说。
在渭北乡下,人们把吃烟叫作烟火,大多是吃旱烟,只有为数不多的富有人家吸纸烟或者吃水烟,甚或抽大烟。吃烟人的一致说词是,烟能熏虫豸,劳作困了就地一躺,蛇见不得烟味所以不敢伤人。其实这话经不住考证,杏洼的侯三拐烟火极重,还不是叫蛇咬死了。
世间,人分三六九等,平头百姓耍不起阔人的牌子,只得抽旱烟末子。平日里,你看看身边的人,不是脖项里插着烟锅,腰里别着烟锅,就是手里提着烟锅,嘴里噙着烟锅。你到集市上去,卖烟叶的摊子摆得一排一排,亮黄亮黄的烟叶码成捆,地面铺片油布,放着揉好的烟末,供买烟的品尝。摊主鼻梁上架着一副月饼似的大镜砣,吊着烟袋一边很有滋味地吃烟,一边向围蹲的买主说道他的烟叶:你看看这成色,甘肃唐台的,老革命当年打游击,就抽的这旱烟。解放后进了北京城,捎话带信想吃唐台的旱烟。尝过烟的人都说好。
我家丁口众,父亲为了省钱就自种旱烟。每年开春,在自留地挖一片地种小叶烟。等烟苗一天天长上来,顶着火烧火燎的日头,蹲在地里一窝窝地上肥,一株株地打岔。进入秋季,叶片肥厚地鼓暴起来,墨绿一片。待烟叶熟了,又一瓣一瓣地扳下来,用绳子串起来,挂在窑洞的山墙上晾晒。烟叶一天天地萎缩,渐渐由绿变黄,山风吹过,满院飘散着烟草的香气。这是父亲为他准备的另一种粮食。
吃旱烟就得有器具——烟锅,就像做饭得有锅一样。我十分钦佩老先人造词的智慧,把吃烟与吃饭相提并论,都蕴含着烟火气。烟锅也是有讲究的,从这器物上能分出贫富之别。富户人家的烟锅安着白铜头,脊上匹着“鞍子”,雕刻有龙凤花草的图案,光彩熠熠,精致玲珑,就是一件工艺品;烟杆为空心檀木或对节木,色沉古雅;烟嘴不是玉石便是玛瑙,晶润细腻,清亮剔透。平日出门,手里捏着一根白蒿搓成的火绳,把长长的烟锅噙在嘴里吸溜,悠悠地吐出一圈圈青烟。腰间吊搭着绣有花草的烟袋,走动起来有节奏地拍打着大腿。鞋子倒趿,迈着八字步,悠然自得地转村游街。偶见相好的,呵呵一笑,露出几颗金牙,便把烟锅从嘴里取出,擦拭一番,让给对方吃。烟锅成了炫耀身份的标志物。
清贫人家的烟锅散发着穷气。如我父亲,买一个黄铜烟锅头,不修不饰,砍一截竹竿安上,无嘴儿,也没有烟袋,扯一张皮实的纸包着烟末。兜里装只火镰,烟瘾发了,撕出灰水浸泡过的棉套子,俗名“火草”,按在火石上用簸箕形火镰一次次地撇打,待火星燃着了火草,摁在烟锅上努力地吸,便有了烟火。吃毕了,烟灰朝鞋帮上一掸,别在裤带上忙手里的活。父亲烟锅过于寒碜,让我也没了脸面:烟锅不值钱,父亲也就不太经心,烟锅往往从裤带上溜掉,烟锅丢了,没奈何,父亲就撕我的作业本,卷喇叭筒。父子俩常为这事闹不快——你有用的他撕了,无用的他却不撕。每当我向他发火时,他总是谦卑地笑,好像自己做了贼一样。过后想起父亲那张笑脸,心里总是莫名地发酸,后悔不该对一个善良的父亲如此不敬。有一天他赶集回来,坐在炕沿上逮着烟锅吃烟,这让我莫名其妙,便问:你买烟锅了?他笑着说:路上拾下的。他把烟锅递给我看,这比他丢掉的烟锅要好多了,起码有一个烟嘴。烟嘴是粗石打磨的,还落下一圈牙痕。我猜度丢烟锅者的社会地位与我父亲一样。
烟锅不只用来吃烟,也用来吓唬人。我小时很顽皮,暑伏天常常招朋引伴,去村头的涝池凫水。涝池水好深,已经淹死过一个小孩。父亲怕出事,禁断我去耍水,我总是当耳旁风。有一回耍到时辰过午,才精着身子,糊着两脚泥巴回到家,气得父亲眼睛都立了起来,举起烟锅要打我。我心想,那家伙抡下来,非砸出一个大包不可,便撒腿就跑,钻进麻地不敢出来,惹得父亲和母亲一路争吵,一路找寻。那扯长声腔的呼叫极度急切,又异常怜爱,我藏在麻地里不敢应声。世间,大人与小孩似乎永远是对立的,大人不能理解小孩池塘里玩水的欢快,小孩也难能理解大人对于生命的关切。我小时候常得眼病,先是一只眼红肿,后来另一只眼也染上了,双目如烂桃。父亲就用烟锅里的烟油(烟屎)在眼皮上抹,多日后就好了。蚕屎(蚕沙)可以明目,烟屎能治眼疾,这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知识。
父亲吃烟的情绪和姿态,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储存着。田间劳作歇缓的间隙,男社员吃着烟,吐着雾,父亲忘记带烟锅,只好干坐,等别人过罢了瘾,便借过来吃。借也要看人家的脸色和交往的薄厚,吃过烟万死不能评说人家烟叶的软硬优劣,要重新装上一锅烟,用手抹净烟嘴,双手递过去,表示敬谢。每当看到父亲为吃一锅烟如此卑下,心里便有一种可怜他的感觉。
忙完生产队的活,就紧打火闹忙家里的活。十多口人张嘴吃饭,推碨磨面成了日常的必须。碨子安在厨窑里,夜里,在昏暗的油灯下,父亲抱着碨担在磨道里来回转圈,脚下带起一团尘土,弥漫了窑洞。老碨子发出沉闷的轰隆声,伴随着母亲箩面的咣当声,一直持续到夜半时分。父亲推累了,背靠着灶火的风箱,急急忙忙吃一锅烟,那吃相是匆促的、敷衍的,吧唧吧唧吸几口,烟未燃尽,就又紧迫地起身推磨。在他心里,一家人的吃饭是大事,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哪能像日子过得滋润的人家消消停停,细细长长地品味呢?我父亲累啊!
瓜菜代那些年,自打春到麦收前,正是青黄不接的困荒时月,一家人吃了上顿愁下顿,乡下把这种景况叫“打断顿”,父亲整天一脸愁容。一天黄昏,我见他一人木然地蹴在院边,望着远处的村舍出神。搅肠翻肚的惆怅与煎熬,让他今一口明一口地吃烟,青烟一团又一团地喷吐着,心事重重地笼罩和模糊着他清瘦的身影,如凝滞的云久久不散。此刻,我从父亲的吃烟中清楚地体味到生计追逼的困顿。他把一切愁苦独自隐埋在心底,借着吃烟予以释缓。这种貌似沉静的安宁,透露出的却是假象,他忧愁不安啊!尽管如此,他对子女还是不动声色:天爷黑了,明日会亮;出了深山,就是平原;好日子能等住,不会受饿一辈子。回想起父亲当年的这些话,多少带有预言家的远见和哲学家的辩证。但说穿了,只不过是给自家娃娃长精神,指出一个假设的寄望。殊不知,为这个好日子我们苦苦盼待、艰难挣扎了二十多年。父亲在生活艰困中吃的是愁烟。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我放学回来,父亲对我说:咱到你姨家借粮,带的口袋、担、绳我都预备好了。我姨家地处荒僻的山坡,那里地广人稀,粮食略有节余。时节正是农历四月初,没有月光,四下一片墨黑。父子俩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路。路边的麦田在夜风中骚动,发出唰唰唰的波浪声,像一群狼在麦田里乱窜。茫茫的原野上哪里都有死人的坟墓,我读书得知,鬼白日隐藏在地下,夜晚出来聚会。这么一想,心里就怕得要紧,我被揪成了一个疙瘩。父亲给我壮胆,就拉话:到了你姨家,千万不要弄出声响,那是你姨私藏的一点粮食,瞒着家人借给咱度荒。脚到姨家已是夜半时分,整个山庄沉没在毫无声息的死寂之中。姨家的窑洞临着院墙,父亲按约定的暗号,扔下几块土蛋儿,不多时一口袋粮食便从墙里溜到墙外。这是一场真正的哑剧,一切都演得天衣无缝。父子俩摸黑分装好粮食,便挑着上山。爬上坡顶,隐隐听到远处狼哭泣般的叫声。父亲把我让在前边,他殿后。进得家门,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母亲张罗着粮食,父亲靠着炕沿吃烟。有了这一把粮食接济,足可疗饥。父亲眉宇间绽露出丝丝欣然之色,姿态是自如的。压在他心中的一块巨石搬走了,一种获救感让他吃起烟来轻松自在,缕缕青烟袅袅如闲云,投射到墙洼上的身影沉静如弥佛。这是消解胸中块垒,开人心灵洞府的一次享受。
我祖母是个性情暴躁的人,和心地温良的爷爷过不在一起,就像卖面的见不得卖石灰的。爷爷死后,她患上多种疾病,躺在炕上一直吃药也无效力。最明显的症状是身下不断流出一种浓稠的液体,腥臭难闻。当时正逢盛夏,苍蝇成群地趴在她裤子上。母亲不停地给她换裤子,晚上父亲将脏污不堪的衣服拿到村西头的小涝池去洗。久而久之,那涝池的水变得恶臭,饲养员去饮牲口,牲口拧头不喝,更别说人去洗衣了。祖母垂危之际,父亲愁颜加重,做老衣、做棺材、打墓、祭奠、送葬一摊事都要他亲自料理。家贫如洗,费用从哪里来呢?他愁肠万结,困窘得常常独自吃闷烟,深深地吸几口,又重重地吐出来,烟雾是块状的,如行雨前聚集的团团黑云。父亲的心是苦涩的,他在吃苦烟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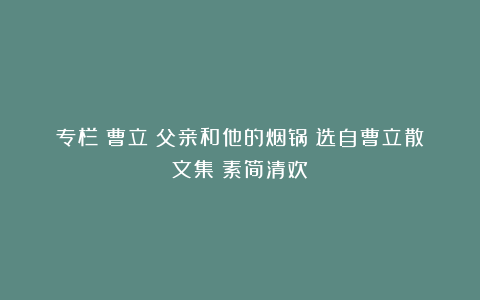
那年,我在离家不远的一个乡镇任职,这里与陇东隔沟相望,地处塬面两镇的夹心地带,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为了活跃当地的物流商贸,乡党委决定设立集市,请来县剧团助兴,唱了七天大戏。我接父亲来看戏,吃过饭,他神态安详地坐在沙发上正要抽旱烟,我急忙给他换成卷烟。他点起一支,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跟往常端着烟锅的姿势一模一样。庄稼汉父亲有他固有的吃烟习惯,对于新事物的出现,接纳的方式依旧古老保守。不过,此刻我更为关注的是他的精神状态——透露出苦尽甘来的满足感。在他几十年的吃烟史中,似乎这是最典雅、最开心的一次,留下了不一样的影像。父亲问:这烟贵吗?我造谎说很便宜,他脸上泛起释然的表情,吐出的轻烟飘散着浓郁的香味和清心涤虑般的气息。这烟他吃得多么香甜啊!历尽苦悲人生的他,感受到足以自慰的尊荣,哪怕这种尊荣像流星一样倏然即逝。乡下流传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人活一口气。这气就是志气和精神。父亲生养了九个子女,这是他人生唯一骄傲的资本。用他的话说,有人,人有志气,日子就有指望。我们不像殷实人家,靠祖祖辈辈积攒的丰厚财产生活,咱穷,只有人。在艰难困苦、遭欺受辱中,父亲咬着牙,鼓着劲,撑起了这个家庭,虽说少吃缺穿,像吊猫吊狗一样也都拉扯大了。倘若我是一家之主,我恐难为之啊!父亲是一位生存能力极强的人,无论心智还是骨气,他的坚毅和忍耐,让我终生感佩,他是我精神庙堂的一尊神。
打那次看戏之后,我每年给父亲买卷烟,替代了古老的旱烟。料想不到的是,父亲突然戒烟,多好的卷烟也不再招嘴。为了生命?为了节俭?我不知道。直到他去世后,我们从柜子里翻弄出整盒整盒已经霉变的卷烟,勾连出我一腔酸悲,抱怨他为何短自己口份。父亲走了,但他的灵魂还在。思量之后,我佩服父亲戒烟的决心和毅力:在他人生最后的五年中,彻底告别了与他悲欢相随的烟锅。因着父亲平凡的生命与烟火互有深深的渊源,营葬中为安抚他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不短精神,我们请木匠做了一张小方桌,油了漆,下葬时放在他的灵柩前,桌上供着他生前用过的石头嘴烟锅。有这一祭物,他总不再孤独。铭曰:奉安无罕物,独有一烟锅。劳人相厮守,神灵足可乐。
立足咸阳 面向陕西 走向全国
编 辑:宇星 | 审 核:花儿
*声明:除原创内容及特别说明之外,推送稿件的图、文字均来自网络及各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立即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