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皇河水裹挟着晨间的凉意,穿过淮北平原,也悄然浸染了丘府高墙深院内的每一寸角落。少夫人祝小芝启程去南京探望妹妹丘世宁后,丘府原本井然有序的日子便如同失了主轴的纺车,骤然乱作一团。
从前李银锁只需料理些内宅琐事,如今偌大的丘府、田庄、仆役,千头万绪都沉沉压在她单薄的肩上。她坐在账房内,指尖拨动算珠,声音在寂静里显得格外急促,鬓角渗出细密的汗珠,竟将黄铜算盘杆也润得滑腻难握。窗外,连太皇河的水声也仿佛变得格外喧嚣。
真正让李银锁忧心如焚的,是田庄那帮新雇来的短工。那些人如同田埂间难以拔除的顽草,干活拖沓敷衍不说,竟还暗中使坏。牛腿被“无意”打瘸,崭新的犁头莫名其妙在田垄间崩断豁口。账房递上来的损失单子一天比一天触目惊心,李银锁的心,也一日沉过一日。
必须得有人去弹压,李银锁思来想去,唯有庄头丘世园,少爷丘世裕的堂兄弟,性子虽暴烈如雷,却素来管束得动庄子上那些粗野汉子。从前祝小芝在时,只需淡淡几句,便如同给这头套上了辔头。
李银锁在通往庄园的小径上踟蹰良久,终于鼓起勇气,站在了丘世园那间充斥着汗味与皮革气息的房门外。
“世园兄弟,”她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轻颤,“田庄上那些短工,闹得实在不像话,劳烦你……去约束一二?”
丘世园正擦拭他那条油亮的皮鞭,闻言猛地抬头,目光如鞭梢般扫过李银锁局促的脸。他嘴角一撇,露出毫不掩饰的轻蔑:“约束?呵!李姨娘,您这金尊玉贵的手,还是摆弄您的胭脂水粉去吧!田庄上的事,水深泥烂,您搅和不起!爷们儿该怎么管,用不着一个屋里头的人来指手画脚!”
“可是……”李银锁还想再分说几句。
“没什么可是!”丘世园霍地站起,将手中鞭子“啪”地一声重重摔在案几上,震得茶碗叮当乱响。他抓起桌上几张写满短工劣迹的纸,看也不看,三两下揉作一团,狠狠掷向李银锁脚边,“少拿这些鸡毛蒜皮来烦我!” 那纸团滚落脚边,像一团肮脏的雪,冰冷地嘲笑着她的无力。
李银锁僵立在原地,被那声断喝和掷地的纸团钉住了脚步,脸上最后一点血色褪尽。她默默弯腰,指尖冰凉地拾起那团羞辱,再未发一言,转身离开。丘世园那毫不掩饰的鄙夷,仿佛带着芒刺的风,刮过她单薄的背脊,直直钻进心里。
她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那间略显清冷的小院,廊下挂着的鸟雀在笼中啁啾跳跃,衬得她心头愈发沉重。能找谁?她枯坐良久,窗外日影一点点偏斜,直到一个名字倏然划过脑海。
刘桃子!商队大掌柜丘世安的妻子,丘府大管家丘尊农的儿媳。这女子素来是祝小芝最亲厚的姐妹,性子爽利,手腕玲珑,在丘府上下人缘极好。她眼下正在府中!
一丝微弱的希望,如同太皇河上穿透厚重晨雾的第一缕阳光,艰难地渗了进来。
李银锁几乎是立刻起身,脚步匆匆地寻到了刘桃子所居的跨院。院中花木扶疏,刘桃子正悠闲地坐在藤架下,手中一把精巧的团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看着小丫鬟侍弄花草。
“桃子姐姐……”李银锁的声音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干涩和急切。
刘桃子闻声抬头,那双总是含着三分笑意的眼睛在银锁憔悴的脸上略略一转,便已了然。她放下团扇,并未起身,只是拍了拍身旁的石凳:“银锁妹子来了?瞧这眉头皱的,天又没塌下来!坐下说话!”
李银锁依言坐下,将田庄短工如何惫懒、如何暗中破坏、自己又如何被丘世园冷言顶撞的委屈,一股脑儿倒了出来,说到最后,声音已带上了哽咽的尾音。
刘桃子安静听着,指间拈着一朵凋落的茉莉花,轻轻捻动。待银锁说完,她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自有分量:“世园那个炮仗性子,点火就着,除了嫂子,谁的面子也不给,你犯不着跟他硬顶!”
“至于田庄上那帮混账东西……”她微微一笑,那笑容里却无多少暖意,反而透出几分洞悉世情的锐利,“不过是欺生,看你脸嫩罢了。明儿一早,我同你去庄上走一遭!”
翌日清晨,薄雾未散。李银锁与刘桃子同乘一辆青帷小车,吱吱呀呀地驶向太皇河下游的田庄。车还未停稳,远远便望见田埂上聚着一堆人,吵吵嚷嚷,如同炸了窝的马蜂。一个叫王老七的刺头短工正梗着脖子,唾沫横飞地跟管事理论,脚边倒着一架散了架的曲辕犁,旁边一头老黄牛不安地踏着蹄子,一条后腿明显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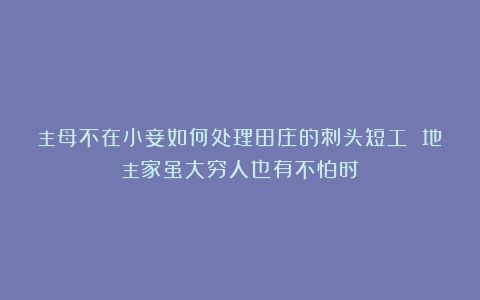
“放屁!分明是这犁头不结实,老牛自己绊了腿!想赖到爷们儿头上?门儿都没有!”王老七的声音又粗又响,震得田埂上的露珠都在颤。管事气得脸色发青,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众短工或站或蹲,脸上挂着看戏的神情,间或夹杂几声不怀好意的哄笑。
青帷小车在泥泞的田埂尽头停稳。李银锁深吸一口气,正要掀帘下车,刘桃子却轻轻按住了她的手背。刘桃子自己先不紧不慢地探身出来,站稳后,才回身朝车内伸出手。那姿态,仿佛迎接的不是同府的小妾,而是什么贵客。李银锁微微一怔,旋即明白过来,借着刘桃子稳稳的搀扶,也仪态端方地下了车。
两人站定,刘桃子并不看那吵嚷的中心,目光平静地扫过整个田头。方才还嗡嗡作响的喧嚣,竟在她这无声的环视中,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脖子,一点点低弱下去,直至鸦雀无声。那些原本或站或蹲、面带讥诮的短工们,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收敛了神色。王老七梗着的脖子也软了几分,眼神开始躲闪。
“哟,好热闹啊!”刘桃子这才开口,声音不高不低,清朗朗地传开去,脸上甚至还带着点温和的笑意,径直走向那散了架的曲辕犁和跛腿的老牛。她围着那牛慢慢踱了两步,视线落在那条明显肿胀的伤腿上,轻轻“啧”了一声,仿佛只是看到一件寻常的憾事。
“可惜了,”她摇摇头,语气平淡得如同在谈论天气,“好好一头能下力的牲口,腿成了这样。” 她目光转向旁边那堆烂木头似的犁具残骸,又转向噤若寒蝉的王老七,笑容依旧挂在唇边,声音却像浸了太皇河的初春水,带着凉意,“王老七,是吧?你方才说,是这犁头自个儿不结实,老牛自个儿绊了腿?”
王老七喉头滚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在刘桃子那双看似带笑、实则洞悉一切的目光下,竟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只觉后背一阵阵发凉。
“嗯,”刘桃子点了点头,仿佛接受了他的沉默,话锋却陡然一转,轻飘飘地抛下一句,“那倒也好。既然这牛腿折了,留着也是白费草料,横竖不能下田了。”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清晰地吩咐道,“管事,回头叫厨房的胡大来,把这牛牵回去。立冬还早,但府里上下,提前添道酱牛肉,倒也不错!”
她话音刚落,王老七的脸色“唰”地变得惨白如纸,豆大的汗珠瞬间从额角滚落下来。他猛地扑到刘桃子脚边,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少奶奶!少奶奶开恩呐!是小的瞎了狗眼!是小的……是小的不小心!小的该死!小的这就去找兽医!这牛……这牛还能治!求您千万别……”他语无伦次地哀告着,涕泪横流。让那牛受点小伤可以,若把牛使死了他自己也就交代了?
刘桃子微微侧身,避开他的拉扯,脸上那点温和的笑意终于彻底敛去,只余下平静的威严:“哦?不是犁头不结实,也不是牛自己绊的?那是什么?”
“是小的!是小的手笨!干活没留神!”王老七磕头如捣蒜,再不敢有半分狡辩。
“起来吧!”刘桃子声音恢复了平淡,“念你初犯。这牛,赶紧找兽医瞧。犁钱,从你工钱里扣一半。另一半……”她目光扫过周围那些缩着脖子的短工,“你们这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一起担了。可有不服?”
“服!服!谢少奶奶开恩!”短工们哪里还敢有二话,七嘴八舌地应承着,个个把头点得像啄米的小鸡。
一场风波,就在刘桃子三言两语、举重若轻间,化为无形。接下来的时日,李银锁但凡遇到棘手的事务,便去寻刘桃子商量。无论是外头铺子送来的含糊账目,还是府里仆妇间的龃龉,只要刘桃子那双含笑的眼睛看过来,再难缠的人事,也似乎有了捋顺的线头。
田庄上的消息也日日好转,短工们老实勤快了许多,再不见那些莫名其妙的损耗。丘府这架一度濒临散架的纺车,终于又在某种无形的秩序下,重新吱吱呀呀地转动起来。
晚风送爽,吹散了白日的燥热。庭院里,李银锁和刘桃子坐在廊下小几旁,一盏清茶,几碟时新果子。账册摊开在银锁面前,她手中的笔却悬着,久久未落。远处隐约传来太皇河亘古不变的流水声,带着平原的沉稳与苍茫。
“桃子姐姐,”李银锁终于放下笔,声音低低的,带着一种卸下重负后的疲惫与释然,“这些天,多亏有你!” 她望着刘桃子那张在灯下愈发显得温润平和的脸,轻声道,“看着你处事,我才明白,有些事,硬顶是顶不过去的。” 她顿了顿,目光落在自己纤细、因连日拨算盘而微微发红的手指上,声音更低了些,“有些位置,不是强求就能坐得稳的。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
刘桃子闻言,端起茶盏的手微微一顿。她没有立刻接话,只是轻轻吹开浮在水面的碧绿茶梗,啜饮了一小口。茶烟袅袅,模糊了她唇边那抹惯常的笑意,只余下眼底一片澄澈的了然。她放下茶盏,伸出手,温热的手掌在李银锁搁在几上的手背上,安抚似的轻轻拍了拍。那动作极轻,却仿佛带着一种洞悉世情后的温厚力量。
“银锁,”她的声音和这初夏的晚风一样,轻缓而熨帖,“各人有各人的缘法,各人也有各人的担子。这丘府的天塌不下来,嫂子也快回来了。你管好你该管的,能稳稳当当的,就是本事!”
李银锁心头那点沉甸甸的、说不清是委屈还是自惭的块垒,被这温言软语和手背上传来的暖意,一点点熨平了。她垂眸,看着刘桃子那只骨节分明、因常年打理事务而显得比闺阁女子略粗糙些的手,良久,终于极轻、却无比清晰地“嗯”了一声。太皇河的水声依旧在远处低语,只是此刻听来,已不再令人心烦意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