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墉于画,以书入道。篆籀的线质与行草的笔法,贯注于画纸之上。他深知,中国画本是线的雄辩,笔墨根基皆源于书法。故其笔下花鸟,根骨挺立,线条正而劲道,如根须扎入纸底。
吴昌硕与任伯年对他而言,并非炫目的灯彩,而似山间溪水,无痕地浸润过他多年的砚田;他深信创新如酿新酒,只能静待时光的酝酿——刻意催之,反败其味,僵其画意。
瓶花这一寻常之物,却成为周墉笔底常客。
起初不过图其分明的轮廓:白瓷、清水、红花,便于练笔时观照。
然而细究之下,瓶花竟渐渐显出一种深藏不露的意味:花枝插于瓶中,虽姿态舒展,根脉却早已断绝;色彩娇艳,却注定在案头一日日走向萎谢。此种情境,暗暗与人世间诸多难以言说的遭际相合。
他曾见过不少瓶花画作。有人精雕细刻,连花瓣上的露珠也纤毫毕现;有人挥洒写意,寥寥数笔便捉住神韵。前者自矜于技巧之工,后者陶醉于气韵之逸。
而周墉伏案之际,却常常生出一种被审视之感——仿佛瓶中之花正凝视着他,那目光里似有三分戏谑,又含着七分悲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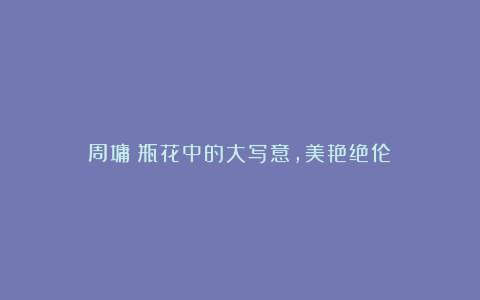
花不语,却比许多喧嚣的言语更为诚实。它从不掩饰自己行将枯萎的脉络,亦不伪作娇艳的姿态。今日盛开便盛放,明日凋零便坦然萎落,从不曾迁就画者的窘迫。
周墉坦言,有时画至中途,案头瓶花已悄然飘落两三瓣,他只得将这凋零也纳入画中。待画成,竟比原先构想的更添一种真实——那是一种拒绝粉饰、直面衰残的真实。
作画者与插花者,心意竟在瓶口相汇。周墉道破其中意味:画瓶花之人,大抵难逃一个“痴”字。
明知留不住,偏要留;明知画不像,偏要画。此般痴心,与那将花枝插入瓶中的人,何尝有异?不过是各自执拗,各自在无常中试图挽留一点浮光掠影。
最终,花必凋萎,画亦会褪色。而那驻足于画前的人,又能真正留住几分当初凝望瓶花时的心情呢?
瓶花静立案头,不过一瞬的光华;而周墉以笔与之相对,在纸墨间捕捉其形,亦是在记录那永不可被真正挽留的瞬间之魂。
花之易逝,画之恒存,这悖论本身,便是一幅永未完成的画,是生命在纸上的回响。
画者之痴,不在永存,而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那瓶花与画纸之间,横亘着永恒与短暂的鸿沟,周墉的笔,不过是在这鸿沟上悬起一道细如发丝的索桥——他走过,看花者亦走过,桥下便是时光奔涌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