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一次去平顶山,都要抽空拐到这个地方,到园里走一走。
这个地方,你知道的,是郏县茨芭乡;这个园,你熟悉的,就是三苏园。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这是早年苏轼(1079年,42岁)写在《狱中寄子由》二首中的一句。那时,他还想着死后随便找一个“青山”埋掉;但22年后(1101年,64岁),他遇赦从儋州北归,途经常州暴病,弥留之际提笔给苏辙写了一封信,嘱托“即死,葬我嵩山下”。
次年,苏轼的三个儿子迈、迨、过扶柩将其迁葬于郏城钧台乡上瑞里,也即现在的郏县茨芭乡“小峨眉”。
是处青山,真有幸!苏轼临终,一定不会再“独伤神”了!
1094年(57岁),苏轼罢定州任,以朝奉郎的身份知广东英州军州事,途中来到苏辙任职的汝州,游兴大发,拜郏城中顶莲花山上的老子行宫。
郏县地方志记载,当时他突然发现上瑞里的山体分东西两道,翠林密布、景色旖旎,不由喟然叹道:“类蜀之峨眉山也!”这,便是“小峨眉”一说的由来。
不过,“小峨眉”的称呼或许在宋时就有。苏辙的迎柩文中就曾说,“地虽郏鄏,山曰峨眉,天实命之,岂人也哉!”
现在的“小峨眉”,已变成了北方平原地区常见的黛眉山丘。我来多次,也只见田间阡陌纵横、路旁瓦舍林立,附近的山体,只显出深深浅浅的“青”,却没有看到丛林密布的绿和秀。
千年过去,沧海桑田真的塑造了一切?
但那时的苏东坡,或许真的在这片应许之地发现了他家乡峨眉山的影子,最起码,是一种家乡情怀的寄托。
他一生辗转多地,命运多舛,期间为开荒自给或遂“归田之愿”,先后在黄州(1080~1084)、常州(1084)、惠州(1094)、汝州(1094,留一子定居)、儋州(1097)“请地”或“买田”,没想到,最终他想起归去来兮的终极之地,还是这个离嵩山最近的地方。
1112年,也即他去世11年之后,一生与他患难与共、手足情深的苏辙也不在了,遂也葬在此处,圆了早年“夜雨对床”之志。
当然,现有专家论证,苏轼遗愿葬此,理由一在于苏轼子孙已经多散居于中原地带,且苏辙已在临汝买地,家人和族人也多在此安葬;二在于“以汴京东近,表恋阙之微诚”,仿效包拯、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京畿附近与“官家”相守相望;三如苏辙在祭奠家人的祭文中所说,“葬我嵩少,土厚水深”“举棺从之,土厚且坚”。
——以宋朝人从上到下对堪舆学的笃信、沉迷程度来看,这最后一条,或许是最根本的原因。
不管怎样,今天的茨芭乡“小峨眉”,或曰旧时的钧台乡上瑞里,因接纳了苏东坡这样一个千古难见的人物——不,还有他的弟弟苏辙和其他族人,以及苏老泉的“衣冠”——因而显得“山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这个地方,堪称福地。“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话,用在“托体同山阿”的苏轼这里,何尝不可同比?
只是,上瑞里这里的山,现在还不是“名山”。它本可以成为名山的,但它没有努力去做到。
整个平顶山,以“平顶”二字先导,连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也没把握住。小峨眉和尧山,当真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
2
我们都爱苏东坡,他,已经与我们许多人的一生如影随形。
每次来到上瑞里,沉浸于三苏园寂寥、安静甚至有点荒凉的氛围里,我都会时走时歇,任那些缤纷轻盈的诗句在四周如蝴蝶一般翩翩舞动。
同样像是在穿越他的一生。
先是三苏园那新修的大门,屋脊飞扬,一左一右两棵高大的旱柳在迎风吹拂,似两个人在挥手致意。“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这一首,苏轼写于郑州西门外,“夜雨对床”的宏愿自此发下。
在郑州二七商圈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曾多次到这个地方追怀他们兄弟俩的砥足情深,奈何那里现在只有两尊兄弟拱手揖别的雕像,而且还放置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
但在三苏园,他们是主角。进得园中,一条甬道铺向远方,沿路有湖,湖畔有树,大片空着的土地似是管理部门还想不起到底要在上面填充什么。
“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凌虚台记》)、“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到陕西凤翔府担任签书判官,3年中创作了130多首诗歌,内心并没有留白,恰如他在诗中所写,“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
今天的凤翔,已将他当年疏浚而成的东湖变成了一座公园,公园正中心,也树立了一座巨大的苏轼石像,附近还建有苏轼祠堂、凌虚台和喜雨亭等与他相关的纪念性建筑,算得上是对这位诗人遥远的隔空唱和。
但凤翔东湖,毕竟比不得杭州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饮湖上初晴后雨》)、“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法惠寺横翠阁》)。
苏东坡先后两次到杭州任职(1071-1073年任通判,1089-1091年任知州),现在传下来的与西湖相关的诗文,据统计就有30多篇(首)。
今天的杭州人为纪念他,修复了苏堤、六和塔等东坡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打造出“苏堤春晓”景观带,同时建成苏东坡文化公园,以数字化方式展示苏轼的诗词世界与治水智慧,那是真的拿他为城市之魂。
柔情万种转折之处,就是豪情万丈。
听,“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江城子·密州出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是来到密州(现诸城)之后苏东坡发出的千古浩叹(1074-1076年),自此,他被称为北宋诗词“豪放派”的开山鼻祖。
我望向三苏园四周的远山,寻找苏轼上山狩猎的身影,却只有一阵风吹来。想起去年去山东潍坊诸城市,在古城墙前仰望苏东坡那宏伟的雕像,并登临重修后的超然台和黄茅岗东坡狩猎园,恍然之间像是骑上了一匹烈马,要一直追着苏公背影而去。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超然台记》)。
诸城是我去过的复建东坡遗迹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有气魄、有格局。类似的,在当今的徐州、黄州,我们同样能看到如同在东坡诗词中咏唱过的黄楼、放鹤亭、东坡赤壁、遗爱湖,更不用说东坡纪念馆、东坡书院这样的纪念园地了,处处都是活着的苏东坡。
也难怪,自在湖州被逮并被贬到黄州后,东坡一方面继续延续在密州、徐州那样的豪情壮志,吟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样的词句,另一方面又难免会发出款曲徘徊之叹:“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琴诗》)、“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滔天”(《南塘》)、“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满庭芳》)。
很遗憾,这样珠玉瑰丽的文字以及展示的境界,并没有在现在的三苏园展现出来。
特别是当我一路走到三苏园的核心地带——祭奠三苏的祠堂,那种简陋、粗糙、破旧的景象让我的心情一下子压抑起来:门楼、牌坊几乎和门口的石马、瑞兽、石像生一般低矮,古柏、碑刻带着古旧的气息肃穆而立,虽让人油然而生敬慕,却终究难以相信,这能与苏轼三父子那博大、清新、奇崛的气象格局相匹配。
三苏坟入口
一个有趣而达观的灵魂,我们也许无法给他建造一个漂亮、宏伟的英灵殿,但最起码,翻修一下,让他笔下的那种“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次韵蒋颖叔》)、“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和秦太虚梅花》)的情景得到部分再现,也还是能够做到的吧。
可惜,可惜。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
苏轼后半生,虽有短暂重新入朝的机会,但因与旧党之间也存在分歧,故又一次被放外任,历定州、杭州、扬州。他每到一个地方,或登山临水,或访僧问道,都投入自己最真切的生命感受,对仕途的退意已经十分明显:
“孤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满江红·怀子由作》)“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
上图眉山,下图郏县。生与逝
这样的心声,今天定州、杭州、扬州的人都听到了。他们修建了东坡广场、东坡公园,定期举办“东坡行旅”文化节、东坡文化月或东坡雅集,梳理东坡在各自城市的行迹,设立《归来·苏东坡》剧场,真正在各自的城市里为苏东坡安了一个又一个家。
可是我们这里呢?苏氏父子三人最初赴京城应考,后苏东坡多年在开封任职,元丰年间任汝州团练副使,又曾游历汝州、陈州、叶县、辉县等地,现在如若去这些地方探访,我们会发现,今人恢复修建的纪念苏东坡的遗迹实在是少之又少。
汝州(现平顶山地区)还有一座荒凉落寞的三苏园,开封、陈州等其他城市,相关纪念性的地标几乎完全没有。好像,历史上的苏东坡从来没有到这些地方来过?
可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手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如梦令·寄黄州杨使君》),“清淮浊汴,更在江西岸。红旆到时黄叶乱,霜入梁王故苑”(《清平乐·送述古赴南都》),这些词章,写的又是哪些地方?
3
似乎经历了无数层峦叠嶂、惊涛骇浪,我终于一次又一次来到整个三苏园的后端部分——三苏坟前。
其实每次都有点不愿意来,怕遇到那种突然而至伤心、凄凉、落寞和悲愤。但是又不得不来,因为这是三苏长眠的地方,我得祭上一杯酒,燃上三柱香,鞠上几个躬,这样才算安心。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记梦》),这写的是苏轼对他亡妻王弗不舍的怀念和依恋吗?那座“孤坟”以及连接着的“凄凉”,放在他这里,放在三苏园,何尝也非如此?
风从西北来,这里的苍松、翠柏都倾斜向东南,显得密集而凌乱;坟茔只是几座土堆,坟前用青砖垒起一个池状平台,近前的青石祭龛,像是凑合着摆放在那儿的,简陋、粗糙,一推就倒;也许应该好好立上几块碑的,但是,现有的碑大概仍是老碑,风蚀严重,有些字迹已经漫漶不清。
我去过许多历史名人托身安魂的地方,总起来说,如果用心去修葺维护,舍得投入,那么这样的茔园就不会显得阴郁、压抑;反之,只把墓地当墓地,不打开一定程度的美学、诗学和环境学空间,那么,它一定会距人于“百步”之外。
去过西湖旁边的岳飞墓、林和靖墓、秋瑾墓和苏小小墓吗?那是融合了自然与人文元素的经典画作,每天游人如织。
去过荥阳的刘禹锡墓、李商隐墓,淇县荆轲冢,洛阳白(居易)园,焦作韩(愈)园吗?在这里,人融于山融于野,鸟语花香、草木葳蕤,而且视野开阔、景色层叠。
再去看伊川的范(仲淹)园、姚(崇)园,巩义的杜甫墓(偃师也有)、寇准墓、包拯墓、宋陵,许昌华佗墓、许由墓,等等,它们大多和三苏坟一样,立于荒野之中,任萧瑟秋风吹又吹。
我们都想来郏县寻找“小峨眉”,看它的山川秀美、人文繁盛,可是,这个“小峨眉”难道该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守着苏东坡,守着他的魂,竟然守着一个大寂寞、大朴素、大荒芜。
所以,河南应该倡导一种“名人祠园美学”,在园林设计和视觉艺术上做好文章,让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安放灵魂的地方,和他们的故里以及曾经求学、应试、游历、诗词打卡、建功立业的地方一样,对当今民众产生人人愿意来、人人喜欢来的吸引力和魅力。
河南这方面的“资源”和“项目”实在太多了,可惜我们往往谈“墓”色变,并敬而远之。
这实在是不应该。因为他们当初选择一个地方,一般是选中了那个地方别致的风景;而他们现有的存在,则反过来为这个地方的山川增了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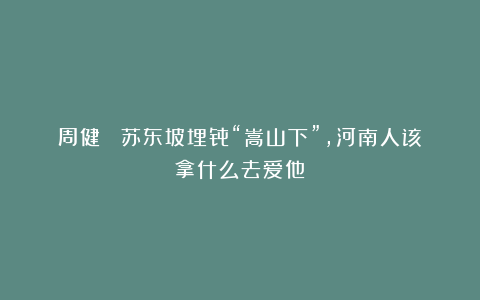
在这上面,苏东坡后期一路谪居的惠州、儋州,以及遇赦之后途经的廉州、英州、韶州、虔州等地,数百年来也都感恩苏东坡的“路过”,要不同样建有“东坡纪念馆”“东坡祠”“东坡路”,要不恢复东坡游迹、开展东坡古迹研学游,要不打造“东坡宴”并举办“东坡文化月”“寿苏会”这样的活动。
以上二图为惠州东坡纪念馆
以上二图为儋州东坡书院和东坡文旅大会剧目《男神东坡》
一个个都在争、都在抢、都在唤醒他,通过举办各种形式丰富多样、内容精彩纷呈的特色性文旅活动来纪念他,有不少活动已超越了简单的缅怀,而更深地融入到当地的文化肌理和日常生活中了。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归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这样一种深情,被南方的那些人永远记住了。
所以,当苏东坡从儋州出发,在路上悲喜交加地吟出《澄迈驿通潮阁》一诗后(“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他感谢到虔州送别他的好友江公著,“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前者的归乡情切跃然纸上,后者的不舍之意江河为证。
苏东坡曾论自身,“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若问起他的生死,我想他一定会提及这几个地方:眉州、湖州、常州、汝州(颍昌)。
眉州三苏祠
眉州乃其出生之地,有其祖茔地,有他父母和爱妻王弗的亡灵,有他爱吃的菔根和肘子。
他在诗文中写尽了对家乡的思念:“东风陌上惊微尘,游人初度翠城闉”《和子由踏青》,“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南轩梦语》),“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寄黎眉州》)。
家乡人呢,自然也以他为傲,现在的眉山,到处都充满了东坡元素:路、桥、河、湖、景,学校、广场、公园、楼堂、馆所,茶、酒、菜、饮、居,等等,皆以“东坡”二字命名。
其诗词融入到这里的山山水水,其故事为当地人如谈邻家父兄那样津津乐道,真也似爱他爱到了骨子里,惜他惜到了自家堂桌上。
在眉州,东坡文化元素渗透进城市的角角落落
常州则是苏东坡的终老和离世之地,他生前曾称常州为“出处穷达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吾州”。因此,如果说眉县强调“根脉”,杭州、密州强调政绩和诗文,惠州儋州强调贬谪和放达,常州的核心则是“归宿”。
现在的常州人,在城市里设有东坡小学、舣舟路,在其离世地修建了藤花旧馆,在附近建了舣舟亭公园,里面有东坡洗砚池、怀苏亭、仰苏阁等建筑,他们常常对外说的是,常州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
湖州的故事本来普通,从他到任到离开,其间仅仅有两个月零八天,但因为他在此处被御史台派朝臣乘驿马在此追摄并被拘捕,而后又被押解到京城,所以这个地方,在他一生中也很重要。
以上二图为常州东坡公园、舣舟亭
他在此写下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等少数几篇诗文,却贡献了“胸有成竹”这样的艺术理论;他在例行性的《湖州谢上表》中说了几句像“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这样的话,就被新党官僚断章取义,指斥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成了“乌台诗案”的主要导火索。
“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幽谷。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这首名为《游道场山何山》的诗,记载了苏轼游历湖州山水的惊鸿一瞥,多少年后,“我今废学不归山,山中对酒空三叹”这样的话成了当地久传成诵的景点。湖州人没忘记苏东坡和他在这里待得那两个月,他们将岘山山脚下当年东坡泊舟的地方命名为“苕溪苏湾”,在湖州飞英公园内修建了东坡纪念馆。
很有意思的是,苏东坡曾经待过的地方,只要有湖,湖上必有被命名的“苏堤”,湖州如此,杭州如此,颍州、徐州、惠州也如此。
最后,与苏东坡的死有关的地方,就是汝州郏城了。这是他的魂归之处,是他的长眠之地。但这里除了三苏坟,整个县城、平顶山市乃至当年的颍川或汝州所包含地区,还有他的其他什么印记?
以上二图为苏轼与秦观登临过的飞英塔和墨妙亭
4
即便现在,许多外地人说起苏东坡殁后葬在哪里,都还是一脸茫然。
他们知道苏东坡待过的眉州、黄州、杭州、儋州,却不知道他临死托身的汝州,以及具体埋棺的郏城上瑞里。
郏县现在在全国叫得响的有什么?一曰饸烙,二曰“广阔天地”,三曰铁锅,四曰张良墓,五曰文庙,六曰三苏坟。相较前三者,后三者作为文化景点,在全国的知名度还很低,去的人还很少。
这种情况,和苏辙长期隐居的颍昌(现许昌)情形类似。
长期以来,苏辙是一个被其兄苏轼的锋芒所遮盖的人物。他晚年参透朝堂纠葛后,隐居颍昌12年,期间出资修建汝州永兴寺吴道子壁画,补刻知名文人杨亿诗碑,扩建思贤亭,并写就众多锦绣文章,形成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
他又让自家子女在这片土地上置地繁衍,如今,其后裔已经广泛分布在河南的许昌、周口、平顶山、荥阳等地,人口近10万之众。
但现在的许昌,也即原来的颍昌,我们已经看不到苏辙任何的历史足迹。人文学者夏钦去年年底曾在《南方周末》撰文,称由他的老家眉山发起的传承“三苏”文化的18座联动城市中,没有许昌加盟;许昌政府部门或民间团体中,也没有专门研究苏辙的机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许昌主打的文化牌是“三国文化”。
现在河南留有苏辙印记的地方,也只有郏县上瑞里了。不过,与官方的失语不同,在河南民间,存在着一群自觉维护和传承苏轼、苏辙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的拥趸。如夏钦所说,“他们也许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也许就是普通的农民,却对薪火相传’三苏’文化,有着惊人的自觉”。
这样的人群,有很多。仅以苏氏兄弟的追随者为例,许昌市建安区苏桥镇上的苏辙后裔在镇上建有苏氏宗祠、苏家桥,以苏辙及其后人名字命名道路,家家户户的外墙上都书写三苏诗词,他们以家族接力的方式延续着对先祖的纪念。
苏东坡的民间守护者则更多。学术方面,王水照(复旦大学)、曾枣庄(四川大学)、莫砺锋(南京大学)、朱刚(复旦大学)、康震(北师大)等知名学者,不少人都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对苏东坡的研究、阐释和传播。
地方上,无论是苏轼后裔,还是地方上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民间苏东坡爱好者(“苏粉”),抑或是郏县苏坟村那些三苏坟守护人后代(已经守护922年),也都以自身的文化认同和自发宣传,形成一场场跨越近千年的、对“三苏”之魂的虔诚守望。
这里面,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刘楠推出了苏东坡“云守护”项目,以数字藏品等新媒介为桥梁,吸引更多的苏东坡爱好者成为苏坟寺村“云村民”,打破了时空界限,呈现出良好社会效果。
眉山三苏祠
而更多的普通人,则以自身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对三苏父子的敬仰和纪念。
我每次去三苏园,发现来的最多的游客是学生群体,特别到了每年的中考季、高考季,来拜苏东坡祈求金蟾折桂、榜上有名的更是成群结队。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现在三苏园中的苏轼像,已形成了独特的“拜干爹”文化。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乡亲带着自家的孩子在石像上挂了一块红布,然后跪在那儿磕头,红布上用黑笔写了一段话:“XXX,男,7岁,河南省汝州市纸坊镇东赵庄村,任苏东坡为干爹。”一看就是孩子的书写体。
这要比拜祖来得亲切,来得贴近人间。
但也有一些人并不是来拜来访的,而是别有所图。
不久前,媒体曝光一个自称苏辙后人的“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苏文,号称将投资33亿元投建三苏园项目(包括15亿元的“三苏纪念堂”等),几年过去,事实证明这个承诺属于子虚乌有,苏文本人甚至还打着当地“东坡书院院长”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事情败露后,郏县有关部门将该项目列入“重大未履行协议”清单,启动退出程序,纳入“招商引资风险防控教材”。
三苏园需要投资吗?相比于其他东坡路过之地动辄投巨资修建的公园、纪念馆、祠堂、道路、水系等设施,这个地方更需要!
需要加强维修吗?连三苏园现有的管理者都说,目前园区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从周边风貌的整体打造,到三苏园内的游览动线设计;从脚下该用条石还是青砖,到墙壁上碑记位置是否妥当,都需要来一次大手术。
可是,尽管当地在2023年曾发债8600万元用于“三苏园景区建筑物工程、基础设施综合提升工程、配套设施建设工程”,但几年过去,并不见有什么动静。
三苏园现状
我想,这里应该成为一座大型的花团锦簇的纪念园的(如同荥阳刘禹锡公园、李商隐公园那样的模板),但是,这里现在还不是!
我想,这里应该有一场以“夜雨对床”“乌台惊梦”等为主题的大型露天演出或歌舞剧的(类似成都话剧《苏东坡》、眉州音乐剧《宋遇东坡》、黄州音乐剧《大江东去》),但是,这里没有!
我想,这里的许多街道、楼堂、饭店应该多以东坡名字或诗词命名的(如同眉州、密州、黄州、儋州、常州所做的那样),但是,除了苏坟村周围,其他地方皆没有!
我想,这里应该设有一座书院,让苏氏父子三人能继续在这里读书、制策,勉励天下人“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但是,这里也没有!
没有,没有的太多了,只有那单调的、符号性的景观摆设。可惜。
我想或许正因如此,三苏园只能继续它既有的简陋、朴拙、粗糙、荒凉,让人难以与这“小峨眉”应有的钟灵毓秀对上号,难以与这“皇天厚土”“还千古英灵之气”的人文昌盛挂上钩。
历史上,此类人文建筑多是建了毁,毁了建,经历风雨淘洗属于常事。不过,其复建或维修一直由官方主导,官方有意无意都展现出一种饱含儒家意识的“文化责任”。
三苏园自建成后第一次大修发生在元至正十二年,也即1352年,郏县县尹杨允将苏洵衣冠冢置于二苏墓旁,建三苏祠,塑三苏像;不久之后,当地扩建广庆寺,置僧侣守护,并置于祀田六顷余,保障祭祀开支;明清之间,三苏园又多次扩建,乾隆四十五年立苏轼后裔苏建芳为奉祀生,专司祭司。
1963年列为河南省重点保护文物,1997年开始景区化建设,修建东坡湖、跨路牌坊等;2004年,民营企业禹州中天介入,计划投资3000万元开发,但实际投资400多万元用于绿化和设施维护后,即告中止,三苏园当时的景区面貌维持至今。
而正是这20年来,“东坡热”在全国兴起,各地规模不等、形态不一的纪念馆、公园、路桥等建筑拔地而起,各类讲座、节目、书籍、纪念活动层出不穷,苏东坡,从沉重的历史走向了这绚丽妖娆的人间。
人人都爱苏东坡。
5
去年去眉山市,闲逛了几日。东坡肘子、东坡肥肠鱼、东坡扣肉、东坡春鸠脍、东坡鳊鱼被遍尝一边;三苏祠、无忧城、东坡水街、柳江古镇、泡菜城,一路走来,处处都是浓郁的“搞扭儿”(干什么?)、“憨吃哈胀”(胡吃海喝)风情。
有许多年轻人会穿上宋朝服装,扮作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他们,在人群中穿梭。很奇怪,你在这里看到这种装扮,竟没有任何违和感。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这里的任何一道街景、任何一个场景,大都与苏东坡关联。
我想这位川人的一生中,有两段在家乡度过,一是小时候在眉山读书,父母亡后在家守孝,他一定和弟弟苏辙一起,将这里的万水千山走遍,将这里的美珍佳肴尝遍。
家乡人记得这一切,于是就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为他摆上了时光复读机。
“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做凌云游”“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这样的苏东坡,永远属于眉山。
但苏东坡同样说过,“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是京师、凤翔、密州、黄州、湖州,还是定州、扬州、惠州、儋州、常州,他磕磕碰碰一路走来,皆“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们今天有幸有他为伴。
那一天去开封尉氏凭吊阮籍啸呼台,突然想起苏轼在嘉佑五年(1060)年路过此处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大雪独留尉氏,有客入驿,呼与饮,至醉,诘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谁”(夜晚宿在尉氏驿馆,大雪,偶遇一南下客人,就招呼人家一起畅怀痛饮,等到第二天早上客人离去,竟不知道人家姓名。)
《大雪留尉氏》
古驿无人雪满庭,有客冒雪来自北。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我酌徐徐不满觥,看客倒尽不留湿。千门昼闭行路绝,相与笑语不知夕。醉中不复问姓名,上马忽去横短策。
“见之何必问相识”“醉中不复问姓名”,这是千古遗憾吗?我想对苏东坡,不是,他一生经历的太多,在尉氏写下这一幕,只是记趣而已,他有的是豁达和快乐。但对于那位“北方客人”而言,假如他多问几句,知道对面坐的是苏东坡,一定会大声笑着道一句:
“苏东坡,你就是苏东坡啊!老弟,你好!”
现在的我们,都是那位“北方客人”。我们和苏东坡对饮,如人生逆旅中的过客,醉也罢,醒也罢,“相与笑语不知夕”是一定能够求来的。
只是,千年阔别之后,哪一天对酒当歌时突然想起他,一定要到现在的郏县小峨眉,去他的坟前敬上一壶老酒。
他记得“你”,“你”也要记得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