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导读: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 MG)是一种由神经肌肉接头传递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近年来,中西医结合治疗MG在提高疗效、减少副作用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本文系统综述了MG的西医靶向治疗新进展(如补体抑制剂、FcRn拮抗剂)、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深化(证候分型标准化、核心方药研究)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协同机制(免疫调节、增效减毒、整体调节)。通过分析临床实践优化策略(个体化精准方案、序贯与联合治疗、重视生活质量和长期管理)论证中西医结合模式的应用价值。尽管仍面临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不足等挑战,中西医结合治疗MG代表了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
童广安 副主任医师
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MG的全球患病率约为15-25/10万人,发病率约为1-2/10万人/年,可见于任何年龄,女性在40岁前发病率略高于男性,而60岁后男性发病率则可能更高。根据发病年龄、抗体类型、是否合并胸腺瘤等因素,MG可分为早发型、晚发型、MuSK-MG、LRP4-MG、胸腺瘤相关MG等亚型,这种分型对治疗选择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西医治疗MG主要依靠胆碱酯酶抑制剂(如溴吡斯的明)对症治疗,以及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如硫唑嘌呤、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和血浆置换(PLEX)等免疫调节治疗,以及针对胸腺异常(增生或胸腺瘤)的胸腺切除术。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预后,但长期使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带来的显著副作用(如感染、代谢紊乱、骨髓抑制、肝肾功能损害、恶性肿瘤风险增加等)、部分患者疗效不佳或反复复发、以及高昂的治疗费用等问题,仍是临床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医药凭借其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多靶点调节和“治未病”的优势,以及在改善症状、减少西药用量和副作用、调节免疫稳态等方面的潜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中西医结合治疗MG,旨在融合两种医学体系的精髓,取长补短,探索更安全、有效、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已成为当前MG研究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近年来MG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并探讨优化临床实践的策略。
重症肌无力西医治疗
近年来,随着对MG免疫病理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对补体激活、抗体介导的致病途径的阐明,以及生物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针对MG发病关键环节的靶向生物制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传统治疗效果不佳或不能耐受副作用的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1. 补体系统抑制剂
依库珠单抗 (Eculizumab):作为首个获批用于治疗抗AChR抗体阳性、难治性全身型MG成人患者的补体C5抑制剂,其作用机制是阻止C5裂解为C5a和C5b,从而阻断补体级联反应终末膜攻击复合物(MAC)的形成,保护NMJ免受补体介导的破坏。多项关键临床试验(REGAIN及开放标签扩展研究)证实,依库珠单抗能显著改善患者肌无力症状、生活质量评分,减少急性加重和急救治疗需求,疗效持久。主要风险是脑膜炎奈瑟菌感染,需在用药前接种疫苗并密切监测。
Ravulizumab:作为新一代长效C5抑制剂,通过工程化改造延长了半衰期(约8周),实现每8周静脉给药一次(而依库珠单抗需每2周一次),大大提高了用药便利性。其疗效和安全性在CHAMPION MG III期临床试验中得到验证,为非劣效于依库珠单抗,已被批准用于治疗抗AChR抗体阳性的全身型MG成人患者。
Zilucoplan:这是一种皮下注射的肽类C5抑制剂,患者可自行给药,使用更为便捷。RAISE研究显示其在抗AChR抗体阳性的全身型MG患者中能快速起效并显著改善临床症状。
其他靶点:针对补体上游成分(如C1s抑制剂Sutimlimab)的研究也在进行中,有望提供更多选择。
2. 新生儿Fc受体 (FcRn) 拮抗剂
Efgartigimod:FcRn拮抗剂的作用原理是通过阻断FcRn与IgG抗体的结合,增加IgG(包括致病性自身抗体)的分解代谢,从而降低循环抗体水平。Efgartigimod alfa(静脉注射)及其皮下注射制剂Efgartigimod alfa and hyaluronidase-qvfc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获批用于治疗抗AChR抗体阳性的全身型MG成人患者。ADAPT研究及其开放标签扩展研究ADAPT+显示其起效快(首次给药后1周内可见改善),能显著改善肌力评分和生活质量,且总体耐受性良好。其“按需治疗”的模式(根据病情复发情况周期性给药)是另一优势。
Rozanolixizumab:另一款皮下注射的FcRn拮抗剂。MycarinG研究证实其在全身型MG(无论抗体状态)成人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Batoclimab:在中国开展的III期研究也显示了其在治疗中国全身型MG患者中的显著疗效和良好安全性。
3. B细胞靶向治疗
利妥昔单抗 (Rituximab):尽管主要用于抗MuSK抗体阳性的MG患者(这类患者对传统免疫抑制剂反应可能较差),但在抗AChR抗体阳性、难治性MG患者中的应用经验也在积累。通过清除CD20+ B细胞,减少抗体产生。越来越多的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支持其在特定MG人群中的有效性和相对安全性(需注意感染风险)。
新一代B细胞/浆细胞靶向药物:如靶向BAFF/BLyS(如Belimumab,主要用于SLE,在MG中研究有限)、靶向浆细胞(如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抗CD38单抗达雷妥尤单抗)等在难治性MG病例中有探索性应用报道,但尚需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
4. 其他靶点与策略
靶向Fcγ受体:如Nipocalimab(抗FcRn单抗,同时具有Fcγ受体阻断效应),研究显示其在全身型MG(包括MuSK-MG)患者中的潜力。
IL-6受体抑制剂:如托珠单抗(Tocilizumab),通过阻断IL-6信号通路抑制炎症和B细胞活化。小型研究和病例报告显示其对部分难治性MG患者有效,尤其是一些对传统治疗和上述新药反应不佳的患者。
CAR-T细胞疗法:虽然在MG领域尚处于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主要在动物模型),但其在B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病(如SLE)中展现的深度缓解潜力,为未来根治某些类型的MG提供了理论可能性,但安全性和长期影响是巨大挑战。
个体化治疗与生物标志物:随着生物制剂选择的增多,如何根据患者抗体类型、疾病严重程度、共病情况、药物可及性、成本效益等因素进行个体化选择变得至关重要。探索预测治疗反应的生物标志物(如特定免疫细胞亚群、细胞因子谱、基因表达特征)是当前研究热点。
靶向生物制剂的涌现极大地丰富了MG的武器库,特别是为传统免疫抑制治疗效果不佳或无法耐受的难治性患者带来了希望。这些药物作用机制明确,起效相对较快(尤其是FcRn拮抗剂),部分可实现“按需治疗”。然而,其高昂的成本、潜在的感染风险(尤其是补体抑制剂)、长期安全性和疗效的维持、对不同MG亚型的疗效差异(如MuSK-MG、LRP4-MG、血清阴性MG的最佳选择仍在探索中)以及停药后的复发问题,仍是临床应用面临的挑战。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优化治疗策略(如联合用药、序贯治疗)、拓展适应症(如眼肌型MG、儿童MG)、寻找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以及开发更安全、有效、经济、便捷的新疗法。
重症肌无力中医治疗
中医药治疗MG源远流长,近年来在现代科学研究的推动下,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临床与基础研究日益深入,尤其在证候标准化、核心方药作用机制探索及特色疗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1. 中医病因病机认识的深化
中医将MG主要归属于“痿证”范畴,尤其与“睑废”、“视歧”、“头倾”、“大气下陷”等症状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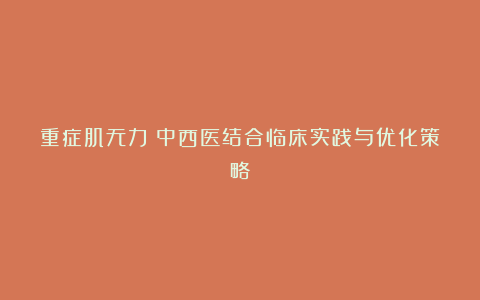
核心病机:主流观点认为“脾胃虚损”是MG发病的核心和始动因素。“脾主肌肉”、“脾主运化”、“脾主升清”,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乏源,肌肉失于濡养,则痿软无力;清气不升,则见胞睑下垂、抬头无力、声音嘶哑、吞咽困难等;浊阴不降或阻滞经络亦可加重病情。
2. 辨证分型标准化研究
为促进中医诊疗的规范化和可重复性,学术界致力于建立MG的证候分型标准。参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及近年发布的《重症肌无力中医诊疗指南》等权威文件,结合临床实践和研究成果,MG的常见基本证型可归纳为:
脾胃气虚证:主症眼睑下垂或复视,四肢乏力,劳累后加重,休息减轻。次症:食欲不振,大便溏薄,面色萎黄,少气懒言。舌脉:舌淡苔薄白,脉细弱。
脾肾阳虚证:主症全身乏力明显,畏寒肢冷,腰膝酸软,抬头困难,吞咽费力,构音不清。次症:小便清长,夜尿多,或阳痿早泄(男),月经不调(女)。舌脉:舌淡胖或有齿痕,苔白滑,脉沉迟无力。
肝肾阴虚证:主症眼睑下垂,视物模糊或复视,口干咽燥,头晕耳鸣,四肢痿软无力,肌肉瘦削。次症:五心烦热,失眠多梦,盗汗。舌脉:舌红少苔或无苔,脉细数。
气血两虚证:主症神疲乏力,面色苍白或萎黄,心悸气短,眼睑下垂,肢体软弱无力。次症:头晕目眩,自汗,易感冒。舌脉:舌淡苔薄白,脉细弱无力。
兼夹证(标实证):兼湿热浸淫证:肢体痿软,困重无力,或有发热,胸脘痞闷,小便黄赤。舌红苔黄腻,脉濡数。兼瘀阻脉络证:肢体痿软无力,麻木不仁,或有固定疼痛,面色晦暗,口唇青紫。舌质紫暗或有瘀斑瘀点,脉涩。兼痰浊阻滞证:吞咽困难,构音不清,咯吐痰涎,胸闷脘痞。舌苔白腻或厚腻,脉滑。
需要强调的是临床实践中患者常表现为复合证型(如脾肾阳虚兼痰瘀阻络),且证型随病情演变和治疗干预而动态变化。标准化分型为研究和交流提供框架,但临证仍需个体化辨识。
3. 核心方药及复方研究
经典方剂的应用与优化:基于“补脾益气,升阳举陷”的核心治法,补中益气汤(黄芪、党参/人参、白术、当归、陈皮、升麻、柴胡、炙甘草)是治疗MG(尤其脾胃气虚证)的首选和基础方。大量临床观察和部分随机对照试验(RCT)证实其单用或联合西药能有效改善MG临床症状、减少西药用量、降低复发率、提高生活质量。针对不同证型,常进行化裁:脾肾阳虚证合右归丸或肾气丸(加附子、肉桂、熟地、山茱萸等)。肝肾阴虚证合左归丸或杞菊地黄丸(加熟地、山茱萸、枸杞、菊花等)。气血两虚证合八珍汤(加熟地、白芍、川芎等)。兼湿热加苍术、黄柏、薏苡仁等(如合四妙散)。兼瘀血加丹参、红花、地龙等。兼痰浊:加半夏、胆南星、石菖蒲等。
大气下陷危象时急用大剂量补气升陷药,常重用生黄芪(60-120g或更多),合升陷汤(黄芪、知母、柴胡、桔梗、升麻)加减,必要时配合西医抢救。这些复方多在补气升阳基础上,结合补肾、活血、通络、祛湿等法,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
4. 针灸及其他外治法
针灸:作为重要的非药物疗法,在MG治疗中起辅助作用。选穴常以健脾益气、补益肝肾、疏通经络为原则。常用穴位:百会、印堂、攒竹、阳白、太阳(针对眼睑下垂)、足三里、三阴交、脾俞、肾俞、关元、气海(整体调节)、合谷、曲池(通络)。研究表明针灸可能通过调节神经递质、改善局部循环、调节免疫等途径改善症状(特别是眼肌症状)和全身状态。
艾灸:尤其适用于虚寒证患者(如脾肾阳虚证)。常用穴位:神阙、关元、气海、足三里、脾俞、肾俞。具有温阳散寒、补气培元之效。
穴位敷贴/注射:选用具有补益或活血作用的中药制剂(如黄芪注射液、当归注射液)或复方膏剂,敷贴或注射于特定穴位(如足三里、脾俞、肾俞),通过经络腧穴和药物双重作用调节机体功能。
中医治疗MG在理论体系、证候规范、方药作用机制及特色疗法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核心在于以“补脾益气、升阳举陷”为主轴,结合滋补肝肾、活血通络、祛湿化痰等法,进行个体化辨证施治。现代研究揭示了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靶点、多层次(免疫、神经、肌肉、代谢)调节的优势。针灸等外治法是重要的补充手段。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深化对中医证候生物学基础的认识,开展更多高质量、大样本、长周期的RCT研究,优化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并加强中药新药研发和标准化工作。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协同机制与优势
中西医结合治疗MG并非简单的中药与西药叠加,而是基于两种医学体系的理论特点和MG的复杂病机,通过多途径、多靶点的协同作用,旨在实现增效、减毒、调节免疫稳态和整体功能改善的目标。其核心协同机制与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免疫调节的协同与互补
西药优势:作用靶点相对明确,起效较快(尤其生物制剂、激素冲击、IVIG/PLEX),能迅速抑制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降低自身抗体滴度,控制急性炎症和危象。
中药优势:中药复方具有多靶点、整体调节的特点。其协同机制在于:
增强免疫抑制深度与稳定性:中药(如补气、补肾、活血类)可能通过调节Treg/Th17平衡、抑制过度活化的B细胞、调节树突细胞功能、改善免疫微环境等途径,增强西药免疫抑制剂的疗效,并可能有助于维持更稳定的免疫抑制状态,减少复发。
促进免疫耐受/稳态重建:中医“扶正固本”的理念,强调在抑制异常免疫的同时,扶持正气,调节免疫系统的内在平衡。中药可能通过诱导免疫耐受、促进免疫自稳机制恢复,从长远角度减少对强力免疫抑制的依赖。
减轻西药免疫抑制的副作用: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可导致免疫功能低下,增加感染风险。一些具有免疫调节(非单纯抑制)作用的中药(如黄芪、人参),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或增强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降低感染发生率。
2.增效减毒,减少西药依赖与副作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能获得比单用西药或单用中药更好的临床疗效(如定量MG评分QMG、MG日常生活能力评分MG-ADL改善更显著)、更高的临床缓解率和改善率、以及更长的缓解期。减少西药用量(减量)是中西医结合最显著的优势之一。对于长期依赖激素的患者,在辨证使用中药(尤其补益脾肾、温阳类药物)的基础上,可更平稳、更快地减少激素用量,甚至部分患者最终能停用激素,显著减轻库欣综合征、骨质疏松、血糖升高等激素相关副作用。中药可能允许降低硫唑嘌呤、他克莫司等免疫抑制剂的维持剂量,减轻骨髓抑制、肝肾毒性等风险。滋阴降火(如知母、生地、麦冬)可改善阴虚火旺症状(潮热、失眠、口干);健脾和胃(如陈皮、半夏、茯苓)可减轻胃肠道反应;补肾壮骨(如骨碎补、杜仲、续断)有助于防治骨质疏松。健脾益气养血(如黄芪、当归、阿胶)可改善骨髓抑制导致的贫血、白细胞减少;疏肝健脾利湿(如柴胡、茵陈、茯苓)可保护肝功能;健脾补肾(如黄芪、白术、山茱萸)可保护肾功能。其常见的胃肠道痉挛、分泌物增多等胆碱能副作用,可通过健脾理气、和胃降逆(如陈皮、半夏、竹茹)的中药缓解。
3. 整体调节与症状改善,提升生活质量
西药主要关注免疫病理环节和核心症状(肌无力),对患者伴随的全身症状(如乏力、倦怠、畏寒、失眠、食欲不振、情绪焦虑抑郁等)关注和处理相对不足。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精髓在此体现。通过调和脏腑、平衡阴阳、疏通气血,能显著提升肌力、改善眼睑下垂、复视、吞咽、构音、呼吸困难和肢体无力。有效缓解疲劳感、畏寒肢冷、食欲不佳、腹胀便溏、口干咽燥、失眠多梦、腰膝酸软等,使患者整体状态明显好转。疾病带来的焦虑、抑郁情绪常可通过疏肝解郁、养心安神的中药(如柴胡、郁金、酸枣仁、合欢皮)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改善身体机能、精神状态和社会参与度,使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如MG-QOL15)显著优于单用西药治疗组。
4. 防治危象与稳定病情
在肌无力危象等紧急情况下,西医的呼吸支持、IVIG/PLEX、激素冲击是抢救生命的关键。此时,中医大剂量补气升陷(如重用生黄芪、人参、升麻、柴胡)以振奋宗气,辅助改善呼吸功能。醒神开窍(如石菖蒲、郁金)或清热化痰开闭(如安宫牛黄丸)用于合并感染、痰热蒙蔽清窍者(需在严密监护和西医抢救基础上使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核心优势更在于稳定期和缓解期的长期管理:通过持续的中药调理(扶正固本为主,兼祛余邪)、生活调摄指导(避风寒、调饮食、畅情志、适劳逸),增强患者体质和抗病能力。有效控制感染(中医认为外感是重要诱因)、调节情绪、避免过劳等措施,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更易被患者理解和执行。中西医协同调节免疫稳态和整体功能,能显著降低MG的复发频率和严重程度,实现更长期的临床稳定。
中西医结合治疗MG的协同优势在于:免疫抑制与免疫调节/稳态重建互补;快速控制病情与长期稳定防复相济;强力干预与减毒增效兼顾;核心症状改善与全身状态调治并重。这种整合模式通过多靶点、多层次、整体性的干预,最终达到提高疗效、减少西药用量和副作用、降低复发率、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的综合目标,为MG患者提供了更优化、更个体化、更具可持续性的治疗方案。
结论与展望
中西医结合治疗MG代表了整合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坚持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循证医学为标准,以患者获益为核心,不断加强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完善诊疗规范,培养复合人才,中西医结合必将在攻克重症肌无力这一顽疾的征途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全球MG患者提供更优化、更富有人文关怀的“中国方案”。未来的MG治疗模式,将朝着更加精准化、个体化、整合化(融合中西医及其他有效手段)和预防化的方向发展。目前西医靶向治疗迎来革命性突破,以补体抑制剂(依库珠单抗、Ravulizumab、Zilucoplan)和新生儿Fc受体拮抗剂(Efgartigimod, Rozanolixizumab, Batoclimab)为代表的生物制剂,为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难治性MG患者提供了高效、快速且相对安全的新选择。B细胞靶向治疗(如利妥昔单抗)在特定亚型(如MuSK-MG)中价值凸显。
成功实施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关键在于基于精准的西医评估和中医辨证制定个体化方案;根据疾病不同阶段(急性期/加重期、平台期/减药期、稳定期/缓解期)采取序贯与联合策略(西医主导、中西医并重);高度重视生活调摄(避风寒防感染、合理运动、饮食调养、情志舒畅)并建立长期规范的管理随访制度;特别关注儿童、老年、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的需求。中医药当前面临高质量循证证据不足、诊疗规范标准化待完善、作用机制需深入阐明、复合型人才缺乏等挑战。未来应着力于加强高质量临床研究(RCT、真实世界研究);深化“病证结合”精准化研究;利用现代科技(系统生物学、人工智能等)创新机制研究方法;推动中药新药研发与现代化;促进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与人才培养;优化相关政策支持。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肌无力通过融合现代医学精准靶向干预的强大力量与传统中医药整体调节、扶正祛邪的独特智慧,形成了一种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整合医学模式。它不仅能更有效地控制疾病症状、减少西药不良反应、降低复发率,更能显著改善患者的整体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尽管前路仍有挑战需要克服,但中西医结合代表了MG未来治疗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方向。随着研究的深入、规范的完善和临床实践的推广,这一模式必将为全球更多的MG患者带来更优的治疗选择和康复希望,彰显整合医学在应对复杂疾病中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