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留下来的人——那些没能走上长征的人
十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留在了已经渐渐冷下来的苏区。他们不是不想跟着大部队往前走,是主动说“我来守着”。他们留下的时候,可能也没想过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撑到胜利那天。你说人生哪有多少岁月,能像那年秋天一样刀尖上跳舞?
这话搁到今天,就是谁令你走,谁令你留,明知道眼前是灰头土脸,没人盼着被埋进土里。但人总要有人留下。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成为通向传奇的浩荡人群。有一小撮人在灯光暗下来的地方,咬着牙把门关上,说:“守住不让敌人把门踹烂。”你扒开几十年历史尘土,能看到这十个人的身影渐次模糊。有些名字今天还算响亮,有些现在提起来,不少人只记得个头衔或壮烈的死法。
1934年秋,天阴沉沉的。长征临出发。那会儿谁都不笨,红军打了几年,弹药粮食不多,指头一数,士兵一个个有伤、饿着肚子,上头人决定:一部分人走;一部分人,得原地死磕着抵挡“围剿”。谁走,谁留,会议上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戏码。只是个别同志最后抿嘴点了头,自己先自觉地“自愿”留守。
想象一下,瑞金的夜晚,十几号人在油灯下,烟雾腾腾,项英新官上任,推了推眼镜,说:“大伙都知道干这事的人结局可能不怎么好,但我先表个态。”有人饭也没吃饱,掏出根干巴玉米充饥,有人还想见小孩最后一眼,来不及——队伍第二天就得走。留守的人,只能眼看着红军主力“满目疮痍的队伍”远远溜进夜色。
博古、李德、周恩来,先是合伙扛成了三人团,高处决策,底下人则是收拾起大大小小的烂摊子:赶制枪榴弹,挨家挨户征粮,生病伤员他们也没办法全带走。留守苏区的这些人,必须在最危险、最暗淡的时候,撑住最后一口气。令人唏嘘的是,这最后一口气,撑了多久?
天大地大,敌人杀过来的马蹄子更大。项英、陈毅、瞿秋白、贺昌、陈潭秋……这些名字,好像一股脑儿钻进了烈火里。陈毅那阵子说话带着湖南腔,半开玩笑半真心:“死守,不打招呼就别撤。”而实际上的气氛却是:“活着能再见天日吗?”
十个人,一张纸列名单。顺手还能补上几位,比如毛主席的亲弟弟毛泽覃、方志敏,还有岁数不小的何叔衡、铁嘴的刘伯坚,以及古柏。大多数都是血肉之躯,也有骨头发软焦心的时候。可是一旦选定留下,该谁带兵谁带兵,该写口号谁写口号。苏区的红色政权就像被烟灰压住的火星,咬牙熬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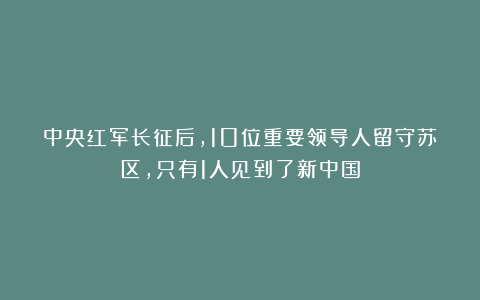
十几天后,主力已经走远。敌人的“围剿”部队像被甩了个大跟头,费了半天劲才发现自己对着的是“留守主力”,被晃了道。蒋介石反应过来,差点气得直跳脚,一封又一封电报飞来,命令声称要“杀他个鸡犬不留”。可那帮红军还真不是干皮匠,刀子藏在袖子里,暗地里调兵遣将,小部队作战灵活。整体上,局势依然是“苟且偷生”,但有时候“偷生”就是为了留住一点点火种。
你说这些人怕死吗?怕。不过跟后人想的不太一样。他们是那种,没人想摆好姿势去英勇就义;但如果只有自己去背黑锅、唱主角,也认了,扛着就是。譬如瞿秋白,肺结核咳着血,气喘吁吁。他主动要求:“我不拖累大队人马。”何叔衡年纪大,路上走不动,活生生被追兵“逼到崖角”,他索性一跺脚跳下去,死得决绝。你说革命不讲浪漫,连死都死得硬扎。
他们最怕的是消息断了。山里夜里风吹得嗡嗡响,有时困了,最大希望是明天还能看见活人,不是等到自己一枪爆头。一次又一次的突围失败、哨兵被俘,他们已经渐渐麻木。方志敏带抗日先遣队北上,一路死战,最后却栽在叛徒手里。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多写一篇家书”。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字,后来被翻出来,字迹潦草,只有坚持。
毛泽覃带着残兵打游击,无数次在密林里转悠,他掩护小部队突围,没了子弹,最后自己倒在山坡那头。跟哥哥一起革命的人,最后也没在新中国的阳光底下喝上一碗滚热的茶。
说到底,剩下的人寥寥无几。战争年代,活着本身就带点运气。后来能挨到解放的十个人里,只陈毅一个。剩下那几位,项英战死,陈潭秋在新疆被盛世才害死,全变成了人们嘴里的“烈士”。被困在山洞二十多天、啃树皮、吃冷水的陈毅,还能笑着写诗,梅岭三章,不是为了标榜,而是“困死不如撑着,撑一天是一天”。后来新四军组建,项英陈毅又搭档,跟日军、再跟“自己人”玩命。皖南事变那回,新四军被打残,项英阵亡,消息传来,老战士们有人背对着哭。
说起来,那个时候的“留守”有时候比长征路上的逆境还难。你可能听多了红军二万五,雪山草地、爬冰卧雪,其实南方山里的烟火、泥泞、密林、暗杀、背叛,那种压在肉皮子下的阴冷,也是折磨人心的。一队人里,转眼“分头突围”就成了永别。
几十年过去,人们喜欢讲“幸存者”,但那一代人说过:“我不是命大,只是没轮到。”陈毅真的见证了新中国。很多老百姓也许叫不全他的职务,更不记得他年轻时那张黑瘦的脸。
你要问,这十个人最终怎么了?七个埋骨南方密林,三人熬不过太平日。后来的事,谁都猜不到。但埋名的埋名,传世的传世,都没有白走原地的路。今天的我们,路过当年苏区、江西小村子的老井,偶尔能看到边上的一块石碑。没人知道那些夜里没睡的、咬着牙拖着伤病的留守者,此刻会说什么。
他们的故事也许就是这样,平淡得像那年苏区夜里微微亮的油灯——不怎么风光,却照见漫长黑夜里,人心的一点点不屈。人活一世,难敢问“留下”还是“长征”;但总归得有人站在门口,说一句:“你去东,我守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