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县有个黄金镇,山上有个碉楼阵,黄金河旁黄金场,碉楼三星平安长。”伴随着这首童谣,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以黄金为名之地。不为淘金而来,只为这座以黄金为名的小镇背后隐藏的那些扑朔迷离的故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重庆市忠县传唱起这样一句童谣:“黄金坝,黄金河,忠州北部藏金盒。”于是,黄金场有黄金的传说就这样流传开了。
当然,这个传说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清嘉庆年间,一场历时九载,波及川、鄂、陕、豫、甘等多省的战争爆发,史称“白莲教起义”,这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战争爆发后,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罗其清、冉文俦等十余支义军组成了号称白莲教三大主力之一的四川白巾军,并占据山区险要筑垒防守,不但力挫四川总督英善和成都将军勒礼善的部队,还与另一支王牌部队襄阳白巾军互为策应,一时间令白莲教义军声势大振。
很快,清军开始调整战略,针对山区人口稀少的特点,采取“筑寨团练”“坚壁清野”等措施,切断义军各部的粮源、兵源以削弱对方流动作战能力,然后将其分割包围。两路白巾军只好向川东山区撤退,姚之富、王聪儿、罗其清、冉文俦先后被杀,王三槐被诱俘,仅冷天禄等残部辗转至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及川东地区。据说,当时白莲教各领袖清楚大势已去,为保留东山再起的火种,决定派遣冷天禄等部护送起义之初缴获的黄金,并力保其先行入川将黄金秘密安置妥当,其余部队则边抵抗边撤退,最后分散隐藏到川东各山岭中,待时机成熟时挖出秘密藏金作为军资再次反清。
然而,由于冷天禄到达忠县之后又北上折返抗敌,最终中箭身亡,这个关于黄金的传说也就成为了永远的秘密。直到清末,一次大暴雨引发的山洪袭击了黄金场。夜晚,乡民回到场镇的时候,借着皎洁月光隐约发现河水中泛出点点金光,寻着过去,竟然发现了一些细碎金银。消息随即不胫而走,此后所有村民都投入了“淘金”浪潮,有人在河滩和洪水褪去的田地里又发现了一些金银。消息很快传到官府,联想到当地一直流传着白莲教藏金的传说,黄金场的名字也是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才得名,于是,官府迅速开始对河流沿途的山岭开展地毯式搜索,但却一无所获,童谣里神秘的藏金依然下落不明。
黄金场的得名究竟是否真与藏金有关早已无从考证。地方志记载,黄金镇源于金子坝一带盛产的黄荆树,因其谐音“黄金”而得名,但当地老人们都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反而坚信世代相传的藏金传说。深究下来,地方志中提出的“黄荆树”说法很难站得住脚,首先,既然金子坝盛产黄荆树,那又怎么解释金子坝的得名呢?其次,流经黄金场的黄金河原名双新河,其改名时间也与藏金传说吻合。
因此,“黄荆树”的说法有着许多漏洞,姑且只能当做一桩传闻,不过,这也使得黄金镇藏金之谜更加扑朔迷离。
低调的渝东北“土豪”
其实,黄金镇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富庶之地,这与有没有藏金毫无关系。
黄金镇始建于清朝,距今240年有余,位于忠县北部通往梁平、垫江和川北地区的交通要道上,建镇之初便是重要驿站和商贸重镇。因其地处石柱山区与梁平坝子间的过渡地带,地形以丘陵为主,加之水域广阔,天然便极适宜耕种,由此便诞生了许多耕读传家的名门望族,集市场镇也借助商贸迅速兴起。如今,黄金镇境内的几个沿河、沿商道的老街都保留了当年的规模,依然能感受到曾经的繁华与喧嚣。而如此众多的老街密集扎堆于这片区域,也足见其曾经的富庶。
场镇沿黄金河而建,临河一侧是吊脚楼老街,老街长600米,以3米宽的青石铺就,两边民居林立。曾经,老街上的居民基本家家为商,细观门庭,均为楼下摊铺、楼上住宿的格局,此外,以前的政府、卫生院、畜牧保健站、供销社等办公场所也一应俱全,至今还依稀能够辨识。眼下镇上只剩下一些留守的老人,他们讲起以前依然充满自豪:“曾经的黄金人啊,都是见过世面的,那琳琅满目的货品,很多县城人都没有见过。”当曾经的繁华化作云烟,只有那些独具特色的木板门、各式各样的牌匾、匠心打造的小拱桥……仿佛还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大岭老街则是当地望族冉氏的聚居之地,整个老街建在海拔900米高的牛头脑山山顶,至今还保留着100多米长、约10米宽的青石板路。整条青石板路均由长2米、宽50厘米的8行条石铺设,颇具气势,历经150多年依然完好无损,是目前忠县保存最完好的青石板古街。
因此,当藏金的传说流传开来的时候,便给这个曾经的宁静富庶之地带来了许多灾难,特别是在社会动荡的时期,自然有不少“棒老二”盯上这里。到了实地一瞧:这么富庶,藏金都不用去找了,直接动手抢吧。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黄金镇一带成了渝东北匪患极为猖獗的地方,当地居民只能竭尽全力以求自保。后来,在大家族的带领下,有些地方的居民把整个场镇都搬到了山顶,依着地势从上到下层层设卡,封闭布局,比如大岭。而更多的还是就近选择险地构筑寨子,屯粮积物,平时在场镇居住,匪兵来袭时则立马转移,如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双岭古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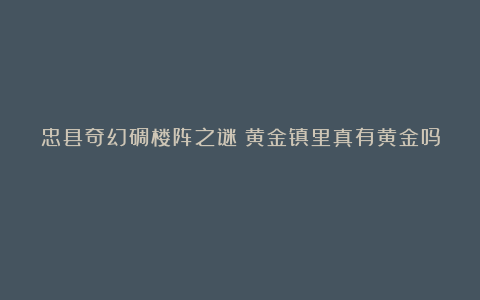
说到黄金镇的防御工事,就不得不提到小河碉楼阵。小河碉楼阵所在的山头以前也是座远近闻名的古寨,爬到山顶极目远眺,视线豁然开朗,山下四周全是浅丘和小河纵横冲击而成的平坝子,如若适逢金秋,便是满目的收获和幸福。
前往这里的路根本不用打听,老远就能望见一座小山拔地而起,四面都是峭壁而山顶十分平坦的“小桌子”造型极具辨识度。整座小山其实就是一块完整的花岗岩巨石,只有两条险要的小路连接着村落和山顶。说是小道,其实只是直接在已被风雨打磨圆滑的石壁上简单地凿坑连接而成,一条垂直得几乎无法攀登,另一条爬至险要处也得手足并用,一步踩滑便会跌下悬崖。
最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这座小山上还有一口神奇的大水井,水源充沛,冬暖夏凉,甘甜可口。黄金镇据险而守的古寨很多,但因为都是花岗岩石头山,饮水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只能挖掘大水池来收集雨水。但这样的方法在抵御民国时期的军阀、匪兵时就很吃力,他们往往就地抢粮抢财补给消耗,只需派少量人马将小山包围起来,寨里无论是饮水还是耕种都需要水,天气稍微干旱一些便难以为继。而这座小山的山顶处居然有一个能够源源不断涌出清水的水井,简直堪称奇迹,不过这水到底从何而来,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更奇怪的是,如果你在比这里低500多米的余家坝犁田,山顶水井的水居然会变得浑浊,因此关于水井与余家坝相连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难道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山下的水抽到了山顶?
关于水井,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传说。有一次,土匪将山寨包围了整整三个月,从春天一直围到了盛夏,但山上依然人声鼎沸,甚至市场还有戏曲之声。这可气坏了土匪头子,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损招:先劫持了一家隔壁村的农户为人质,再逼迫农户家的闺女佯装逃难到山寨,然后伺机在井里投毒。寨中居民见姑娘逃难至此便欣然接纳,但当土匪正信心满满地等待阴谋得逞时,却发现山寨内依然是每天歌舞升平,而自己的手下却接二连三地因为吃了河里的鱼而中毒身亡,这可把土匪头子吓坏了,以为是天降惩罚,赶忙带着土匪们落荒而逃。后来人们便传说是因为井水与小河连通,毒药都沉积在河水中被鱼吃了,山顶的水反而被稀释得没有毒性了。
传说归传说,但这座孤独的小山确实饱受匪患之苦,没办法,谁叫你这么显眼呢,像灯塔一样老远就能看到,省了土匪在山里到处转圈的功夫。此外,优越的条件自然也激发了土匪们想要据为己有的欲望,哪怕遇到政府军队的围剿也能不愁吃喝地守到天荒地老。于是,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堡垒反而成了重点“关照”对象,土匪来了一波又一波,手上的家伙也随着时代发展鸟枪换炮,如此一来,再坚固的堡垒也扛不住啊。
山寨不停地改易主人,一直到山下的方家崛起后接过了这里。他们反复总结过去攻防中的经验教训,组织族人对小山进行了详细的勘察研究,一改以前单纯地加固寨墙、设置关卡的老办法,有计划地在山顶布设了一个由三座碉楼组成的三星阵。三座碉楼的朝向正好可以确保四周完全没有死角,高度也可保证发现异常的位置燃烟示警后,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将物资转移上山并完成布防,同时还可与周围场镇形成联动。
碉楼总体规模基本一样,高约40米,底部面积约30平方米,以规整的巨大条石砌成,楼体设计有5层,每层都开有窗户和石孔。这些石孔外小内大,可供火枪或弓箭射击,设计有石模活塞,平时塞上避风避弹,瞭望、射击时则可取下。其中两座碉楼扼守上山入寨之要道,要进入寨中只能只身侧着从悬崖和碉楼间极狭窄处通过,而四周寨墙密密麻麻的射击孔足以确保万无一失。另一座位置稍高,与其他两座相互照应,三座碉楼形成犄角之势,由石围墙沿着悬崖边缘无缝连接。中间为一片开阔的空地,毫无遮挡,平时为良田,战时方便人员调动。
虽然只有三座碉楼,却已然是铁桶之阵。三座碉楼分别由方静如、方成云、陈佑义三个最有实力的家族出资修建,并亲自居住把守。碉楼阵气势雄伟异常,在山下,无论从哪个方向,总能至少醒目地望见一座,而站在山顶2000平方米的硬石平面上,前后皆是悬崖峭壁,碉楼围成一个三角形阵列,又仿佛置身于魔法坛的中央。“三星阵”修造完成后,小山再也没有被土匪侵扰过,其震慑能力可见一斑。
解放后,三个家族的主人相继去世,后人纷纷迁至其他地方居住。20世纪60年代,碉楼所在地曾经办过学,名叫峻岭中学,设有约五六个初中班,直到70年代末才停办。老人们聊起当年上学时的有趣经历,仿佛历历在目,但当笔者亲身攀爬过后,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险要之地读书的奇幻场景。
END
本篇文章发表于《重庆旅游》2022年7月刊
文 | 寒溪夜浣
图 | 寒溪夜浣
排版/编辑 | 崔红
文章来源:《重庆旅游》杂志
对生活有更高追求的人
都选择了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