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和娃一起乘坐高铁来到了烟台。窗外的风景像被拉长的胶片,一格一格地向后退去
我问,第一次坐高铁,你开心吗?
答曰,我开心是因为要见到姐姐,而不是因为第一次坐高铁。
心里涌上无限温暖。
在我有限的认知里,烟台是个美丽而遥远的所在,仿佛挂在墙上的那座北极星挂钟,永远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清脆地走着,却触不可及。
却没想到女儿的工作和烟台结了缘。
从此,这个遥远的所在也成了我的牵挂的地方。
记得小学三年级那年,父亲从县城买回北极星挂钟。我们围着它看,感觉很新奇。他踩着高高的木凳,把挂钟端端正正地挂在土墙上。母亲扶着凳子,眼睛盯着钟面上“中国-烟台”的字样,轻声地念疲道“中国一烟台”“中国,烟台,”父亲笑着说,“还中国一烟台。”母亲笑着接话:“不就是中国一烟台吗?中国就一个烟台嘛。”我们都笑了起来,那笑声撞在土墙上,又弹回来,撞得满屋子都是。
那挂钟走得极准,每到整点,便清脆地报时,“当——”的声音传遍屋子的每个角落,在院子里也能清晰的听到。它兢兢业业地提醒我们时间的存在。
母亲在锅屋里做饭,清脆的钟声穿过油烟飘来;父亲在院子里修理农具,钟声伴着金属碰撞的声响;我伏案写作业,钟声与笔尖摩擦纸张的声音交织在一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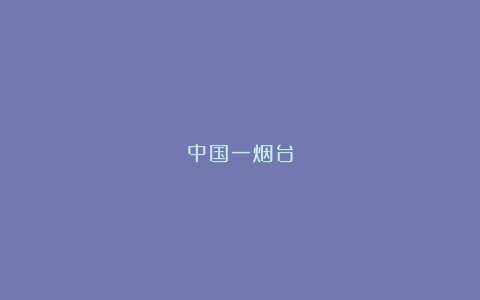
那个挂钟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清脆的钟声一直悦耳动听,不知疲倦。
我以为它会一直陪伴我们走下去。
母亲走后,那挂钟渐渐失了生气。先是走时不准,后来索性停了摆。它就那样静默地挂着,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便彻底消失了。
如今,我站在烟台山高高的灯塔上,凉爽的海风迎面扑来,带着咸涩的气息。远处,一艘艘帆船缓缓驶出港湾,海鸥盘旋其上,发出清亮的鸣叫。海天相接处,一片湛蓝,波光粼粼如碎银洒落。
坐船出海的时候,女儿和儿子都兴奋地看着海面,拿食物喂盘旋在我们周围的海鸥,聪明的海鸥会精准地接住他们抛出的食物,惹得孩子们开心地笑。
我望着那片无垠的蓝,忽然湿了眼眶。
原来”中国一烟台”五个字,承载的不仅是童年的欢笑,更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那挂钟早已不在,但它的声音似乎还回荡在耳边,与此刻的海风和海鸥的鸣叫混在一起,让我恍惚间看见母亲站在老屋的门口,笑着望向墙上的挂钟,笑着说“中国一烟台”。
原来,烟台并不遥远,它一直在我心里,只是我用了近半生才走到它面前。
原来,烟台在我心中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是我童年里那个会报时的家庭成员,是母亲笑着念出这几个字时眼角的细纹,是父亲踩着木凳捧着挂钟时摇晃的背影。
当帆船驶向远方,我看见自己的影子投在海面上,碎成无数个光点,就像那个早已不知去向的挂钟,曾经把时间分割成无数个清脆的声响。
海水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激起的每一朵浪花都在诉说着,有些地方,我们以为很远,其实它一直住在我们的记忆里。
每一处,都藏着时光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