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龙骨”还只是个药方上的名字时,谁会想到它连着我们的老祖宗?甲骨文,这个听起来既神秘又有点遥远的词,差点儿消失在炒药粉的锅里。怪不得现在说起,隔着百年都让人捏把汗:要不是那年头有个好事的王懿荣,也许我们今天连字是怎么来的都摸不着门道。
老王并不是天生就和甲骨文有缘。话说清朝日子渐渐不好过的时候,大家还没有什么“文物保护”的概念,更别提对“挖祖坟”这事儿有啥愧疚。那时候,龙骨在药铺卖得挺火,号称能治虚去邪,扛得住跌打损伤。谁闲着研究上头那些歪歪扭扭的划痕?老药匠抓药手松点儿,直接砸碎了卖,图个省事。要不是凑巧,王懿荣那次吃药没病死,倒差点成了“灭种案”的见证人。
王懿荣的好学还真不是瞎吹。家里是祖上传下来的官人世家,念书讲究、写字认真。进了京,跟着父亲混官场,别人捋胡子打盹,他在角落里翻碑找印。家里头客人多,茶水一端,他就站在一旁瞄几眼,见了稀奇字画就凑上去瞅。要不说人才呢?京里金石圈子里都知道老王能“识宝”,真伪、年代,信手拈来。
可那天,他压根没想当什么民族英雄。他只是肚子不舒服,去鹤年堂寻个方子,等抓药时候眼睛瞄到桌上一堆药材。说起来,抓药那会很随意,师傅手上全是药粉灰。可王懿荣就是手欠,他细看那块所谓的“龙骨”,喉咙一哽——这玩意儿,怎么有点像写字?
换了别人,也许摸着脑袋回家睡觉去了。老王不,他偏有那股较劲,把药包全倒出来,扒拉出所有“龙骨”。可惜岁月无情,药铺为方便病人把骨头敲得粉碎,只剩点零零星星的碎片。老王没灰心,把桌上一堆小骨头当拼图玩,一片一片摞着看,看得桌子上落了半层灰。
拼来拼去,终于出现了一点模样。他虽然认不全那些字,但凭着多年见多识广的底子,心里有谱——这不是现在的文字,这可是“古物”!一时间,惊喜、纳闷、说不上来的兴奋在心里炸了窝。
不过,想单凭几小块骨头拼出个历史,难度堪比拿糖渍橘子皮搭一座城。老王没法,只好找上熟识的古董商人,把自己的新发现如数家珍地掏出来说:兄弟,帮我大批收些“龙骨”来。我可不是想养龙,是想追点老祖宗的下落。商人大眼瞪小眼,真没听说过有人大把花钱买“药骨头”的,心里头犯嘀咕。不过碍于老王面子,也就答应跑一趟。
几个月过去,商人带回满满几筐龙骨,算是对得起老王的信任。王懿荣一头扎下去,白天官场、晚上家里加班,把这些骨头翻来覆去地看。他有了“大量样本”,拼出来的字越来越多了:有的像画,有的像字母,全都带着一股神秘的沧桑气。
正当他兴致冲冲琢磨如何进一步时,大清国祸起萧墙。八国联军打进京城,风声鹤唳。历史喜欢跟人开这种玩笑。王懿荣自觉无力守护京都和家人,这个学问人,只能以命殉国。跳井的那天,甲骨文字其实还没见天日。谁说身后事是大燕南飞,分明是半截谜团留在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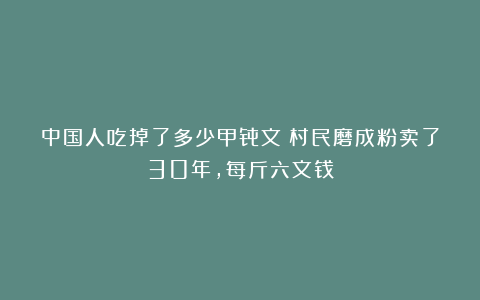
甲骨的故事没有王懿荣,就只剩下一地碎骨和一页药方。可也没因为王懿荣的身死就断了气。风水轮流转,到了罗振玉手里,甲骨又活了过来。
罗振玉是个有心人,他官场不怎么顺利,学问倒是越蹦越高。他琢磨着龙骨都是从一个叫小屯村的地方“流出”。向导领着他,一路打听,才明白当地卖药材的乡亲不过是挖田时碰巧翻到这些骨头。第一块“龙骨”怎么成了药——说起来也讽刺。当年有个村民受伤没钱看病,地里刨出块骨头,谁知道是不是“祖宗牌位”,也没管,打碎了糅水敷头,伤口居然好了。有人赚钱了,消息就传开——村里挖骨成行当,卖得欢,谁想过这玩意儿能上博物馆?
三十年下来,斤两论价,廉价得让人心疼。想想有多少历史,成了药渣、骨粉,被吃进了肚子。罗振玉心里感慨,不愿意让更多的老骨头被糟蹋了,下了狠心,用尽所有积蓄连夜收购,甚至托家里往回传银子。供应商们一见价高,那可乐坏了,纷纷从自家地头找龙骨卖。罗振玉见势,干脆请村民大规模挖掘。
你可能没想到,这些“龙骨”其实花样百出。圆的方的,乌黑的雪白的,不是一个样。回到京城,罗振玉带着一批骨片,找来了同门好友和金石圈子的人,一起琢磨那上面的符号。几夜没合眼后,他们得出的结论——这不就是我们老祖宗写下来的秘密?殷商、商王、古人的祭祀、天文、战争……全都刻在这一块块破碎又顽强的骨头上了。
可惜,消息一传开,古董商、洋人也都赶来了。甲骨片成了“艺术品”,价钱水涨船高。一时间,小屯村热闹非凡,骨头能买头猪,有钱人争着挖、进京客争着买,还有德国、日本的商人生生“搬空”了一地龙骨。这出热闹带来的是一场洗劫。有人发财,有人流泪,更多甲骨片开始流落海外,塞进了柏林、东京、巴黎的博物馆——咱的东西,人家锁柜了研究。
有些人也许会问:东西出国了,还能再要回来吗?答案很难说。建国之后,国力还未恢复,想收回流失文物也只能望洋兴叹。好在,国内还是有许多爱国的藏家和普通人,自发捐出家传一代的甲骨,像刘晦之——人家一口气捐了两万八千片,不留子孙,放进国库。还有后来的一批批捐赠者,或多或少都为这段文化续上了一点火种。谁说百姓没力量?“识一字,领十元”的活动,成了“全民识骨”热潮的开端——安阳的老乡也许不懂甲骨学,说不定却认识了自己祖上的文字。
这些年里,甲骨文就这样从药材铺的昏黄灯光下,一点点被抠出来,安放进展柜和书页——有一部分永远留在了异乡,但剩下的,足够让我们再一次咀嚼自己民族最早的声音。
回想当初,王懿荣弯腰在药铺里多瞅了几眼,谁能想到那一眼,就是一次民族记忆的救赎?甲骨文既不是哪个专家的“专利”,也不是哪本书的注脚。它是在碎石、残骨、药粉、买卖与烽火中,一点一点拼回来的我们。我们和千年前的祖先,其实也就差了这么一层骨头的厚度和一个发现者的好奇心。
到今天,甲骨文仍旧不是“解决完”的故事,它还在等人释读,等新的声音答案。要说文化的根脉在哪里?大概,就是那些不经意被人误解、差点被忘记、最后有人认得出来,重新点亮的温暖。也许下次,我们还能把散落世界的骨片,一片片拼回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