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白斋语】最近有个词非常火爆,就是“开窗”。在一个空气闷热的屋子里,有人扇扇子,有人打坐,有人装睡,一百个人有一百种驱热之法,却很少有人去“开窗”,哪怕有想法,也未必有行动。鲁迅也曾说过,在一个黑屋子里,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那么在我们中国哲学历史长河中,究竟谁是“开窗”者?
人类自有思想以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活着为什么?”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由此产生了哲学。我们之前叫“道学”。由于解读角度与途径不同,由此而产生了佛教、道教、儒学等等。其实无论三教九流,说来说去也无非是解答上面几个问题。曹先生从诸子百家说起,从头到脚梳理了一遍,把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讲得明明白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当下,我们有幸身处盛世,可以纵观上下五千年,从农耕时代到手工业、到工业,再到信息时代、AI时代,人类也从愚昧走向了文明、超文明。站在历史的这一端,再去看长河中那些睿智的思想,不免感慨。古人在没有高科技现代化的那个时代,对宇宙、对生命的探索却走在了前列。
每一个时代都有时代的“开窗”人,韩愈当是,李翱当是,范浚当是,吕祖谦当是,曹梦岐当是,不一而足。韩愈把接力棒交给李翱,对他说:“人生一世间,不自张与弛。譬如浮江木,纵横岂自知。”人生如果不能张弛有度,进退自如,那么就会像江面的一块浮木,失去方向,飘到哪里算哪里。李翱去见惟俨大师,问他:“什么是道?”惟俨伸出手指,指指上面又指指下面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如同醍醐灌顶,心中宛如黑暗的室内亮起明灯,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正因为一代又一代先贤们无穷尽的探索,才有了我们一步步地认清生命的真谛,认清科学的原理,认真世界的本来。曹先生是一位活得很真实,思想很独立的先生,从头到尾梳理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脉络,且随他的笔触来神游吧!
【原文如下:】
“道学”,即“宋明理学”,也就是今人所谓“新儒家”。
关于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两汉儒士有他们的解说,魏晋玄学家也有他们的解说,两宋元明理学家又有他们的解说,可是到了今日,我们即如顾颉刚、冯友兰、宇同诸先生,也已有我们的新解说。这一点,我得重新提出来说一说,一般人只是重复前人的解说,但事实上必须在现代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之下,把前代的学术思想重新解说过。
在隋唐佛学全盛时代,有一个近于传说的人物,即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说是他的弟子满天下,唐朝创业的将相,如房玄龄、魏征、温大雅、陈叔达辈,都曾北面受王佐之道。他的弟子们说:“吾师其为人乎,自仲尼以来,未之有也。……续《诗》《书》,正礼乐,修玄经,赞《易》道,圣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毕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可是,文中子的思想学说究竟如何,我们无从知道,看来也只是张良、诸葛亮和唐代李泌这一型的人物呢!
冯友兰氏说,真正可说是宋明道学家先驱的人物,应该说到韩愈(退之)。“韩愈邓州南阳人,长庆四年(八二四)卒,年五十七。……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倚天下正义,助为怪神。愈独喟然行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跆而复奇。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距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乱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荀况、扬雄为不少矣。”即是说,在佛学全盛时代,站在儒家立场来反佛家与道家,韩愈是第一个战士。
韩愈那一篇著名文字《原道》,并不是很好的说理文字,但文中有如次一段话:“……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苟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正足以代表宋明道学家的基本论点。——这儿得让我插说一句:后世人以为韩愈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唐代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力,殊不知唐、五代、北宋初年那百五十年中,并没人知道韩退之其人,韩愈文章为后人所认识,还是欧阳修所重新提倡出来的。这和一般人的想法,完全不相同。再则韩氏所说的“道统”,即宋明道学家所说的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算作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传的“道统”,经过清代考证学家的考证,证明了这十六字心法并非尧舜相传的古训,而是战国时人所伪造的。这都是我们该明白的,不要再随着前人人云亦云了。冯氏提出了几点该注意的事,(一)韩愈推尊孟子以为得孔子之正传,乃成为宋明以来的传统见解,和两汉儒士尊荀学的不相同。(二)韩氏首先引用《大学》,《大学》乃《礼记》中的一篇,前人很少注意过。韩氏以其中有“明明德”、“正心”、“诚意”的话,所以引用了,也和当时的有兴趣的问题有关。(三)韩氏提出“道”字,又为道统之说,遂为宋明新儒学之新名。
我们还该明白一种辩证的情势,思想文化的演进,决不会像蒸溜水那么单纯的。韩愈是反佛教的,但他的观点中,却受了佛教的影响。韩氏《与孟尚书书》云、“潮州时,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又《送高闲上人序》云:“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心必泊然无所起,其子世必淡然无所嗜。”其彼此亲密态度和当年反佛教的意向大不相同了。
和佛教思想最相接近,而又建立了儒家新观点的,有韩氏的友生李翱。他的《复性书》上、中、下三篇,上篇总论性、情及圣人,中篇论所以修养成圣之方法,下篇论人必需努力修养。冯友兰氏说:“李氏仍用韩愈《原性》中所用的‘性’‘情’二名词,然其意义中所含之佛学的分子,灼然可见。性,有若佛学中所说之本心;情,有若佛学中所说之‘无明烦恼’。众生与佛,皆有净明圆觉之本心,不过众生之本心为无明烦恼所覆,故不能发露耳。如水因有沙而浑,然水之为水,固自若也。然无明烦恼亦非与净明圆觉之本心,立于对待之地位。盖无明烦恼,亦须依净明圆觉之本心而起也。李翱亦云:性与情不相无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他又说: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明与昏谓之不同,明与昏性本无有,则同与不同,二者离矣。夫明者所以对昏,昏既灭,则明亦不立矣。明者所以对昏,所以“性不自性,由情以明’也。上文云:情不作,性斯充矣。圣人能向此方向以修养,即所谓复性也。然所谓“情不作’者,亦非是如木石之无情。李翱云:“圣人者,岂其无情也?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六祖坛经》谓: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李翱此所谓无情,亦于情而无情也。圣人虽有制作变化,而其本心则常寂然不动。此即所谓“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也。圣人之此种心理状态,名曰诚。到了“至诚’的境界,即能与天地合其德,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即已与宇宙合一者也。”——佛家成佛,儒家成圣,都是最高的境界。
到了北宋,佛家之徒,也讲《中庸》。如智圆自号中庸子,作《中庸子传》,契嵩作《中庙解》,这便是融合儒、佛成为新儒学的开端。可是如冯氏所说的,新学之中,又吸收了道教的分。(如汉代经学家吸收了阴阳五行家的思想。)道教中,也吸收了儒家的经典,如《周易》是也。《周易参同契》相传为东汉魏伯阳所著,南宋朱熹曾替《参同契》作注说。
道教的经典,如葛洪《抱朴子》,曾说:“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使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俞琰说:“盖人在天地间,不过天地间一物耳;以其灵于物,故特谓之人,岂能与天地并哉?若夫窃天地之机,以修成金液大丹,则与天地相为始终,乃谓之真人。”冯友兰氏说:“‘窃天地之机’,‘夺取阴阳造化机’,‘役使万物’以为吾用,以达吾之目的。此其注重权力之意,亦可谓为有科学精神。……惟对事物有确切之识,故能有统治之之权力。道教欲统治天然,而对于天然,无确切的知识,故其对于宇宙事物之解释,不免为神话,其所用以统治事物之方法,不免为魔术,然魔术尝为科学之先驱。”此意得之。
我曾经说过,一种学术思想,便是那一时代的人,在那一社会环境中,对社会人生问题的一种新的解说。朱熹化了一生心力,把孔子的学说重新说了一遍,他自以为“吾道一以贯之”了。到了今天,在我们看来,简直不是那么一回事,因此,事事都得重新说起。
宇同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以《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为题,说了如次的一番话。第一,中国哲学中,向无现代英国哲学家怀悌黑所破斥的“自然之两分”。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为二事,未尝认为实在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而认为现即实,实存于现、这即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根本与非根本是可以分的,而不得妄辨实幻,不能说惟根本的为实在,非根本的便非实在。中国哲学不以实幻讲本根与事物之别,实在是一个很健全的观点。(自然之两分,乃印度与西洋哲学的大蔽。)
第二,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变易大流,一切都在变易中,而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无穷无尽的变易历程。然而变易有其条理,宇宙是有理的,一切都有伦有序,不妄不乱。字宙是生生之流,而生生有其常则,生生亦即根本的常则之一。同时承认变易与条理,而予以适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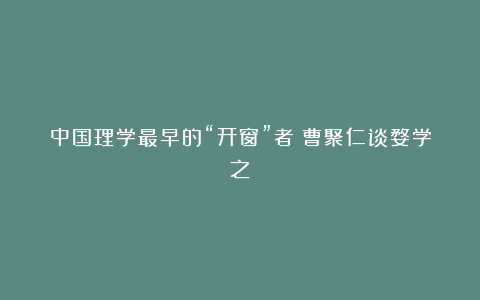
第三,中国哲学既承认变易条理,于是对于变化之条理颇有研究,其结果即是“反复”与“两一”的学说。变化的公式,是极则反,变化的所以,在于两一,即对立统一。固然反复的思想尚未脱离循环论的形式,然决不能说只是循环论而已,而实与西洋哲学中辩证法有相似之点。两一的理论虽颇简单,实甚精湛。(中国哲学,始终以为反复、两一是客观世界的规律。)
第四,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人生至道论,即人生理想论。而人生至道论之最大贡献,是人我谐和之道之宣示。孔子的“仁”墨子的“兼”,都在讲人我谐和之道。孔子的仁是阶级社会中的仁,然仁之本旨,固无内在的阶级性。墨子的兼,以自苦为极,未免有违于人情,然“兼”也不必以极端苦行为实践形式。要之,孔子的“仁”,墨子的“兼”,其本来表现形态实有时代性,而人我之谐和,是永远应注重的。
第五,中国哲学最注重身心实践,将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认为至理的实践不在现实生活之外,而求在日常生活中表现至理。所谓“践形”,所谓“与理为一”,便是“广大高明而不商乎日用”的境界。中国哲学家大都认为人生是严肃的,人之生应异禽兽之生,所以人之生活应有训练,应有修养;而学术之探讨,其鹄的乃在于提高生活。知识理论与生活实践,不可分为二事。印度哲学主脱离现实而别求究竟,西洋哲学不兔分知识与实践为二,中国哲学则主于现实生活之实践中体现究竟真理。
第六,中国哲学中的致知论颇为简略,而有一笃实可贵的倾向,即直截了当地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其所以如此,实即由于不分知识与实践为二事所致。……直截承认物之外在与可知,或不免被讥朴素。然而,如是真理,朴素何害?如非真理,纵讲得精微,亦不过善于诡辩而已。
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谈宋元明以后的学术思想了。
(选自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原题《道学初兴》)
附人物简介: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余毅等,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等,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建国后,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称誉为“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1909—2004)】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省沧州市献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著有《中国哲学大纲》等。他认为学术的基本方法有三,一为思与学的统一,二为知与行的统一,三为述与作的统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是接受已有的知识,思是独立思考。学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识而不进行独立思考,则将迷惘而无所得。思而不学,不接受已有的知识,则将陷于荒谬。研究学问,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独立思考,发前人所未发,取得新的成果。学是基础,思是在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独立思考,以达到前人所未达到的更高境界。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宇宙万象是无穷无尽的,人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认识亦尚待提高。因此,思与学都是没有止境的。
【王通(584-617)】字仲淹,又称文中子,祖籍山西祁县,后迁至隋朝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万荣县通化镇),隋朝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学者。从小受家学熏陶,精习《五经》,被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其著多失传。其弟子姚义、薛收编辑《文中子说》,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为后世所重视。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
【李翱(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属甘肃秦安东)人。西凉王李暠的后代。唐代官员、哲学家、文学家、学者、诗人,古文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李翱自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二十五岁时,在汴州与韩愈相识。从此追随韩愈,经常与韩愈一起谈论学术文章,维护儒道,反对佛老,积极倡导古文运动。贞元十四年(798年),李翱中进士。初任授书郎,后历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考功员外郎、礼部郎中、中书舍人、桂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他在儒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试图重建儒家的心性理论。他所撰写的《复性书》以《中庸》和《易传》为宋代理学家“心性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李翱把“性”与“情”分开,认为“性善情恶”,启迪了后来理学家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也成为理学家“天理”和“人欲”之辩的根源。他提出“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的所谓“正思”的修养方法,对北宋程颢、程颐“主敬”观点的推出影响很大。
【释智圆(976-1022)】字无外,自号中庸子,或称潜夫,俗家姓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初僧人。984年,释智圆受戒于杭州龙兴寺。997年,从奉先寺清源法师学天台教观,孜孜研讨经论,撰著讲训,为天台宗山外派义学名僧。1016年,居西湖孤山玛瑙禅院,世称孤山法师,与隐士林逋相往还。喜读儒家经典,学古文以通其道,吟诗以赋其情性。其论文重道轻文,著有《中庸子集》等。
【契嵩禅师(1007–1072)】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出生于镡津(今广西藤县)。宋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年),文学界兴起古文运动的热潮,敬儒学,排佛教。契嵩禅师写成《辅教篇》,阐明儒佛二教的思想实质,上奏朝廷,以反驳欧阳修等人的辟佛之说,轰动当时文坛。契嵩成名之后,谢绝仁宗和士大夫的挽留,毅然离京,返回南岳衡山,闭关修道,号“潜子”。出关后云游到杭州灵隐寺,撰写《正宗记》和《禅宗定国图》两文,再次前往京都开封,万言书《上皇帝书》令仁宗大为赞叹,赐紫方袍,号“明教”禅师,留住在京城闵贤寺。时隔不久,契嵩又东游回到杭州,居住钱塘佛日禅院和永安院。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四日早晨,契嵩禅师召集大众,吟颂说:“后夜月初明,吾今独自行;不学大梅老,贪闻鼯鼠声。”言毕在法座上双盘而坐,闭目禅定,到午夜时分,涅盘示寂,安然坐化西去。有《镡津集》二十二卷。
【葛洪(约283年–约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世称小仙翁,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东晋时期道士、道教学者、炼丹家、医学家、科学家。出身于江南豪族,13岁丧父,家道中落。16岁起,广览经、史、百家,以儒学知名。后从方士郑隐学道。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葛洪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自行请求出任勾漏令。赴任途经广州,刺史邓岳表示愿供其原料在罗浮山炼丹,葛洪遂决定中止赴任的行程,从此隐居于罗浮山。葛洪在朱明洞前建南庵,修行炼丹,著书讲学。有《玉函方》一百卷(已佚)和《肘后备急方》三卷等。其妻鲍姑,著名炼丹家、精通灸法、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女灸学家,葛洪得力助手,葛逝后其著多为她整理,人称鲍仙姑。
【俞琰(生卒年不详)】字玉吾,号林屋山人、石涧道人、全阳子。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县)人,祖籍河南开封。中国宋末元初时期道士。少时博览群书,闻友人有奇书异传,必求借抄录,以致废寝忘食而成疾。尤好鼓琴作谱,以词赋见称于世。少时学志于科举,十六岁时即已三场粗通,应乡贡进士。宋亡后,归隐山林。喜《易》学,精通老、庄之说,遂援引儒家之论,以证道教丹道理论。著有《周易集说》《易图纂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