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穴居巢居,到以土、木为主要材料建造地上房屋,在不断的实践中创造了种类繁多的建筑,同时也创造了美的建筑装饰。随着建筑的发展,建筑装饰也不断展现出夺目的光彩。山西襄汾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白灰墙面上刻画的图案,可能是我国已知最古老的居室装饰。陕西凤翔县出土了春秋时期秦都雍城遗址的数十件铜器,有学者考证为当时木建筑构架上的箍套,用在横、竖木构件的连接部位,起加固的作用,古代称为“釭”,因为它用金属制成,所以又称为“ 金釭”,这些金釭表面有压制的图案,有的顶端还做成锯齿形状,说明在这里金釭既是一种力学构件,同时也是一种建筑的装饰。秦汉时期的墓葬建筑物遗存,地上有完整的墓阙,地下有砖、石筑成的墓室,它们都富有装饰意味:墓阙,微微凹曲的檐口和翘脊是一种削弱僵直感的审美意识,脊端添加的凤鸟更是为了美化阙,阙身上往往有雕刻装饰,在墓室的砖、石上多刻有丰富的装饰性纹样。再结合明器和墓砖、墓室壁上的建筑形象间接材料,表明秦汉时期建筑装饰已经比较普遍使用了,也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建筑的装饰艺术和中国建筑本身一样地历史悠久。
山西襄汾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
战国赵邯郸城刻有纹样的砖瓦拓片
汉代墓葬所用砖石多刻有纹饰
应该说,古代文献对建筑装饰的描绘比起现存实物遗存要丰富得多,据《三辅黄图》记载,萧何主持所建的未央宫的大殿“以木兰为棼(fén)橑,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木表)璧珰,丹楹玉碣,叠轩镂槛,青琐丹墀,左橑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棼、橑、楹、槛是建筑上檩、椽、立柱和栏杆的古称,碣、墀是古时对碑和台阶的称呼,这段文字说明当时已经用珍稀名贵的材料制作建筑构件,有了色彩装饰,除了玉石、黄金、石料本身的颜色之外,还在构件上涂抹颜色。虽然古代文献的描绘难免夸大,但从今天能见的秦始皇兵马俑以及大量秦汉时期的墓葬工艺品,都可见装饰功能早已渗透其中。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数朝,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可以说已形成独具特色的建筑装饰体系。
出土于四川成都的东汉“凤阙”表明当时建筑前常有这种木、砖、石混合结构的阙
墓阙微微凹曲的檐口和翘脊是一种削弱僵直感的审美意识,脊端添加的凤鸟更是为了美化阙,阙身上往往有雕刻装饰
不仅是对建筑部件的修饰和美化,而且是对整个的建筑群,符合人们观念心理、审美趣味的艺术处理,如:外形与轮廓(南京六朝萧景墓)
空间与节奏(安徽歙县棠越牌坊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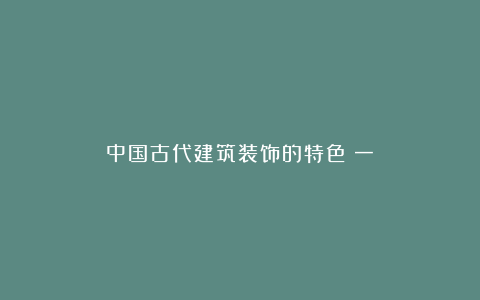
在建筑的装饰艺术实施过程中,古代人很早就注意实现两个统一
(一)、实用功能与装饰功能的统一,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说“中国的古代建筑是最善于对结构部分予以灵巧的艺术处理的”,“结构和装饰的统一是中国建筑的一个优良传统”。所有的装饰手法都是在一个实用的部件上进行,如额枋上的彩画、栏杆上的石雕、窗棂上的刻花,很少出现凭空多余的装饰。反之装饰不会弱化功能,只会去强化功能。例如一扇隔扇门,下段虽然可以雕刻人物花卉、山水等花纹,但必须考虑防寒和防雨水,所以只能处理成浮雕,但上部格心部分,则不能制作成密密麻麻的浮雕,这会妨碍通风和采光,所以只能做成木条或花格,用来糊裱可以透光的纸或薄纱。同样,建筑的梁枋功能是用来承重,不能进行深浮雕,否则会削弱承载力,而沿海地区的石牌坊的人物群雕都尽量采用镂空雕,目的为减少海风的阻力。
材料与质感(关云台石刻)
沿海地区的石牌坊尽量采用镂空雕,减少海风的阻力
(二)、工艺技术与装饰艺术的统一。功能决定选材,材料选定,加工时随即就有了装饰造型的考虑,均顺理成章。例如要解决宫殿台基雨天排水问题,自然用石材导流最好,决定采用石材紧随就要考虑装饰问题,如果将排水口雕琢成龙首石雕工艺,这在技术上很容易做到,而且雨水从龙嘴中喷泻而出会很有气势,故宫台基有1142个螭首,“大雨如白练,小雨如冰注,宛若千龙吐水”的奇观,就是二者结合得好的实例之一。“建屋为用,美在其中”,造房子的目的是为了使用其空间,但美的问题从头到尾,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渗透在其中。
实用功能与装饰功能的统一:上部格心只能做成木条或花格,用来糊裱可以透光的纸或薄纱;隔扇门,下段虽然可以雕刻,但只能处理成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