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繁花千万,牡丹雍容、玫瑰炽烈、梅骨清绝,于我心中,却独独偏爱那一朵栀子花。它不是转瞬即逝的惊艳,更像一坛陈年的酒,初闻淡雅,细品方知醇厚,将两千多年的岁月酿成了清芬,成了我心中最能代表中国风骨的花。
早在汉代,栀子便已走入人间烟火。那时的人们发现,栀子果能熬出最灿烂的黄,那颜色明亮却不张扬,温润里藏着贵气,最终成了帝王专属的服色。一染一织间,栀子的汁液便与王朝的威仪缠在了一起,让寻常草木有了历史的重量。到了唐朝,风气开放,文人墨客开始欣赏栀子花的姿态,将它栽在庭院,看它在夏日里舒展花瓣,成了诗酒年华里的一抹清凉。宋朝人更懂它的好,把它请进自家院落,晨看露沾白瓣,暮听风送暗香,让这份雅致成了日常。
它的美,是素净到骨子里的。花瓣洁白如雪,没有一丝杂色,像被月光揉碎了洒在枝头,在炎炎夏日里静静立着,自带一股清凉气,仿佛连周遭的暑热都被它滤去了几分。古往今来,文人从不吝啬对它的赞美。杜甫说它 “稚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把它比作天真的孩童,赞它在世间稀有;杨万里夸它 “孤姿研外净,幽馥暑中寒”,点出它孤洁的姿态与消暑的暗香。而我最偏爱朱淑真笔下的那句 “一痕春寄小峰蛮,薝卜香清水影寒。玉质自然无暑意,更宜移就月中看”,寥寥数语,便把栀子的清雅、水影的灵动与月下的朦胧写活了,仿佛抬眼就能看见那株立在月光里的栀子,连影子都带着凉意。
这朵花,还藏着多重身份。在佛教文化里,它是清净的象征,常被供奉在佛前,花瓣舒展如莲,香气袅袅,伴着经文,成了连接尘世与梵音的纽带。在传统医学中,它更是全身是宝 —— 根能入药,叶可清热,连那朵娇柔的花,也能化作调理身心的良方,把温柔藏进了药香里。到了现代,它又成了生活里的小美好,提取的精油能制成香水,让花香随身;融入香皂,让洗手时都能撞见一份雅致,把诗意揉进了日常。
不同的地域,还赋予了它不同的意趣。在江南,栀子与茉莉、白兰并称 “夏日三白”,是水乡女子的心头好。清晨摘下一朵,别在发间,白瓣衬着乌发,风一吹,香气便随着步履轻轻晃荡;若是心上人要远行,便把栀子递过去,不言不语,却藏了 “此生不渝” 的心意。在岭南,广东人把栀子煮进了凉茶,汤色清亮,入口微甘,暑气便随着茶汤一同散去,让花香成了饮食里的一抹温润。在客家人的婚礼上,栀子更是少不了的吉祥物,花枝被精心摆放,花瓣洁白,寓意着婚姻纯粹,更藏着 “子孙满堂” 的美好祈愿。可这花也带着几分怅然,每当校园里的栀子开得热闹,空气中便飘起离别的味道 —— 毕业季到了,少年们抱着书本走过栀子树,花瓣落在肩头,像一句无声的 “再见”,把青春的记忆都染成了栀子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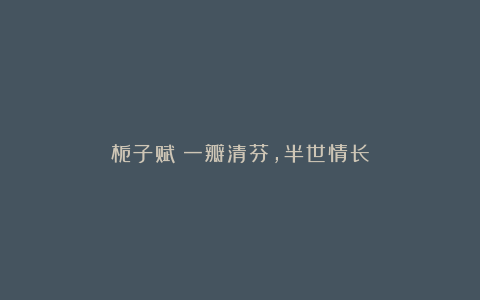
于我而言,栀子花从不是寻常花草,它更像我生命里那些沉甸甸的牵挂,悄悄开在记忆的角落,一瓣一瓣都裹着人的模样。
是母亲。老宅院的栀子树还立在那里,每年夏天都开得热闹。总见母亲坐在树下的藤椅上,满头银发被夕阳染得温软,手里攥着半择的青菜,指尖还沾着泥土,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巷口 —— 那是我每次归家必走的路。她从不说 “我想你”,只在我推门的瞬间,眼睛亮一下,起身把温在灶上的汤端出来,汤里飘着几粒葱花,温度刚好。可我分明从她发间又添的银丝里,从她反复擦拭的门框上,读懂了无数个 “盼儿归” 的黄昏,那些等待,都藏在了栀子花香里,无声却绵长。
是挚友。曾经我们一起坐在栀子树下读诗,风一吹,花瓣就落在书页间,轻轻一压,便成了最温柔的书签。后来我们各赴远方,她寄来的信里,总夹着一片晒干的栀子花瓣,花瓣虽失了水分,却还留着淡淡的香。信里的字写得娟秀:“今日见巷口栀子开了,想起那年你说这花香像我们的日子,平淡却踏实。” 字里行间满是 “别后盼相逢” 的惦念。如今我站在窗前望远方,风里若有似无的栀子香飘过来,就像她从未走远的问候,轻轻落在肩头,暖了整个心房。
也是爱人。那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像栀子香一样无形无影,却早已经融入了呼吸。是清晨醒来,挤好的牙膏放在杯沿;是雨夜回家,他撑着伞站在楼下,伞柄朝我这边倾斜,自己半边肩膀都湿了;是分别时,他站在站台,一直挥手,直到火车看不见。后来我们隔着山海,很少见面,可每当栀子花开,那些细碎的暖意就会穿透时光的壁垒,瞬间将我包围。我才知道,有些爱从不会被距离打败,它们就像栀子香,不管走多远,只要想起,就会漫满心间。
原来思念早被揉进了花香里。风一吹,花香漫过来,那些想念的人、牵挂的事,就都清晰起来。这香,是母亲的等待,是友人的惦念,是爱人的陪伴,岁岁年年,从未消散。往后的日子里,我还要守着这份栀子情,把岁月里的温暖,都酿成与它有关的故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