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认识徐炳南校长,还是在红旗中学任教的时候,或者说还能追溯到更早。上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紧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时担任黟县中学团干的徐老师正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组织的学校文艺宣传队在县城及周边乡村的演出大受欢迎,好评连连,徐炳南的名字也由此在老百姓当中传开。都说县中那位年轻的戴眼镜老师是上海佬,见识广、水平高。当时站在台下看演出的我就认识了他,可惜的是他不认识我。徐校长认识我是在80年代,红旗中学校园内,他的学生程信培家的酒桌上,我与信培(英语老师吴建白的丈夫)兄是邻居,咱俩一同在横沟弦长大,关系不错。信培请老师喝酒,邀我作陪,觥筹交错间,徐老师就认识我了。酒酣之处,也就有了愿意到他麾下干活的承诺,也就有了几年后在五通殿职高的两年时光。这短短的两年,竟也几乎成了我职业生涯中,行事最为愉悦的片段之一。
徐校长是上海人,其祖籍在广东省蕉岭县,抗战爆发那年出生在上海虹口区。他曾告诉我,自己家世代经商,为躲避战乱,出生不久便全家迁下南洋。其先祖在印尼有祖业,便在那定居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又从印尼迁回上海,算起来徐校长也算是归国华侨了。不过这也是他在酒酣微醺后说的话,平日里可是只字不会提的。1957年,徐校长高中毕业,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上海知识青年支援内陆山区建设,来到了黟县农村,以落户的方式安置在西武古竹村农家。那时一同来黟县的上海知青有180多人,如今我能记得他们名字的有王幸之、许铭城、陈克俭、江世清、朱贻琯、顾文忠、钱绪凤、陆全根、王懋林、钱锦成、周启东等。这批上海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偏僻闭塞、发展滞缓的黟县,带来了一股清流,刮来了一阵春风。往后的数十年,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大部分人都已经从农村走出来,走向各行各业,为这千年古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我想,这也是应该在地方史志中记上浓笔重彩的一笔,徐炳南校长就是其中之佼佼者。
那个年代的山陬小县,各个方面都稀缺人才,尤其在文教卫生方面尤为突出,仅教育,1957年的全县中等教育还仅有一所初中,处在皖南地区最落后的状态,读个高中,还要走到休宁的万安、屯溪。1958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掀起,各行各业大跃进,教育自然也毫无例外地随之跃进。这一年,全县小学由1956年的89所一下子发展到139所,两年猛增了50所。这一年,黟县初中开始增设高中部,易名为“安徽省黟县中学”。这一年,县文教科在麻田街天主教堂创办了“县初级师范学校”,县卫生科在西武乡陈闾村(后迁横冈村)创办了“县初级卫生学校”,县农水局在横冈村创办了“初级农林学校”(后易名为“安徽省黟县农业技术学校”,简称“农校”)。一年之间,增办了这么多学校,教师队伍就急需大量扩编。于是,1957年底来黟县的这批上海知青中,相当一部分人便走进了学校,走上讲台,当了老师。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县城碧阳小学就有好几位老师,如戴祝莉、张珊珍、刘玉仙等,他们都是上海人,该不是就是这批知青吧。徐炳南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了教师队伍,走进了黟县中学,并先后担任了学校团干、教务处副主任。文革期间,县中老师分散下迁,他先后到东源初中、际联初中、西武初中任教,继而担任了西武初中副校长。1983年,徐炳南校长领衔在渔亭原县玻璃厂旧厂房,创办了“黟县农业技术学校”,年底,学校搬迁至县城附近五通殿的县“三花园艺场”,更名为“黟县高级职业中学”。自此,徐校长就一直工作在这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调到黟县职业高中,再次见到徐校长时候,他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了。徐校长个子不高,脸庞消瘦,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眼睛炯炯有神。他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三十年,虽然头发有些过早稀疏,脊背也稍显有些佝偻,但其精气神却依然充盈旺盛。兢兢业业,忙忙碌碌一直是他的工作常态,在校园里见到的徐校长,总是手上拎着一大串钥匙,肩上挎着帆布工具包。农机坏了他能修,钥匙丢了他包配。就是平时在路上,见到了一枚小螺丝、小铁钉,他都会弯腰捡起来,装进挎包里。每天清晨,徐校长都会站在校门口迎接着师生到来。有时因半途自行车坏了而迟到的,他就会上前接过车,笑嘻嘻地说:“放学以后再来拿。”保证你在放学时能拿到修好的自行车。两年间,老徐概给我修了三次车,一次是脱链,两次是补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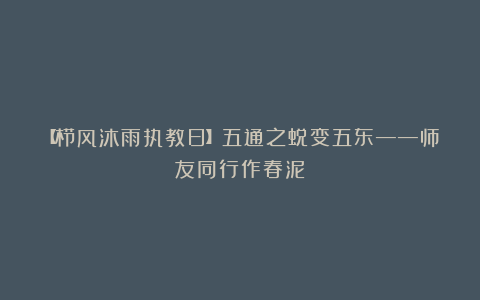
那个时候的职高,老师被要求一律在校住宿,且每星期五晚上还得集中学习两小时,这对我来说可是一大难题。当然我理由也很充分:双亲已年迈,小女读小学,爱人工作也是要频频下乡,还有一位残疾老哥需照应。故老徐特批我不必住校,可以走读,甚至还悄无声息地停止了“周五晚集中学习”,这是一项打建校以来雷打不动的规定。夜学习的取消,自然引起了一帮小年轻的欢呼,他们背地里对我说:“老徐的规矩,可不是一般人可以破的!”两年间,我随同他曾到碧山乡刨坑植树,到西武乡茶园除草,到对面孵坊帮忙潘银顺老师饲养樱桃鸭,到五里村观摩朱永安老师指导村民果树剪枝,参与郑仪老师指导学生制作茶叶,还随同他一道参加农科教活动方案制定、农业科技职业中专班教学计划研讨、森林经营管理中专班招生计划的拟定申报。两年里,他对事业的勤勉付出,对同仁的热情诚恳,对生活的严于律己,成了我人生中永远忘不了的印象。
当然,永远忘不了的印象,应该还有那么一大群同行伙伴们。在篮球场上、围棋盘前,还有西子湖畔的结伴活动。还记得咱们一帮人翘班,溜去青山分场围观《菊豆》的拍摄而一睹巩俐演技。尤其是中午开饭,那排平房前的空地上,“日头窝”里大家围成圈,一边用餐,一边聊八卦。每见此,徐校长不屑一顾,也不见批评,而学生见了却也有碍瞻观。我当选工会主席后,趁机向老徐进言,便在那排平房中挤出一小间作为“工会活动室”,实际上便成了我们中饭餐厅,于是又博得弟兄们一波好感。中午的餐厅不时有小聚会,少不了有汪荣禄额外烧的菜,有在松树林采的蘑菇,有在周边竹林掰的水笋,有一次还在苗圃里打了一条蛇。天寒地冻时节,有人会拿出一瓶酒,那是盐水瓶的散装酒,几口酒下肚,暖和一下午。记得经常到这里用餐的有吕青、汪建清、张贵元、黄胜、金文胜、黄旭东、叶杰辉、程新政、韩烨、王福英、余瑾、顾缨、赵宇等人。几年后,其中有十来人也先后调到县中,我们再度成了同事,且直到我退休。两年县职高的生活,转眼即逝。当徐校长在我的调离申请报告上签了“同意调离”的字样时,感觉他是有些情绪的,似乎在闷郁不快中,还交杂着理解与无奈。办完了交接手续,在“宴宾楼”的送行酒宴上,老徐说了不少话,也喝了不少酒,只是怎么也没能想到,这竟是咱俩的最后一次。
调到县中担任两个班的语文和一个班主任,日子甚是平常,在一个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徐校长带着职高的文化课老师到县中开展教研活动,这是我牵头与县中领导联系的。徐校长与县中江校长是早先县中老同事,自然没问题。一切都没有刻意安排,听课随堂听,评课随年级评,中餐也在学校食堂用餐。我恰好下午有语文课,便没有参加评课后的活动了。那天下班后,我回到红旗初中的住房,烧好晚饭,刚端起饭碗,就见职高的同事王福英老师(时丈夫友平兄也住红旗)骑着自行车从坡上飞驰而下,她来到跟前气喘吁吁地说:“刚才老徐回家路上被流氓打了,很严重,已经送到县医院!”听到这消息,我急忙丢下碗筷,立马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医院。急诊室内围满了人,只见老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双眼紧闭,头部肿得老大,隐隐还能见到斑斑血迹。我赶紧问前来抢救的主治大夫王跃建,只见他对着我只是叹气摇摇头。这时,县中的余耀斌老师也从外面闯进来,一下扑倒在床前跪下,嚎啕大哭起来。耀斌兄是徐炳南老师的得意门生,感情丰富,情感真挚。他这一哭,引起满室一片哭声,我自然也流下伤悲眼泪。
几天后,细雨蒙蒙,在县职高小礼堂的追悼会上,老韩宣读的悼词。悼词写道:“1983年,黟县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他奉命主持黟县职业高中的创办工作,为开创黟县职业技术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1985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教师”称号。1991年6月6日,徐炳南带领教师到黟县中学听课,下午回家途中,面对流氓滋扰,挺身而出,勇敢地给予谴责和制止,不幸惨遭毒打而牺牲,终年54岁。”事后想想,假如我没去牵头联系这场活动,假如那天没课也去食堂凑一下热闹;有假如在老徐到崇教祠看他当年住的房间时,再多聊会儿话,甚至拉住他吃过晚饭再走,这场悲剧或许就会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