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村小学坐落在孙村中心,沿着旋溪河的流向,恰好将村子一分为二。右侧称孙上,左侧称孙下,孙上的木桥对面称太平坦,亦属孙上的一部分。孙村小学也是两人一校,但办学条件要比湖田小学优越得多。面朝大路的一幢长长的砖木结构平房是校舍,两侧各是一间大教室,中间三间分别为教师住房和活动室。活动室在正中,刚能放下一张乒乓球桌,老师的房间门分别都朝活动室开,乒乓球桌也就成为我们的日常餐桌了。平房外面临一块操场,安有一副篮球架,脚下全都是泥巴土,算是简易篮球场。操场外便是三合大路,靠近孙下人家的一端,师生们自己动手挖了一个大土坑,又从河滩里挑来细沙填满,算是又添置了一件体育设施。平房左侧的一端,倚山墙有一小陂是厨房,相比湖田的多出了一口灶。
孙村小学也是两个班,近六十名学生,低年级一个班,为一二三年级;高年级一个班,为四五年级。低年级学生都是来自村内,最远的也是河对面的太平坦。高年级学生则是来自全大队,最远的有三合旋溪河最上面的锅铺村,有近二十里路呢!于是,又从两老师房间后面分别隔出一小间,提供给远道学生住宿,每年总有五六个。三合大队址在张村,作为一所大队完小不在大队所在地,而是在一个生产队的自然村,这在全县也算得上是唯一的了。
孙村小学也两人一校,我算一人,另一位便是汪老师了。他早我两年到孙村,自然是校长兼教务,我也官升了一级,总务兼少先大队辅导员。汪老师,即汪双武,十都宏村人,中等偏高身材,长得标致,尤其那高度近视眼镜后的那对眼眸不仅深邃,更是能透出一副俏书生模样。他是屯溪师范最后一届毕业生,才华出众,文采飞扬,虽比我大不了两岁,但却是我的又一位师父加兄长。我们在孙村分手后,双武兄先后出任了洪星、西武小学辅导站长,没几年便转行进了县委机关。双武兄参加过西递、宏村以“中国皖南古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工作,是申报文本撰稿人之一。他曾在多加家报刊发表过不少文章,著有《中国皖南古村落——宏村》《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两书,是一位乡土资深徽学专家。如今当人们分享“世遗”红利的时候,该不会忘记当年为之努力付出的那些人士吧!
三合孙村的生活是愉快的。沿着旋溪河,三合大队境内除了孙村小学,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一所“一人一校”的村小,这是那个年代“将学校办到贫下中农家门口”的特色。村小的老师中有好几位也是我的兄长,他们都给了不少帮助,使我在孙村的两年生活色彩更加多彩多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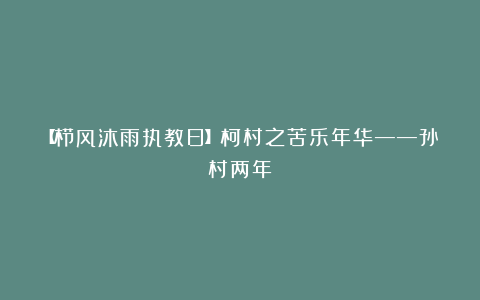
张村小学老师是刘芳胜,这是一位我打小就认识,并且同住在桂墩里的好邻居、好兄长。上世纪60年代初,我家曾住在老刘家隔壁。芳胜的父母,大家都称“刘先生、刘师娘”,一听就不难知道其家世的非同一般。刘先生在搬运站当搬运工,矮小的个儿扛大包、拉板车,虽然很是吃力,但迈出的步履却坚实无比。不管时间过去多久,如今只要一见到芳胜他们兄弟姊妹,桂墩里的往事就会一幕幕自然浮现在眼前。芳胜兄是刘先生家老三,个儿不高,却敦实精干。在桂墩上玩耍时,他那漂亮的前空翻和后空翻,成了我儿时的偶像。芳胜家兄弟姐妹多,全凭父亲刘先生在搬运站苦力收入,家境甚是艰难。我家搬到桂墩里,成为芳胜家邻居的时候,他大姐已经远嫁萧县。第一次喝到葡萄酒,就是在他家厨房里,芳胜偷偷倒了一些,说是大姐从萧县带回来的。二哥刘芳职,在文化部门工作,县黄梅戏剧团兴盛的那会儿,所有的舞台布景都是他绘制,直到安徽艺校毕业的史承武分配到黟县,才由两人共同承担。刘芳职有些异像,下唇厚大得有些过,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打小就称呼他“刘老师”而深深钦佩其才华。老四爱仙是位美女,下放当知青后,招干进了计生委,家庭事业顺顺当当。老五芳顺、老六芳美,打小我们就在桂墩上相互嬉戏打闹,关系自然是不错。长大后,他们先后当上厂长、经理,各为生活奔忙而很少见到,但只要一碰面,桂墩上的少儿情谊就会瞬间又萌发新芽!妹妹春仙是老幺,圆圆脸庞,两条麻花似的小辫,乳名叫“仙”。多年后,仙突然作为学生家长参加高三毕业典礼而出现在面前,我又一次深深感到了岁月如梭!芳胜兄是老三,小学毕业正逢三年自然灾害,便早早走上社会谋生以贴补家用。他砍过柴、挑过担、拉过车,还在麻田小学干过职员,再后来进了山,当了民办老师。几年后,娶了孙下的一位美女姑娘,算是在此安家落户了。199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受到了国家教委表彰。
余家畈小学的老师正是丁邦全,他是从翠林小学,与我同时调来三合的。至今我还记得当初他带我来柯村报到时讲的一段往事。他说:“到了柯村,首先要学会讲柯村话。我初到时,听不懂柯村话,就闹过大笑话。有天上课,我边讲课,边走下讲台来到课桌间过道。此时,有学生喊:“老师,’雅,雅’!”我不知道说什么,就虎下脸训斥他们好好上课’雅’什么。话还没说完,我便一脚踩上坨’屎’。原来学生是在提醒我,刚刚有小孩在过道间拉了泡屎。可惜我没听懂,太尴尬了。”打那后,我牢记了邦全兄的话。柯村六年,当地方言学得还真不赖,以至后来回到县城教书,柯村来的学生还以为我是他们老乡呢!
上世纪70年代小学的行政管理,公社称小学辅导站,大队便是小学辅导组。借着辅导组活动,隔一两个星期,三合大队的七八个教书匠就会聚在一块,或政治学习,或上公开课,或集体备课,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喝酒聚餐了。四周透风的教室里,三四张参差不齐的课桌拼成临时餐桌。喝的酒是在张村小店几毛钱一斤的山芋干酒,菜吃菜是遵循老规矩的派菜。喝了酒,吃了菜,月儿也爬上了树梢。接着,便是谈天说地、讲古论今到夜深,有时甚至到启明星高挂在山尖头。
派饭、派菜是那个年月的专用词。派饭,一般都是指公家人员进村工作,由生产队分派到农户家就餐。这对于能领到“派饭”任务的农户,是一份信任,一份荣光,派饭次数越多,说明公家对你越信任。派不上饭的除了“黑五类”户,还有“超支户”,当然知青户也是不会派到的。派菜,则有不同,这是我们山里小学老师独享的待遇,湖田、孙村小学的派菜,自然也不例外。孙村小学的派菜,是按学生座位顺序,如同值日扫地一样自动轮流。依照双人课桌,每天一桌,一桌两人;每人两菜,一荤一素。清早上学,轮到送菜的学生就会将炒好的两碗菜,端放在我们的窗台,或者房间外面的乒乓球桌上。四碗菜,两荤两素,足够我俩一天享用了。如果有外客到来,便会临时多派一桌,那就是四人八碗菜了,而且八碗都会不一样,似乎是学生们事先商量过的。有这么多菜肴招待客人,在那时的山里算得上非常丰满的了。
三合孙村工作也是充实的。我负责上一至三年级语文课,四五年级算术课,双武兄则反之,两人都是半天低年级,半天高年级。如果双武兄要到公社开会,那我就必须一人包下两个班。长长的走廊,左右两个教室来回跑,一天下来也挺够呛的,好在当时我也才二十来岁,扛得住。那个年代的小学老师,除了正常教学,还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开展扫盲活动、动员流生入学,甚至还要参加大队的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政治大清查等运动。为此,三合辅导组教改出了《三合教革》简报,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又出了《三合战报》简报,在“双抢”时节,还出了《战地黄花》的“双抢”简报。说是工作充实,其实是个忙得不亦乐乎!当年乡村小学的“教书育人”与生活实践、生产活动、文化建设的紧密结合,如今回想起来,还是挺怀念的,算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