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村小学的生活不仅一如既往于三合、湖田,而且还能经常过访于农中、医院、粮站、供销社,以及设在柯村祠堂的文化站等。成天虽然忙忙碌碌,但也甚是充实,唯一不如意的就是“一日三餐”了。山上的小学里除了柯绍林老师的家住在对面的竹柯村外,长住在山上的包括我在内共有五位。在站长老项的建议下,五人办起了“伙食团”。伙食团是那个年代的特色,近似于如今的“AA”制。单位有了“伙食团”,供销社的物资供应券可以多领到一些,工会福利费也可以些许补贴一点,只是“派菜”的活儿就不如下面的完小、村小了。
柯村学生送的基本上都是生菜,需要我们自己烹调,而且多半不会自动轮流,是真正意义上的“派”。不过好景不长,原先尚好的“伙食团”还没坚持到一个学期就散伙了,原因也是比较客观的。永涛兄夫妻俩添了宝宝,最早退出伙食团;紧接着是老项的弟弟朝发来到柯村做工,随哥哥住在了一起;茶假之后,老孙也从西武将小儿接来学校一同生活。就这样,柯村小学的“伙食团”便不疾而终,小厨房的锅灶也由大家轮流使用,这里终日充满了烟火气,我自然是最后一个轮到,最后一个就餐。一则我年龄最小,二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山上的小学,从操场左侧下山,不出百余步便是柯村公社。公社有食堂,通过公社徐开副主任(曾与继父同事,1976年后担任书记)同意,允许我搭伙,算是彻底解决了我“一日三餐”的难题,同时也基本结束了“派菜”的活儿。在公社食堂搭伙,不管饭菜质量如何,最大的好处就是时间宽裕了,人事熟络了,道听途说之事儿也随之更加丰富了。尤其是冬日清晨,端着两分钱热粥,拨上一些小咸菜,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公社大门前,在暖阳拂煦下吃着早饭,听着广播,交流着东西见闻,谈论着远近热事。这自然成了干群们的每天一聚,同时我也更多地知晓了柯村的过往今来,尤其是四十年前发生在这一带的“暴动”之事,以及一些民间流传细节。
柯村历来为池州、徽州两府交界之地,既兼有池阳遗风,又顾及徽州古韵,两地千年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使得柯村一带的文化特征很有特色。比如,这里的不少村落都是以姓氏命名,如李家屋、胡家门、孙村、叶家田、余家畈、吕家坞、方家坦、杨家湾,还有罗家、刘家、章家、夏家、程家、郑家等,柯村、竹柯村也是如此,这些都是聚族而居的村落。据《柯村宗谱》载:柯姓,源于黄帝后裔仲雍之五代孙吴王相,仕周为大夫,与周成王会诸侯于柯山,遂依山为姓。传至柯相之下第四世孙柯卢,袭封吴伯,为纪念曾祖父柯相会诸侯于柯山,故尊柯相为得姓始祖,受郡望济阳,史称该脉为柯氏正宗。延至唐朝,有尚书柯颖、学士柯九思;再延至北宋,有柯仲常任潭州(今长沙)通判,为江南柯氏一世祖。靖康之乱,仲常裔孙为避战祸而四处迁徙,其五世孙柯艺、柯英“由徽郡祁门迁徙池阳贵邑塘溪之胜地,续后各从其志,意卜其居址之,可迁者而迁之”。柯艺之子柯和,爱九华山之秀,遂居青阳东南天宝之乡乌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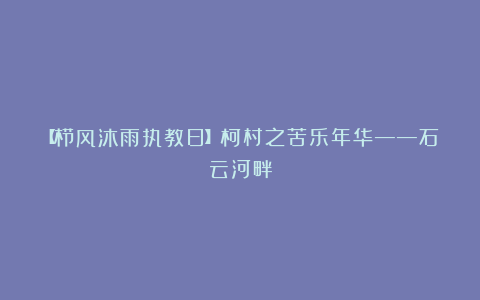
延至大明,柯和裔孙柯祯祥十一世孙柯忠良,从池阳迁居今柯村之地杨树陇落脚,拓荒造田,安宅建村,名曰柯村,故柯忠良为当地柯氏始迁祖。明清之交,柯村已发展至颇有规模,沿着石云河,以“柯村宗祠”中心,分为柯上、柯下和上、中、下三屋弄。在柯村对面的竹柯村,比柯村稍晚一些,但也分为上边屋、中间屋、下边屋三部分。清初,石云河两岸的柯姓人口已达70余户、700多人,建有房屋80多间,这在几个县交界的群山之间,也还是颇具规模的。村落之间修建有石板路、石河塝、石墩桥,村落水口兴建了关帝庙、土地庙、水磨坊,村落之中还建有多座宗族祠堂,如今保存较好的仅有柯村的“敦仁堂”和竹柯的“崇德堂”了。
我在柯村六年,接触最多的柯村祠堂还是竹柯里的“崇德堂”。竹柯也是村,与柯村隔着石云河,面面相对。柯村是面临石云河,房屋建筑一字排开,竹柯村却是背倚虎形山,房屋建筑亦是一字排开。“崇德堂”是一座建于明清时期的柯姓支祠,位于村落中心位置,我到柯村的时候,“崇德堂”正是柯村粮站。每月我们都要来到这里,凭一本“供应证”购买到每斤9分6的大米。虽然“崇德堂”已经改做了“柯村粮站”,但祠堂的规制还基本保留原貌,窄窄的、长长的,虽不及山外三六九都的祠堂宽大敞亮,但在偏僻的深山区,也还算得上是气势磅礴的了。上世纪80年代,柯村粮站迁移至茅山岭北麓公路旁的新址,“崇德堂”一都废弃而造成了部分坍塌。2013年,作为历史文物而重修,如今基本恢复原貌,成为申报“传统村落”的鼎力之作。
柯村的“敦仁堂”同竹柯“崇德堂”一样,它也建在整个村落的中央。“敦仁堂”是柯姓宗祠,它的建筑规模自然要大于对面村的“崇德堂”。“柯氏宗祠”是一座三间三进式的建筑,因地就势,倚山面水。祠堂大门外的厅坦临河,宽阔平整,祠堂内厅堂宽敞明亮。因为是倚山,整幢建筑进进往上,给人以步步登高之感。在柯村的一年,除了柯村“农中”、公社卫生院,柯村文化站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当年的文化站就设在“柯氏宗祠”内。站长汪建松,是当地翠林人,刚从美溪高中毕业没几年,有热情,有水平,我们是在公社门口吃早饭时认识并且熟络起来。接着我便参与建松领衔的资料收集、祠堂布展,还为文艺汇演参与了好几个大队的小剧本创作或审编,足足忙了一个冬季。
那一年的纪念“柯村暴动”四十周年活动,没多大阵势,在“柯村宗祠”开了一个座谈会,办了一个图片展,添了几个玻璃柜,最后一进寝堂上方的板壁,还挂上一幅巨幅油画。年轻英俊的方志敏身披蓝色军大衣站在桌前英气勃发,神采奕奕,他一手叉腰,一手用力挥动着,正在大声演讲,身后是一面鲜红的镰刀斧头军旗,在汽油灯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经过这一番捯饬,祠堂似乎恢复了一些四十年前的气氛。“柯村宗祠”规模说不上大,但当年“柯村暴动”成功后所成立的皖南苏维埃政府、皖南苏区江边特区革命委员会就设在这里,而且方志敏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柯村休整时,还曾在祠堂前召开过群众大会,并在这里建立了红军皖南独立团。
“柯村宗祠”由此远近闻名,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祠堂就被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也能够避免往后的人为毁坏而能够完整地留存下来,使得如今的“敦睦堂”几乎仍属于原生态。以往有关资料都是介绍“柯氏宗祠”是建于清代中期,2010年我随县方志办徐金鑫主任到柯村调研,收集修志资料,在“柯氏宗祠”大门外的抱鼓石下后侧,人们常不经意的地方,却发现了雕刻有“清顺治己丑六年仲秋之吉,景公建立”字样。顺治己丑年,就是公元1649年,这一下就将清代中期改成了清代前期,将“柯村宗祠”的历史向前整整推进了百余年,这也算为柯氏宗祠的历史作了些许填补
这是一个冬日清晨的早餐聚会,公社教干洪庆发端碗来到我面前,告知公社决定明年在宝溪创办初中班,伍书记(公社副书记伍良,分管教育)有意向调我过去任教,这算是征求我意见了。一顿早饭的时间,就决定了我又要挪动,这时我在柯村山上刚刚呆满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