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童年的老房子到旧金山的家;从少女时代“小花”剧组到《末代皇帝》《太阳照常升起》的银幕背后;从祖辈的往事到父母、哥哥三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猫鱼》是当代不可多得的回忆录,是知识人的心灵史,电影艺术家的传记,也是一部当代女性的成长之书、勇气之书。
陈冲,1961年生于上海。演员、电影导演、作家。主演电影《青春》《小花》《末代皇帝》《红玫瑰白玫瑰》《误杀》《大班》《意》等,执导电影《天浴》《英格力士》《世间有她》《纽约的秋天》等。
我梳理了一下陈冲家族有关的人,书没看完,只能先整这么多,看起来可能有些乏味。但看书就不一样了,陈冲文字的海洋,让这一个个人物活了起来,岁月的歌,缓缓流淌。
父亲陈星荣,1931年7月出生于重庆,放射学专家,中共党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爷爷陈文镜(1903年-1987年),四川永川松溉(今属重庆)人,外科专家。1925年因五卅惨案引发的学潮导致湘雅医学院停办,1929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院进修外科。历任武昌同仁医院、重庆宽仁医院外科主任,上海第四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1953年起任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外科主任。九三学社成员,1951年参加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1926年随兄陈文贵加入叶挺独立团任军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
外婆史伊凡(1908年-1989年),生于江苏溧阳,知名社会学家,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张昌绍夫人。出版有《为中国药理学奠基的人——张昌绍的一生》《回忆救护队生活》《吃的科学》;译著《苏联区级医务人员手册》等。参与过北伐、抗日战争。
外公张昌绍(1906年-1967年),男,药理学家,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出生于嘉定县望仙桥镇。1934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并留校任教;193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194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张昌绍是中药研究抗疟药的先驱,1946年和1948年分别在《科学》和《自然》报道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对后来青蒿素的科学研究有重要影响;指导他的研究生邹冈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工作——— 脑内吗啡作用部位的发现等。1967年12月20日,张昌绍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迫害、自杀,逝世于上海。
外公的学生邹冈(1932年-1999年),出生于江苏苏州,神经药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外婆的父亲史蛰夫,国学泰斗,光绪年间廪生,曾参加辛亥革命,为维新人物。曾在常州中学、南菁中学、无锡高等师范任国文教师和历史教师。在篆刻上有极深的造诣。
外婆史伊凡的好友有徐志摩、沈从文、丁玲,和吴健雄是同学。
外婆同学吴健雄,吴健雄(1912年—1997年),女,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太仓浏河镇(一说出生于中国上海市),原籍江苏太仓。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健雄长期从事实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开发了用于分离铀同位素U−235和U−238的关键技术,这项技术至今仍被视为机密,她是首位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女性科学家,成为美国物理学会历史上首位女性会长,与爱因斯坦、费米和费曼等著名物理学家齐名。曾获得富兰克林学社魏德瑞尔奖章、美国国家科学奖章、普平纪念奖章等荣誉奖项。
陈冲哥哥是陈川,中国旅美华人画家,1982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师从孟光、陈逸飞等画家。其代表作《王青肖像》被导演奥利弗·斯通收藏,《Ona和女儿Lisa》以人物情感刻画著称。
陈冲妈妈张安中,张安中(1933年-2021年),籍贯江苏溧阳,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长女,复旦大学神经药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并留校任教,主要从事神经递质、内啡肽及针刺镇痛机制研究,获1980年、1990年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等奖和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张安中1951年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1979年起赴纽约Sloan Kettering研究所等单位研修神经药理学。1992年回国后参与筹建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任副主任,兼任针麻原理研究所副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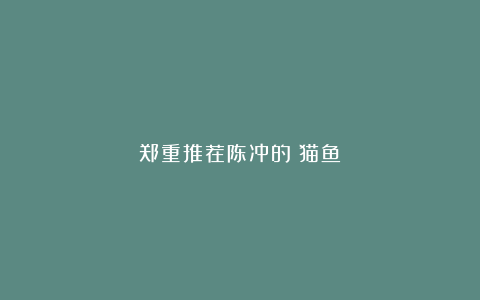
张安中学生饶毅,男,1962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生物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IDG麦戈文脑研究院创始所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创始主任、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名誉主任、西湖大学创校校董会成员。
张安中学生晏义平,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其博士论文《谷氨酸载体在脑缺血及针刺抗脑缺血中的作用》(1999年)荣获全国百优博士论文,这一奖项标志着中国博士研究生学术成果的最高荣誉之一。
张安中学生夏萤,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市针灸机制与穴位功能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2020年荣获首届Sheikh Zayed国际传统医学奖针刺研究金质奖章。
张安中学生孙凤艳,女,1987年获上海医科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1985-1986年任日本东京理科大学药理教研室客座研究员,1990-1994年任美国乔治城大学飞蒂亚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国际福格蒂研究员及访问研究员,1976年起在上海医科大学任教。
看到书中一些原文记载,还是令人极其唏嘘和敬佩的,比如她姥姥去重庆的事情。
一九四二年,在日军从缅甸进攻中国大后方的危急时刻,姥姥又被借调到滇缅铁路督办公署卫生处,在美国援华抗疟委员会工作,工作所在地为弥渡。一九四三年她才从弥渡回到歌乐山,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在歌乐山,姥姥和外公终于安定下来,便决定去上海接女儿们到后方一起生活。姥姥出发之前先寄信到上海,在亲戚家寄宿的母亲和二姨接到信后就开始期待。大人们叮嘱她们,只能跟人家说姥姥是从南京过来的,千万别说重庆。姥姥到沪以后,把我母亲接回到自己的父母家,把二姨仍旧留在我外公的弟弟家。过了数日,姥姥到外公的弟弟家来,却不是来接二姨,而是来跟她告别的。她跟二姨解释说,闯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太困难了,回沪路上花了一个多月,她实在无力带两个孩子上路,只能带母亲一个人。
在二姨的记忆里,那是她第二次被姥姥遗弃。第一次是她三岁时姥姥去英国,把她交给了亲戚。二姨在回忆录里描写了她那天的感受:“在一个昏暗的屋子里,我睡在一只笼子般的小床里,周围一圈都是我从没见过的、可怕的脸,我手里捏着一只纸袋,这是我母亲最后交到我手里的,据说里面是几块蛋糕。这个小床和这个纸袋成了我唯一的世界,我紧闭双眼,不哭不哼,据说就这样待了三天。”
五年后从重庆回到上海,姥姥又一次弃二姨而去,还带走了她的姐姐。那时二姨留着两根硬得像棍子的长辫子,姥姥说喜欢。临走拍拍她的头,叮嘱她好好留着辫子。待姥姥一走,二姨就抓起针线盒里的剪刀,把辫子剪掉。
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上学的时候,借了一本《简·爱》的英文版,带回家读。我那时的英文水平读原文书十分吃力,记得姥姥经常在边上帮我一起查字典,给我解释字典不能回答的疑问。书里有一段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并激起我对远方和未知的向往。
我爬上三道楼梯,推开顶楼的活动天窗,来到铅皮屋顶,极目远望与世隔绝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线。随后,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我曾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气勃勃的城镇和地区。随后我渴望掌握比现在更多的实际经验,接触比现在范围内更多与我意气相投的人,熟悉更多类型的个性……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的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
我完全可以想象二十岁的姥姥在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读《简·爱》的样子。她一定也向往去发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证实自己,并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姥姥是个失败的母亲,但她无疑爱自己的孩子。她一直保存着我母亲六岁的时候,给她往英国写的信。那一小条发黄的纸对姥姥的价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每次我母亲提及童年被遗弃的事,姥姥脸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哪个选择没有代价,抑或一切皆命中注定,根本没有选择。
我自己的女儿十三岁那年跳级考上了全美最顶尖的高中住读,比同班同学都年幼一些。入校后不久她得了厌食症,在治疗过程中,心理医生跟我提到女儿年幼时我外出工作给她带来的心理阴影,专业术语为“分离焦虑”。女儿的病根源在我。我无力地为自己辩解,我只是偶尔离开,一般都在两周内回家,最长不过一个半月左右。医生说,对一个孩子来说几天可能就意味着抛弃,而每次被抛弃,她都以为是永远。孩子们不记得你平日的付出,因为那是理所应当的,而她们记得你的离开所带来的痛苦。也许我遗传了姥姥灵魂深处的不安分,无意中总是在伤害我最爱的人,而那份痛心疾首的后悔,也是我必须承担的命运。
我给母亲打电话,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跟姥姥从上海到重庆的经历,她先说记不太清了,然后叹口气说,一路上很艰难,我们坐了火车、汽车、牛车、木船,绕了很多地方。当时从日占区去重庆是不允许的,姥姥在各个关口需要通行证,需要交通工具,只好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帮忙。那些都不是好人,他们占姥姥便宜。我问,怎么占她便宜?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她要陪他们睡觉。我哑口无言,完全没有想到母亲会跟我这样说。我再追问细节时,母亲不愿说了。但她强调说,要是换你外公去上海接我,一定到不了重庆的。姥姥胆子大,也会随机应变,她总是把我的一只小皮球放在箱子的最上面。到关口打开检查的时候,皮球会滚出来,我就跑去捡,这样检查的士兵注意力就分散了,好心一点的士兵还帮着捡,这样就不会留心到箱子里藏着违禁品或贵重物品。
放下电话后我想,这些占姥姥便宜的都是些什么人?在一两个月的路途上,又有多少个“他们”?这“陪他们睡觉”的交易是怎样达成的,又去哪里实现?这些我都永远无法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