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阿甘本《皮诺曹》
译:蓝江
真相并非一成不变的公理:它随着生命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甚至变得越来越繁琐和难以应对,尤其是对于那些毫无保留地信奉它的人来说——这恰如皮诺曹的鼻子。
如果从木偶的种种遭遇来判断,科洛迪更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非共济会成员。猫与狐狸——或许这就是它们被大写的原因——是统治我们的权力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残暴的暴力与欺诈,警察的警棍与国家元首及议会成员的仪式性诡计。“简单的残暴”与“讽刺性的残酷”,“杀手的灵魂”与“语言的迷宫”,正如评注者所说的那样(Manganelli 2002: 107)。而人类城市的寓言便是“教育性与幻觉性”的“捕愚者之城”(107),一种“反乌托邦”(108),两位恶棍在此引领皮诺曹,其唯一目的便是让皮诺曹经历“最具教育意义的旅游绕道”(107),而皮诺曹却未能看到:一侧是饥饿得打哈欠的瘦弱狗群、因寒冷颤抖的被剥毛的羔羊、失去鸡冠和肉垂的家禽、卖掉翅膀的蝴蝶,另一侧则是“在这群穷苦乞丐和穷人中间”,载着狐狸和猛禽的豪华马车。奇迹之场,科洛迪对此只字未提,仅说那里“是一片孤零零的田野,看起来和其他田野没什么两样”(第十八章),它就在城墙外,这正是个欺骗和诈骗的地方,愚蠢和贫穷的人被狡猾和富有的人剥夺了他们稀少的财物。就在那里,其中一个穷人挖了一个洞,把四枚金币放进去,然后用一点泥土覆盖坟墓,再用鞋从池塘里舀水洒在上面。
二十分钟之后,当皮诺曹从城里回来,准备收获他的劳动成果时,让他明白自己“缺乏盐分”并被“更狡猾的人”所骗的,又是一只动物,这次不是昆虫,而是一只鹦鹉,它嘲笑那些愚蠢的猫头鹰(尽管是比喻意义上的动物,一种夜行性鸟类),认为“钱可以像播种豆子和南瓜一样在田野里播种和收割”。鹦鹉的警告使他陷入了最悲惨的激情之中,这是他此前从未经历过的:绝望,这种激情——根据一种奇特的中古世纪词源学——缺乏双脚(拉丁语pedes)来行走于善的道路。正是绝望促使皮诺曹做出最严重的错误决定:诉诸“捕愚者法庭”,“控告那两个抢劫他的歹徒”。随后展开的逆向法律程序或许是无政府主义者科洛迪最颠覆性的发明。法官,这位“因年迈、白胡子和尤其因那副金边无镜片眼镜而受人尊敬的年迈大猩猩”(他因多年眼疾不得不一直佩戴这副眼镜),是人类法庭中那盲目如命运的正义的激烈隐喻。在耐心倾听木偶遭受“不义欺诈”的悲惨遭遇后,法官竟将他交给宪兵——“两只穿着宪兵制服的猛犬”——并说道:“这可怜的家伙被抢走了四枚金币;因此,抓住他,立即将他投入监狱!”(第十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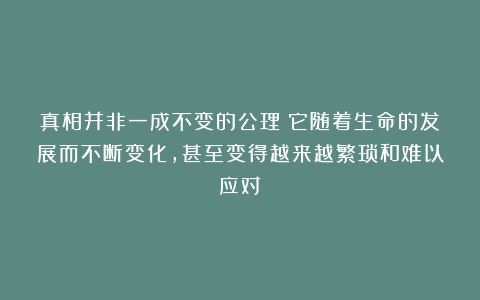
关于皮诺曹在监狱中度过的四个“非常漫长”的月份——或许比木偶在其他所有冒险中度过的时间更长——我们一无所知,除了它们以一种在现实世界中常见的方式结束:愚人皇帝宣布大赦,伴随着“盛大的公众庆典、灯光秀、烟花表演、马术和自行车比赛”(第十九章),以庆祝对敌人的伟大胜利。卡奇福尔斯不属于皮诺曹的童话故事:它是童话中插入的讽刺插曲,一面倒置的镜子,反映出人类城市的真实形象。因此,在这四个漫长的月份里——也可能是四年——皮诺曹似乎既没有生活过,也没有停止生活。
从监狱获释后,皮诺曹如猎犬般飞奔向仙女的茅屋。或许正是那种曾使他入狱的绝望,让他如今开始思念父亲,并抛弃了自己那森林般的童话天性,开始自责:“难道还有比我更忘恩负义、冷酷无情的孩子吗?”(第二十章)
此时阻挡他去路的绿色蛇,是他自我诽谤的双重幻象(“忘恩负义”我尚可容忍,但自称“男孩”实在过分)。正是这头“眼睛如火、尾巴尖锐如烟囱般冒烟”的爬行动物,揭示了对这部作品的玄学解读之粗疏。这只绿蛇不过是引用了同名童话中的绿蛇,而这位最反皮诺曹式的作家、国务顾问歌德,将其插入到他的著作《德国流亡者的对话录》(Unterhaltungen deutscher Ausgewanderten)中(Zolla 1992: 431ff.)。
剥夺这一比较的任何依据的,是注释者所说的一个重要事实:歌德的蛇是一座(共济会)桥梁,横跨河流以供通行,而科洛迪的蛇则是一个障碍,木偶请求它“稍微让开一点,让[他]通过”。正是这种徒劳地试图绕过障碍物的努力,导致木偶绊倒,重重摔倒后,双腿朝天地陷进泥里。木偶倒挂着踢腿的景象——或者说“鼻子朝下”?——让蛇笑得直不起腰(“笑啊笑啊笑,他笑得最后因笑得太厉害,胸口的一根血管爆裂了”;第二十章),表明只有恢复自己的喜剧天性,皮诺曹才能摆脱折磨自己的幻觉。
然而,这种解放只是短暂的,因为自我诽谤和内疚感又以会说话的蟋蟀的表亲或姐夫——一只萤火虫——的形式重新出现,它指责皮诺曹意图(而非实际尝试)偷走田野里看到的两串麝香葡萄。正是出于这个无辜而饥饿的愿望,皮诺曹落入了农民们设下的陷阱,目的是“捕捉那些偷鸡的肥胖松鼠,它们是附近所有鸡舍的祸害”(第二十章)。
这场冒险始于此处(曼加内利将其描述为“他最晦涩的冒险之一……,其中他存在中的各种道德与幻想主题交织在一起,相互矛盾,形成一种微妙而绝望的纠缠”;2002: 117)是木偶即将遭遇的荒谬变形的预兆:发现他的农夫在他脖子上套上“一条布满黄铜尖刺的厚重项圈”(第二十一章),并用他取代刚去世的狗梅兰普斯,守卫着鼬鼠们威胁的鸡舍。皮诺曹——正如鼬鼠的问候所证明的:“晚上好,梅兰普斯”——在所有实际意义上都成了狗;但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只是假装接受四只鼬鼠向他提出的歪曲协议(“这些鸡中,七只将由我们自己吃掉,一只将送给你,当然,条件是你必须假装睡觉,并且永远不要想到要叫”),当这些小偷认为他们已经确定了事实,皮诺曹真正开始叫起来:“他像一只看门狗一样叫着,声音越来越大,呜呜呜呜。”这种转变为看门狗的行为,并未如皮诺曹让农夫明白的那样(“你需要知道,我虽然是个木偶,身上有各种缺点,但我绝不会为罪犯站岗或帮他们忙!”),是一种意想不到的、不协调的正直。正如“你需要知道”所示,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流浪汉身份的恢复,以及这种身份所暗示的与死者之间的秘密团结——甚至认同。皮诺曹并没有揭露梅兰普斯与鼬鼠之间可耻的协议,而是“想起那只狗已经死了,他心想,’背叛死者有什么意义?死者已死,最好的做法就是让他们安息!”’(第二十二章)
而此刻等待皮诺曹的,正是与一位死去的女孩的邂逅。刚被农夫释放的木偶——正如我们所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浪狂(有人因此将他定义为“一个流浪的木偶”)——立刻以惊人的速度冲向田野,奔向“仙女的茅屋”。然而,他找到的不是小屋,而是一块墓碑,上面用大写字母刻着这些令人心碎的文字:
此处安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