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还需要真实的影像吗?或者说,“真实”要如何被重新定义?
真实,正成为一个动词
作者:朱钰
编辑:张先声
巴斯科姆说:“电影的影像现实,从来就不是有关什么是现实的问题,而是有关什么可以被’接受’为现实的问题。”如今随手可拍的现实世界充斥短视频,虚拟影像对电影制作流程的全面入侵,人们并不期冀在影像中看到现实,而是倾向抓取猎奇和奇观。纪录片的创作也已无法再满足只是拥有现实素材,影像得以成为作品,需要有意识地建构,如何建构,又试图在建构中如何摆放和呈现真实。
NOWNESS今年“天才发现计划”的主展映中设置了“再见真实”单元,选取的五部影片都基于对真实生活和环境的拍摄,在此之上他们大胆呈现了不同的视角和对素材的重构,无论是何种路径,都还是不得不面对,在真实世界被不断模糊的当下,我们试图通过影像表达什么,触及什么?
重构过往的真实再现
巴赞在《完整电影的神话》中说:“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的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人有保存生命的本能,有留存过往的欲望,而影像以无限接近现实的样貌进行着再现的尝试。李扬在《家庭影像》中记录一同玩滑板的朋友们,那段一起租房生活的日子被他称为“家庭影像”,因共同热爱而相聚,因残酷现实而分开,而呈现出来的部分像是生活中高光时刻的集锦,鲜活、碰撞、嬉闹,那确实是被纪录下的真实发生的生活,但一定是提炼和筛选之后的,展现出一种强烈的对青春的赞美和留恋,正因为那段时光成为过往,影像也留存下回望时赋予的无限美好,而这种美好的真实,是以导演的目光重新建构的。
同样试图留存过往的罗正凯,选择了再现的搬演方法,他在美国留学期间认识了一位街头卖报黑人哈尔·罗林斯,一年后他产生了想将两人相识过程重现的想法,于是他撰写台词和分镜,排练并实景拍摄,即便哈尔尽力配合,也时常分不清表演和真实的界限,场面一度崩溃,一次次从表演中跳脱出来,真实在建构和失控中展现出多重面貌。
在试图再现过去的努力中,是一场无力的表演,而摄影机对哈尔的侵入以及哈尔对他的依赖和信任,让罗正凯一度陷入道德的自责。在这场双重嵌套的拍摄下,在试图重现过去的努力中,一步步退居幕后,真实好像反而被一层层瓦解——过往无法被还原,真实似乎只存在于当下,是在场的发生。
《家庭影像》剧照
多媒介融合的“幽灵”再现
德里达用“幽灵”描述一种 “非在场,同时又非缺席”的悖论性存在,如果说试图留存和再现的过往是影像中难以再现的幽灵,那么在《如何在曼谷做一只鬼》中,导演直接构建了幽灵身份的存在,虽然是现实纪录的素材,但融合了桌面电影和旁白的叙事建构,成为了一部做鬼指南,“ghosting”在互联网时代,指人际关系中,一方突然且毫无解释地终止所有联系和沟通,数字时代的消失,无从寻找的痕迹,成为了数字幽灵。
导演戏虐式地以十个步骤讲解做鬼方法,模拟鬼的视角,甚至和ChatGPT生成了鬼的语言,试图也体验一种“非人类存在”的可能,不建立人际关系,不承担情感责任,只是游荡且随时隐匿,在这层叙事的重新建构后,原本只是在曼谷街头纪录的影像素材,被赋予另一层意义。
《来自太阳的光》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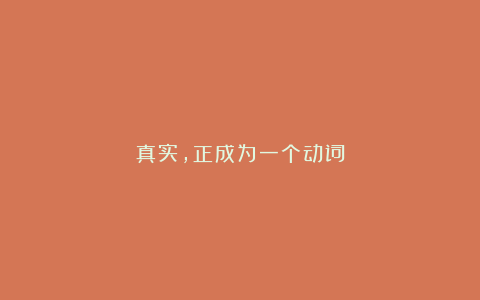
同样对纪实素材进行再构建的《来自太阳的光》,导演拍下中国西北地区被阳光照射的建筑墙体,不同质感和材质的墙,留下了中国过去半世纪进程中不同年代的痕迹,有年久失修的土坯墙,也有七八十年代国营瓷器厂的红砖墙面,时间凝结在墙面,以物质的记忆而存在。
导演将其作为叙事的幕布,真正的主角是在上面涂画的人物和时不时飞过的鸟,海子的诗以大字涂鸦的形式被直接投映在墙体,似乎融为一体,成为对那个年代逝去的文本注脚。这些是创作者的直接在场,同时它也打破了实拍与动画,客观与主观的界限,呈现出消解二元对立后人类叙事。
对现实素材注入作者视角,进行叙事的二重构建,呈现出当下纪实影像多媒介融合的创作路径,作者们不再满足只是将现实完整地纪录下来,在现实素材中寻找叙事,而是以主观的视角赋予新的架构,甚至是在对抗“记录现实”的权威,强力灌输自我的在场,这是否是对真实的破坏或重新建构?
《来自太阳的光》导演马海蛟,荣誉嘉宾:动画艺术家黄炳(左),演员梁靖康(右)
去人类中心化的真实行动
在逐步消解二元对立和去中心化的构建下,当代影像已经越来越呈现出“非人类中心化”的趋势,在《地衣》中,王裕言将叙事主体聚焦在人造风景上,从石油如何被转化为塑料,塑料又如何生产人造花的过程中,试图揭示了自然与人工之间复杂的关系,人工的努力在于用自然材料去替代自然景观,镜头近距离跟随石油缓慢而流动,同时巨大人手的呈现,将人类的干预放大,这种完全丢弃人类中心视角的呈现,生长出了陌生而怪异的视觉体验。
同时,作者也几乎放弃了纪实拍摄的工作,而是将“现场”放到了虚拟的公共图像空间,在重新排列、拼接、组合拾来影像的过程中,抵达直接拍摄所没法表达的真实,她直言:“没有任何影像能捕捉完整的现实,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那些转瞬即逝的片段,邀请观者在其中游走、体会、补全。”在浩荡的影像幽灵中,去进行挖掘、回收和重组,不再是为人类审美而存在,而是各种技术视觉系统的集合,我们也跟随着人造花的制作,进入到一个不曾观看的非人类视角的世界,去看到人类对其进行的操控,是极具挑战性的观影。
《地衣》剧照
《如何在曼谷做一只鬼》《来自太阳的光》也都摆脱了传统的观影经验,将电影对“完整世界”的建构转变为可操作、可注释的数据和界面,且消解了人类的视角,我们也像一只游荡的鬼魂,或者跟随石油的流动和锻造,感受物质世界的弥散。利奥塔说:“艺术的任务在于成为不可呈现之物的见证…意在让人看见有不可见、不可图形化之物存在,并且它抵抗一切掌控。”当代的影像碎片,已无法承载宏大的主观叙事,而更多是一些无法被叙事整合的瞬间,成为不可言说的幽灵,真实也不再是等着被镜头“记录”下来的客观现实,而是不断被技术、媒介、物质和记忆共同构成的、幽灵般多维度的呈现。
或许,当下的真实不再是名词或形容词,而是以动词存在,是需要观众也参与其中的,不断建构的过程,观众已不满足于只观看作为“现实的渐近线”的等待被揭示的现实,而是要探寻“不可呈现的真实”,解放“人类中心”的视角,不再是旁观式的记录,而是让真实去发生这个行为本身。
凹凸镜DOC
ID:pjw-documentary
微博|豆瓣|知乎:@凹凸镜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