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初唐重臣、浙江第一位“状元”,贺知章极富文采,而且诗书双绝,可惜他的诗名掩盖了书名,在李白看来,他的水平能与王羲之并列:“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宋代施宿则认为其草书水平不仅超过孙过庭,甚至超过了初代“草圣”张芝、索靖:“凡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索不如也。好事者供其笺翰,共传宝之。”
学界认为,贺知章的草书用笔丰富精谨、千变万化,与孙过庭的“千纸一类,一字万同”“闾阎之气”迥然不同;而其草融合草隶、章草、行草笔意,继承魏晋六朝诸家笔法,论古意与境界,也非“宋四家”可比。
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的《孝经》,是其唯一存世的书法,此作全卷纵26厘米、横265.1厘米,总计100余行、2000余字,字径大小约2厘米,于明末清初流入日本,被岛国皇室世代珍藏,仅在2006年首次回国展出过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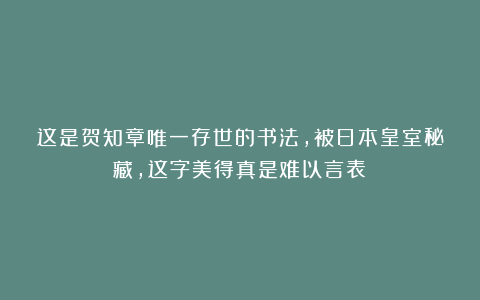
窦蒙在《述书赋》注中写道:“贺内监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惟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贺知章草书将法度与意趣融合,心手合一,达到了“书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
这部《孝经》非常适合初学草书者临摹。起笔多露锋直入,如“孝”字入笔似蜻蜓点水,轻快爽利又不失稳健,行笔时中锋绞转,收笔或急停或轻提,提按之间见八面出锋的自由。方折与圆转自然切换,刚柔相济而不显突兀。
结字上,贺知章善用欹侧造势与简省求变,以重心偏移形成张力,“親”字省略中部笔画,仅以两笔牵丝连贯,中宫留白,四周笔画舒展,尽显密处紧实、疏处空灵的安排,这种处理既合草法规范,又因随势赋形,避免了程式化弊端。
《孝经》开篇浓墨饱满,显庄重肃穆,中段因连续书写出现枯笔飞白,却笔断意连,末款又润笔书写,形成浓枯润的情感节奏。清代吴德旋言:“贺监草书,非徒狂放,乃礼法中见性情”,每笔皆有来历,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典范。
此作的价值在于:笔法上,示范了二王正统的写法;结字上,揭示如简省笔画而不失辨识度;墨法上,展现浓枯对应。临习此作,不仅能掌握草书核心技法,还能医治草书的“燥气”,避免陷入“江湖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