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有关伦理学的论述者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认为伦理学只需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伦理也牵涉到人以何种态度面对世界和他周遭的所有生命。当认定植物和动物这些生命也跟人的生命同样神圣,并愿意帮助处于困境的生命时,人的行为才是符合伦理的;也只有这种超越种族界限、将道德责任扩及一切生命的普遍性伦理,才能够在人类思想中深植下去。人类彼此如何相待的伦理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只是普遍性伦理中的一个特殊产物。”
将伦理学讨论的范畴超越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涵盖到所有的生命形式,这让史怀哲的伦理学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康德在内的主流伦理学哲学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果要敬畏所有的生命,打死一只蚊子或蟑螂,食用各种肉食,踩死一只蚂蚁,清理一片树丛⋯⋯似乎都有悖于上述理念。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点类似于我们要如何看待电车难题、洞穴奇案之类的思想实验或者如果我们身处奥斯维辛又当如何。显露出两难的思想实验仿佛无解,一则我们不会碰到,二则既然都是错,就没有讨论的意义。奥斯维辛的问题就像那些幸存者的自我谴责一样,因为好像只有将活着置于伦理之上的人才可能活下来,在那种极端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不敢保证自己不是那个想要首先活下来的人。
讨论思想实验和奥斯维辛的价值,并不在于好像颁布了一个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好像在奥斯维辛那里活下来就是人性的耻辱;它的价值在于,我们只有更多地思考极端环境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寻常问题,也才能在某种极端或两难出现的时候,不至于惊慌失措,无所适从。
史怀哲的伦理学在上述意义上也不应当被我们僵化地理解。
首先,史怀哲强调的是生命的神圣与平等。“对于真正具有伦理观的人来说,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类立场来看似乎相对低等的生命。只在情况紧急或形势所迫时,他才会不得不加以区别。例如,陷入必须决定是否该牺牲某个生命以保全另一个生命的处境。在针对个别情况做决定时,他会知道自已是主观的、武断的,对被牺牲的生命也应负有责任。”
其次,他的目标仍是着力于解决人类“生存意志自我分裂”的问题,这一问题表现为“以牺牲他人的存在成全自己的存在,用一个存在摧毁另一个存在”。“只有开始思考生命的人,才会在自己的生存意志之外意识到他人生存意志的存在,愿意与其休戚与共,携手进退。但是人却无法完全这么做,因为面对令人费解且残酷的法则时,人有时会不得不以牺牲他人的生命为代价才能活下去,并且在摧毁与伤害他人生命的过程中,罪孽也会越来越重。幸而身为道德动物,人会竭尽所能地奋力挣脱这种制约;自觉且慈悲的人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遏止这种生存意志自我分裂的悲剧。人渴望能展现人道主义精神,协助他人从痛苦中解脱。”
“因此,’敬畏生命’的伦理涵盖了所有能称之为爱、奉献、同甘共苦与齐心协力之类的价值。”
“思考生命者心中’敬畏生命’的概念,包含了伦理学与肯定世界和生命的理念,这二者是紧密相关的。’敬畏生命’的目的是创造价值,真正实现个体与人类全体在物质、精神及伦理等方面的进步。当代缺乏思想性的肯定世界和生命的理念,有知识、技能与权力之间踉跄而行;而开始思考生命的人则将追求精神与伦理上的完善作为最高理想,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其他方面的进步发挥真正的价值。⋯⋯于是我们不再被那种愚昧狂妄的文明所掌控,并敢于正视这个事实——知识与技能的进步对真正的文明发展不仅没有助益,反而使其更加困难。精神与物质进步过程中的关系,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所有人都要与自己身处的环境对抗,也必须关注如何扭转这场几乎毫无希望,且让许多人陷入不利处境的战局,使文明再度辉煌。”
史怀哲总结说:“有两种体验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阴影:一是领悟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神秘莫测且充满痛苦,二是认识到自己出生在一个人类精神文明衰颓的时代。然而,经由思考’敬畏生命’这个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伦理观,我克服了这些阴影所带来的问题。在这个理念中,我找到了人生的依靠和方向。因此,我希望这个伦理观也能帮助他人深入思考且变得更好,使他们内在精神变得更丰富,这是我对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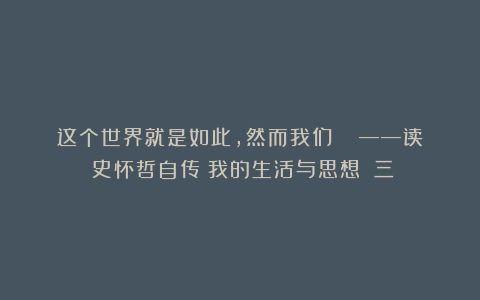
时代所暴露的诸多恶果都源于我们对思考能力的蔑视和不信任感。人们难免会质疑,“自己是否真能通过思考来回答有关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与世界之关系的问题,是否真能通过某种方式赋予生命以意义”。不信任感则是因为无论是团体还是政府,他们总希望我们不经思考便被说服,事实已经无数次、并将继续证明:看上去美好的各种说法、制度、理念,不过是试图进一步压榨我们的绞肉机。这个时代“想尽办法贬低和打压个人思想,它对待个人思想的方式,几乎就是福音中’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拿去’这句话的写照”。
“迫使人对自己心智能力信心大减的另一个压力,来自知识的爆炸。人们对新知识应接不暇,无法完全消化和吸收,于是只能把理解不了的内容当作正确的信息囫囵吞下。这种处理知识的态度很容易使他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确实判断力不足。”
知识爆炸的影响在我们这里体现为两种面对人工智能的极化态度:一种是极度的自卑,认为人类最终会沦为人工智能的奴隶;一种是盲目的自负,认为人工智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证据就是它们仍旧会犯很多低级错误,而且离人性的共情或理解还很遥远。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是史怀哲所说的放弃思考的表现,“放弃思考等于宣告精神破产”。在这种情形下,不用等到AI发展到某个阶段,我们就已经沦为自己的奴隶;或者,我们的狂妄会让人类丧失充分利用AI的机会,它可能是人类跨越光年尺度的距离限制,寻找宇宙中另一个家园的机会。
放弃思考必然导向怀疑主义,对事实真相失去知觉,不再渴望知道,游走于各种意见之中。史怀哲坚信,“仅仅通过’敬畏生命’这一思想特质,人们就能胜任对抗怀疑主义的任务,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思想”。“所谓的’根本’,是指这个思想是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生命的意义以及善的本质等根本问题而出发的。它直接与每个人的思维联结,并在我们的思维中得以扩展、更加深刻。”
史怀哲将世界形容为不仅包含了“事件”,也包含了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隐含着赋予人的存在意义的唯一办法,那就是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从物理性提升为精神性,通过顺应天命的态度与世界建立起精神关系。
“真正的顺应天命,是人在屈服于世事的同时,能从形塑他存在之表象的命运中超脱而出,然后得到内心的自由。”这就好像康德道德哲学的延续,我们承认现象界的因果关系,但持守本体界作为“理性的事实”的自由。因此一个人为了某种进步的事业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甚至蔑视流言、诋毁、酷刑或死亡。他不是天真地以为邪恶之力量不会施加暴行,或者暴行不会造成肉体的损伤、精神的折磨;他承认在一个现象的自然界,因果关系无可置疑,不过他更看重同样无可置疑的、存在于本体界的自由、理性或道德(三个可以互相替换的理念)。
“内心的自由,意味着他能找到让自己度过难关的力量,并因此变得更有深度、更内敛,也更成熟、平静且祥和。因此,顺应天命可说是一种对自我存在的精神性与伦理性的肯定。唯有经历过顺应天命的试验者,才有办法对世界持肯定态度。”
“至于积极主动的人,则通过另一种方式与世界建立精神关系:他并不是只为自己而活,而是与周遭所有的生命合而为一;他对他人的命运感同身受,并尽其所能地提供协助,把提升他人生命价值和拯救生命视为他所能分享的最大快乐。”
“一旦人开始思索自己生命的奥秘,以及自己与世间万物的关系,唯一的结果便是:对自己和周遭所有的生命产生敬畏之心,并在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伦理观中身体力行。从各方面来说,他会因此变得比为自己而活更辛苦,但同时他的精神也会更丰富、更美好、更快乐。他的生活将不再只是得过且过,而会变成一种真正的人生体验。”
“敬畏生命”的涵义包含顺应天命、肯定世界和生命、肯定伦理道德。它们是世界观的三个基本元素,彼此密不可分。史怀哲在此基础上的人生观是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混合:在认知上的悲观,但总怀着乐观的意愿与希望。
这其中包含一种可贵的清醒与精神,即无论世界的面目如何,认识它,接受它;在另一个精神的维度则相反,无论世界的面目如何,我都要试图改善它,更新它。正如史怀哲所说:“所有人皆须分担世间之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人生在世,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某种能力,以终止某些苦难。⋯⋯每个人都应该走一条能够救赎他人的人生道路。”
评价: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