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上映的中国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抗战爆发,张忠良因参加抗战救护队离开了上海,妻子李素芬在沦陷区照顾婆婆和儿子抗生。张忠良在重庆结识了王丽珍并与其同居。抗战胜利后,张忠良回到上海,并与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关系密切。因此张忠良分别有了“沦陷夫人”、“抗战夫人”和“胜利夫人”。李素芬因生活贫苦而在何文艳家里做女佣。在何文艳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李素芬认出了丈夫张忠良,并得知了张忠良与王丽珍和何文艳的关系。李素芬将实情告诉了婆婆,婆婆带着李素芬和抗生找到张忠良问罪,但张忠良仍徘徊在王丽珍和何文艳之间,绝望中的李素芬跳入了滚滚江水中。该影片上映之后,连续放映时间长达3个月之久,观影人数达到了70万余,创下了1949年前国产电影的最高上座记录。(经先静:《社会史视野下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电影文学》2011年第4期,第84页。)
“抗战夫人”“沦陷夫人”“胜利夫人”是抗战时及战后人们对男子重婚或婚外同居的对象的戏谑称呼。“抗战夫人”指原有配偶的男子因在战时与妻子分离而另娶的妻子或婚外同居对象。“沦陷夫人”指抗战发生后未随丈夫奔赴抗战前线或后方而留在沦陷区内的妻子。“胜利夫人”指抗战胜利后,原有配偶的男子另娶的妻子或婚外同居对象。
讲述类似故事的还有现当代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的葬礼穆斯林》。在这部小说中,回族琢玉匠人梁亦清将长女梁君璧嫁给了爱徒韩子奇。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子奇担心玉器珍品被毁而随英商赴伦敦。梁冰玉因感情挫折而随姐夫共赴英国。在法西斯国家的疯狂进攻下,英国岌岌可危,在旦夕不保的伦敦,韩子奇与妻妹梁冰玉相爱,并生下了女儿韩新月。战后韩子奇、梁冰玉携女回国,为梁君璧所不容。梁冰玉留下女儿,孤身远赴他乡。(霍达:《的葬礼穆斯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小说《的葬礼穆斯林》虽内容大不相同,但有着非常相似的关键情节——在战争背景下出现的重婚或婚外同居。除此之外,抗战后涌现出一批有关抗战时期“沦陷夫人”和“抗战夫人”的文学作品,中篇小说有张爱玲的《等》、秦瘦鸥的《劫收日记》等,刊登于报刊、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更是不胜枚举。
《劫收日记》1982年版
大量相似主题的文艺作品的出现,反映出抗战引发的社会问题——战争使婚姻家庭关系面临着种种的考验,这些婚姻问题随之引发了战时和战后婚姻纠纷问题。
战争对婚姻状况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在抗战期间,一方面,人口迁移加剧,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域人口的交流,跨籍婚姻开始增多。“北平籍的男孩子与四川籍的女孩子结婚了,上海家庭里的女儿嫁给了广东人,这是很奇怪的姻缘。站在结束时,有一个可爱的广东女郎,丈夫是上海人,丈夫暂时留渝,她则由政府机关送到上海,她说:‘我丈夫给我一封给他母亲的介绍信。我听说她是旧式的人;我们彼此说话都不会懂的——我不会说他的方言’。”([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8页。)另一方面,婚姻关系中出现了“伪组织”。
这一所谓的伪组织,是说许多因故乡沦陷而逃亡的人们,本是结过了婚,但在家庭离散的时候,又有一方独自重行婚姻,或以婚外同居的形式,另成立一个家庭。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有三种情形:第一,是男的方面另行娶妻,成立一个家庭;第二,是女的方面另行嫁人,成立一个家庭;第三,是男女双方都另有婚嫁,各成立一个家庭。不管这三种情形怎么样,总之,在前一次合法成婚的家庭,未经过合法离婚的手续,这几者的发生,都可以叫伪组织。(参见姜蕴刚:《结婚二重奏——家庭“伪组织”之检讨》,《女铎月刊》复刊后第2卷第10—11期合刊,1945年1月。)
抗战爆发后人口迁徙的洪流使得很多家庭支离破碎,妻离子散,而战时婚姻观念的转变也给家庭“伪组织”的出现提供了方便。首先,战时两性结合的手续日趋简便,甚至连形式也不注重,只须在报端刊登一则订婚、结婚或同居的启事,便算人事已尽,较诸集体婚礼,还要简便节约。其次,战时两性的离异非常自由。战时的舆论对于夫妻平等协议的离婚从不非难,甚至对于日趋简单化的离婚手续亦不予以苛责。再次,战时两性的再婚通行无阻。在战前,鳏夫续弦,司空见惯,毫无阻碍;但是寡妇再醮,困难重重,迥非易事,尤其有了子女,阻碍更多。抗战以还,此种片面的苛求,已逐渐失其存在,无论鳏寡,均可再婚,绝对自由,不复引人注意,而招致恶意的批评。(张少微:《战争与家庭改造》,《东方杂志》第43卷第13号,1947年7月,第53—54页。)
在这种战时婚姻家庭道德观的影响下,家庭“伪组织”乃日见增多。男子因原有的妻室不在身边,因而在外另行娶妻者颇多,有的男子有了“沦陷夫人”,又娶“抗战夫人”,再娶“胜利夫人”。(左涌芬:《漫谈妇女和婚姻》,《妇女》第2卷第12期,1948年3月,第5页。)同时贫困阶层的已婚妇女,因为原有的丈夫生死未卜,或天各一方,因而在外另行婚嫁者也很多。(陈盛清:《战后的婚姻问题》,《东方杂志》第37卷第7号,1940年4月,第19页。)当时曾有人指出:“在目前,一切似乎都很自由,很随便,只要有钱有势,只要高兴,便可以东组织一个家,西组织一个家,可以随便捐弃这一个,宠纳那一个,不觉困难也无需顾虑,甚至置妻儿于不顾,视为陌路。舆论不予制裁,法律也往往因无人告发,无从执行;所以更随意所欲,横行无忌。弃妇弃儿,流离孤苦,家庭惨剧,莫此为甚!”(李曼瑰:《转移婚姻的道德观》,《中央日报》1944年5月7日,第5版。)的确,在对方生死不明的情况下,丈夫另娶,妻子别嫁,成为抗战时期屡见不鲜的现象。战后陈白尘的剧作《胜利号》、张恨水的小说《大江东去》以及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都对这时期的家庭“伪组织”问题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大江东去》1946年版
这种“伪组织”有些是正式的婚姻,而更多的是男女双方在报上登载同居启事便宣告结合。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许廷干、吴淑贤在《中央日报》上所刊登的同居启事,云:“廷干原有家室,于廿六年抗战失散陷区,阅今将近两载,音息全无,生死莫卜。奈家有年迈老母及幼稚儿童,一切家务急在需人料理。谨奉慈母之命续娶,于廿八年元月在平都,与旧亲吴女士订婚。原约在本年三月间结婚,值此抗战严重期间,征得双方同意,为免除俗礼,实行节约,在重庆同居。特此登报,敬告亲友。”(《许廷干、吴淑贤同居启事》,《中央日报》1939年4月11日,第1版。)这类同居启事在当时绝非个例。(尚可参见1939年10月15日及1945年3月7日,重庆《中央日报》载陈玉亭、李福英及毛瑞根、谭素梅的同居启事。)根据岑家梧对贵阳《中央日报》1942年10月至1944年3月间刊载婚姻广告的统计,这一时期的同居启事每天都有,最多一天是16条。“战时有了这种同居的关系,战后便发生了所谓‘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的问题了”。(岑家梧:《从婚姻广告观察中国战时婚姻问题》,《社会建设》第1卷第7期,1948年11月,第56页。)这还只是一地一时一家报纸的记录,由此推算,这种“伪组织”在整个大后方不在少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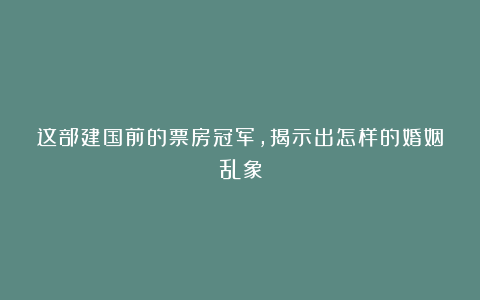
“伪组织”如此频繁的出现,以致于在战后如何处理这种伪组织一度引起热烈讨论,一些人主张承认这种事实婚姻,一些人则坚决反对,主张付诸法律解决。而那些身处“伪组织”的人也为解决这个难题想尽办法。面对“沦陷夫人”和“抗战夫人”,一夫多妻又不可能,于是只有离婚一途。据当时一位律师记载,当时这一类离婚案件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一般来讲,作为丈夫当然愿意与“沦陷夫人”离婚,于是某罗姓女士被丈夫用手枪逼着离婚,某杨姓女士被丈夫用经济手段困顿使其离婚,而一位王太太,更是被丈夫以虐待婆婆的罪名给告上法庭。(濮舜卿:《战后离婚问题的面面观》,《妇女文化》第2卷第3期,1947年5月,第7—8页。关于婚姻伪组织问题,又见潘素:《现阶段的婚姻问题》,《妇女共鸣》第11卷第3期,1942年5月,第3—5页。《抗战夫人问题座谈》,《女声》第3卷第24期,1945年12月。)
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的这种“露水夫妻”重返家园,家庭中就出现了亟待解决的婚姻问题。《一江春水向东流》和《的葬礼穆斯林》等文学作品就反映了“抗战夫人”、“沦陷夫人”与丈夫之间的婚姻纠葛。
战后最为著名的“抗战夫人”案件就是萨本驹重婚案。萨本驹,33岁,福州人,海军上将萨镇冰的族孙。电气专科毕业,战前从商,曾创办胜利商行。抗战开始后从事地下工作,曾任青浦县长,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萨被释放后,于浙江任中美英同盟军东南情报部顾问。其妻陈季政与萨本驹育有一子一女,居于昆明。史璧人为萨本驹所在情报部的译电员。史办事勤奋,深受萨的赏识,二人逐渐由同事发展到同居关系,并育有一女。
《萨本驹双订鸳鸯起裂痕——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对簿公庭》,《社会画报》第4—5期
1946年,萨本驹、史璧人被萨本驹原配夫人陈季政控告重婚罪。(静江:《萨本驹双订鸳鸯起裂痕——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对簿公庭》,《社会画报》第4—5期,1946年10月,第20页。)此案在社会上引起了有关“抗战夫人”和“沦陷夫人”的热议。1946年12月,该案一审判决萨本驹和史璧人各处有期徒刑四个月,缓刑两年,如易科罚金,则以500元折算一日。二审撤销了易科罚金,维持两年缓刑。如果通奸行为再次发生,将直接执行一审判决中所判的四个月刑期。(《“抗战夫人”高院定案》,《申报》1946年12月8日,第2张第6版。)但萨本驹、“沦陷夫人”、“抗战夫人”三人之间的纠纷并没有结束,1947年8月,陈季政以继续“通奸”为由,报警将萨、史二人抓捕。最终,于当年的8月19日,双方的代理律师正式对此事进行谈判,结果决定由萨氏给陈季政生活津贴三亿元,正式宣告离异婚。(《萨本驹慷慨解囊 恩怨悲欢一笔勾》,《申报》1947年8月20日,第1张第4版。)
《萨本驹慷慨解囊 恩怨悲欢一笔勾》,《申报》1947年8月20日,第1张第4版
萨本驹重婚案是战争所带来的重婚问题中的一个典型。在沦陷的北平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1942年的一件离婚案中,原告赵关淑兰与萨本驹案中的陈季政有着相似的遭遇:赵关淑兰于1926年与赵振华结婚,家境困苦。在赵关淑兰身怀次子的时候,丈夫赵振华不知所踪,赵关淑兰在娘家亲戚的照顾下平安生产,但所生婴儿没活过百天就夭折了。之后赵关淑兰赴天津寻夫,夫妻两人同在天津的宝成纱纺厂做工,但不久赵振华被裁员,赵关淑兰便独自供养家庭。不料不久后,丈夫再次不辞而别。之后赵关淑兰接到书信一封,说赵振华已经考入了南京炮兵学校,赵关淑兰“始而民心非常愤怨,既见此信,心亦稍安,遂安心在厂工作,冀耐忍数年,民夫毕业后必有出头之日”,但丈夫一去多年,“事变前尚有书信往来,事变后即音信杳然”。赵关淑兰经常去婆家探问消息,某次在抽屉里发现赵振华的家信一封,这才发现“夫已在广西落户,与沈姓之女结婚已三年之久,且已生子”。(《赵关淑兰请求离婚》[1942年],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J065-018-02681)
赵关淑兰等待多年,不料自己竟成了“沦陷夫人”。于是将丈夫诉至伪北京市地方法院,请求离婚。
在萨本驹案中,经过双方的代理律师正式谈判,结果决定由萨氏给陈季政生活津贴三亿元,正式宣告离婚。但在赵关淑兰请求离婚案中,“沦陷夫人”得到的判决仅仅为“准原告与被告离婚。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据当时报刊所载,在萨本驹案中,“沦陷夫人”陈季政“对于无线电一项,颇有研究”,是“一个标准的评剧迷”,由此可以推断出陈季政受到过新式教育。而在赵关淑兰案中,“沦陷夫人”赵关淑兰的教育状况未知,已知的是赵关淑兰曾在宝成纱纺厂做过女工。
以上两个案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和主要人物均不相同,将二者进行对比,不是为了对比两个“沦陷夫人”何者更惨,而是希望借此来突出沦陷时期北平中下层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无论是从判决的结果来看,还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沦陷夫人”赵关淑兰的生活前景都不甚乐观。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