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主流,或者说正统的中国书法,似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即以二王和晋唐为则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已被后世经典化,从未有实质性改变。在这个体系之内是自由的,笔墨风格可以有所不同,即便二王父子之间也有差异;否则,如果试图超越这个体系,诸如明人徐渭、清人郑板桥等,无论士人、他人如何建构,也无论大众如何喜爱、称赞,均不被固有体系所接纳;即便赵孟頫那样的显赫人物,也会被骨头里挑刺,何况他也是这一体系的承续者。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书法的艺术标准,早在二王和晋唐已被塑造完备,已经完成了艺术价值体系的建构。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它是客观存在的一尊“神”。它就在那儿,永远在那儿,一直在傲视群雄、俯瞰过往,无论时光如梭、朝代更替等,都不可能改变它的容颜,它的功能只是像“神”那样等待众人、后人顶礼膜拜。所以,学书就是摹仿,摹仿就是仿古。于是,“临摹”不仅成为了书法入门的必由之路,也成为了所有书家的本分而伴其终生,其它路数均为旁门左道,甚或歪门邪道。
与书法关系密切的中国绘画就不是这样,尽管它也有某种程度的“逻各斯性”。例如汉画像石,在中国画史上具有显赫地位,但是,在砖石上雕刻限制了画技,存有很大局限也就在所难免,“象征”而非“相似”是其主要特点,而“相似”才是图像艺术的根本。至魏晋南北朝,中国画开始了对相似性的自觉追求,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等,并非常人理解的那样是在强调神韵,而是强调它的前提——形,只有“形似”才有可能“写神”“传神”。没有“形”怎么可能有“神”呢?不“写照”怎么可能“传神”呢?而当时关于“形”的“写照”,恰如张彦远描述的那样,仍处于“人大于山,水不能泛”的幼稚水平,这是不可能很好“传神”的。而这一“形似”技术,直到宋代才算达成。至于宋代之后的士人画、文人画,则是宋画“形似”的背离,或者说是另一层面的“形似”。概而言之,中国画从“象征”到“相似”,从“写实”到“写意”,观念和技术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与此相关的评价标准同样如是,从顾恺对“形似”的倡导,到苏轼对“形似”的贬抑,中国画的艺术追求完全不同;更不必说西画的艺术标准了,现代与传统几近天翻地覆。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书法何以另类?它的艺术标准何以历久不变,成为了“神”一样的客体存在,就像一尊“逻各斯”雕像?
首先,参照现象学的观念,“书法现象”当是根本依据。所谓“书法现象”,就是将其作为“存在物”。“书法现象”作为“存在物”,汉字书写是其存在的理由。而汉字本身,就其起源而论,是祭神的产物——记录“神言”“神意”,于是才有汉字的创生。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之类的神话传说,实则是汉字神性出身的表征。也就是说,汉字及其书写,不过是从“神”那儿挪用过来借以记录“人言”“人意”,是神秘、神圣之物的世俗化。在这一意义上,即汉字作为神秘、神圣之物这一身份属性,却是稳定的、永恒的;因为它已经作为文化积淀,永远地沉浸在了使用者的心理深层。即便后世拟或现代社会,汉字书写在道教(符箓)和民间信仰中的神性表征依然如故,汉字崇拜(“惜字”传统等)依然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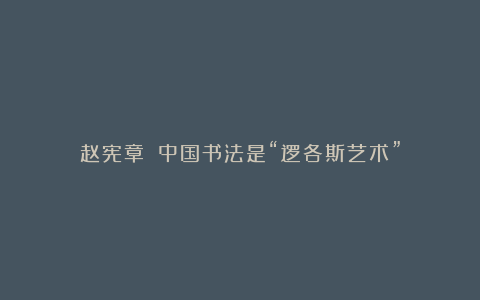
其次,从商代甲骨到唐代楷书,2000年的历史足以使文字书写经典化,唐楷和狂草的成熟更是在“法”的层面形成了铁律。这是由能否“识文断字”在古代社会的重大意义所决定的,也是由书写之美在个人社会化中的重大作用所决定的,此乃众人皆知,无需赘言。此外,古代文人生活的相对单纯、相对空闲,也为书写的历练和经典化提供了有利条件。重要的还在于,汉字作为表意符号,其构型规律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属性,也为书写和书像的经典化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再次,由于书法创新、另寻别路被字象所束缚,书家也就不可能无视字象的构成,因为字象是书法艺术标准的“大管家”。这也是书法与绘画的不同之处:眼之所见都可以是绘画的对象,即便不可见的鬼神也可以在画中现身。就此而言,绘画的题材是自由的。书法就不同了,它必须遵循字象之约定俗成,即便狂草,它的笔画和书像也不能任性而为。如前所述,“相似性”是绘画的一般属性——传统绘画与物相似,现代绘画与意义相似。“相似”意味着造像必有根据、必有参照、必有依托。书法呢?书像与何物相似呢?尽管古代书论习用“比象”,但是事实却是,不存在与它相似的参照物——将点画誉为“高山坠石”、将横画誉为“千里阵云”等,只是比象修辞而已,何况真正意义上的“象形”只是字象的初级形态,“像意”才是它的普遍构型规律。而“意”,并不是“物”,不像“物”那样具有可见性、感官触及性,它是无形的、微妙的、飘忽不定的。所以,书法造像只能参照前人、旁人的成功书写(临摹)——这些成功书写来自2000年来的不懈努力——不存在绘画那样直面世界的“写生”。就此而言,书写的典范,就是已被公认的美的书像。而美的书像不过是一种“心象”,即杨雄所谓“心画”是也。于是,书法之临摹,实则是临摹“心迹”,临摹的对象并不是“物”,从而增加了书法既不脱离字象又能创新的难度。
当然,“字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古文和今文、繁体与简体……指向同一意义的字象有可能很不相同。但是,这些不同属于“约定俗成”,拟或是官方定规,已被普遍认同,不可能是书家个人独一无二的发明,就像语言是公共产品,不存在真正的“私人言说”那样。就此而言,书法作为艺术,与一般艺术的规律完全相悖:绘画等一般艺术强调个性、独特性、不可重复性,否则就是“复制品”而非艺术。当然,不同的书家也有不同的书风,但是,由于它被字象所囿,导致书风的个性非常微妙,甚至难以察觉、难以辨析,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其它艺术的风格差异,是很容易辨析的,否则就很难被冠以“风格”,因为“风格”就意味着独特、鲜明。何以如此?还要回到“书法现象”本身——它是“书像”而非“画像”,前者是“言说”的记录、延宕和变体,后者是眼见物像的图像再现。例如当今的“实验书法”,之所以被戏称为“丑书”而不被公众认可,主要原因在于背离了字象之定规。书法作为艺术(特别是草书),一般观者难以辨识很正常,但是,至少应当使人想到它是文字,或能激活受众联想到文字(就像《侠客行》中的石破天那样),否则便与鬼画符无异,不可能成为大众艺术。而书法作为艺术,本是最大众的艺术。
书法及其书像既然是“言说”的记录、延宕和变体,那么,它就和创生并使用这一语言文字的民族性格密切相关。很有可能的推测是:这个民族需要这样的逻各斯“神”,需要延绵不断、稳若泰山而不奢望改变什么。于是,以史为则、以古为则也就成了他的最佳参照系;建构一个逻各斯“神”,寄希望于这位“大管家”能够管住家、管好家,也就成了他的最理想的社会目标。
总之,“字象”是书法艺术标准稳若泰山、始终如一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书法创新的牵制因素——牵制书家不可以自行其是、任性而为。字象之不可变异的意义植根于书法的公共性、实用性,因为书法不像其它艺术那样纯粹,它不是纯粹的艺术。在这一意义上,书法创新是难的,“字象”之囿使其成为了“逻各斯艺术”。同意反复,二王和晋唐建构的书法艺术标准,就像“神”一样的客体存在,书家只能膜拜它、摹仿它、接近它而不可以改变它,有点类似鲁迅在《无声的中国》所说的“开窗”。
不错,当代“实验书法”正在尝试“开窗”,这显然是一个伟大的设想,期待他们能够成功,哪怕能够先开出一线“窗隙”。
稷下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