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赵孟頫,字子昂,生于吴兴。若说此生有何物伴我如影随形,必是那《千字文》。自垂髫之年至鹤发暮年,这一千字非但未曾令我厌倦,反成我笔底山河、心中日月。且让我以笔墨自述,我与《千字文》的夙世因缘,本文放大版按文章顺序选取前120个字,供大家欣赏。
幼年初遇
五岁那年,我于湖州老宅初见智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彼时虽不解其意,却痴迷于字间流转的气韵。母亲常言:“笔墨乃士人之骨。”我便以《千字文》为梯,日临五百遍,纸堆如山,笔秃成冢。少年时光,庭院深深,唯有墨香与蝉鸣相伴。曾有乡人笑我痴,我却暗誓:“千字不工,何谈书道?”
青年淬炼
弱冠之年,我已遍临诸家。然《千字文》始终是我试炼新体的战场。楷、行、草、隶、篆,乃至六体同卷,皆以此文为基。一日,友人持我少年旧作《千字文》来访,卷上稚拙之笔令我赧然,却亦惊叹:“昔日之拙,乃今日之阶。” 我曾自题:“仆二十年来,写千字文以百数。”非虚言也——每遇笔法滞涩,便取千字文重书,字字如磨剑,锋从苦寒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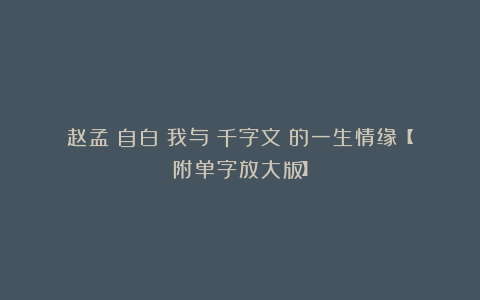
中年悟道
仕元后,世人谤我“失节”,唯《千字文》知我心事。夜阑人静时,展卷挥毫,以行草抒胸中块垒。一卷《行书千字文》,起笔楷法森严,渐入行云流水。墨迹间,可见王右军之飘逸,亦藏颜鲁公之筋骨。妻子管道升观我作书,笑言:“子昂笔下千字,如江潮奔涌,止于规矩而不拘于形。” 此言深得我心——书法之道,贵在“以古人之法,写我之精神”。
晚年化境
暮年归隐,再书《千字文》,笔锋已褪尽火气。绢本之上,楷行相生,如老梅著花,枯润相济。有后生问:“何以千字文书之愈老愈妙?”我答曰:“初学时求形似,中年求神似,至老则忘形神,唯见性情。” 今观故宫所藏《行书千字文》,起首“天地玄黄”四字犹带智永余韵,至“焉哉乎也”已自成宇宙——此非笔墨之功,实乃一生心血所凝。
千字文于我:非止书帖,更是人生
世人皆道我以《千字文》传艺,却不知它亦是我安身立命之舟。宋室倾覆时,母亲诫我“自力于学”,我便以千字文为筏,渡尽乱世浮沉;仕元争议中,又以千字文为镜,照见本心澄明。一卷千字,写尽王朝更迭、人世沧桑,却终归于“坚持雅操”四字——此非周兴嗣之文,实乃我赵孟頫之命。
今垂垂老矣,犹能提笔作《千字文》。篆隶之古朴,真草之飞扬,皆在此一千字中流转轮回。若问来世愿为何物?但求化为一管笔,再书千字文万遍,与天地同老,共笔墨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