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赵孟頫《梅花诗》第十首最后四行。
原文:
麻姑过君急洒扫,鸟能歌舞花能言。
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
繁体:
麻姑過君急灑掃,鳥能歌舞花能言。
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
我们来看看赵孟頫写此诗时,那支笔底下流淌出的韵味和心思。
想象他铺开纸,蘸饱墨,不是机械地抄字,而是在用线条和墨色讲一个关于喧嚣与寂灭、神迹与尘烟的故事。
开头“麻姑过君急洒扫”,赵孟頫怎么写的?
“麻姑”二字,尤其是“姑”字,他手下那支笔走得特别轻盈灵动,笔尖像是沾着仙气儿在飘。线条细而不弱,流畅得很,像麻姑裙裾带起的风。到了“过君”,字形稍稍收敛,带点恭敬的意思,但“过”字的走之旁,那一捺或者挑笔,依然带着仙家行迹的飘逸感。
最精彩是“急洒扫”——“急”字写得快,笔锋甚至有点飞白,像麻姑袖子一挥带起的风尘;“洒”字的三点水,不是规规矩矩的点,可能用侧锋带过,像是水珠甩出去的痕迹;“扫”字的提手旁和“彐”部,笔势肯定急促,转折干脆利落,真像是在用力挥动扫帚,要把凡尘俗气都扫干净,迎接仙人。
这一行字看下来,墨色浓淡变化里,仿佛能听到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和仙袂飘飘的簌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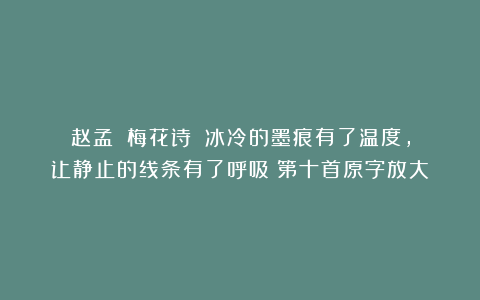
紧接着“鸟能歌舞花能言”,这句诗本身就有种万物有灵的热闹。赵孟頫的笔也跟着欢腾起来。“鸟”字可能写得小巧跳跃,;“能”字的两个部分,结构安排得特别有趣,有种笨拙又可爱的姿态。
“歌”和“舞”字,笔画的舒展幅度肯定大了,线条的起伏摆动,尤其是“舞”字下半部分那些笔画,赵孟頫处理起来一定充满律动感,仿佛能看到花枝摇曳。
到了“花能言”,“花”字的草字头,他可能用几个轻快的点代替;“言”字,特别是下面的“口”,不会写得死板,或许带点俏皮的上翘。
这一行整体墨色相对饱满润泽,笔速轻快流畅,线条的节奏感极强,看字如闻其声,如见其态。
然后,笔锋一转——“酒醒人散山寂寂”。
前一刻的热闹喧天,瞬间被巨大的寂静吞噬。
赵孟頫的笔也立刻沉了下来。“酒醒”二字,“酒”字的“酉”部墨色可能稍重,带着宿醉的沉滞感;“醒”字的笔画肯定写得慢、写得稳,甚至有点涩,透出清醒后的疲惫与空茫。
“人散”二字,结构会显得格外疏朗空旷,“散”字的左右两部分,距离可能拉得比平时开些,笔意萧索,真像看客散去后留下的虚空。“山寂寂”三个字是这句的灵魂。“山”字稳稳地矗立在那里,线条厚重肯定,但透着一股子亘古的沉默;“寂”字,整行字的节奏骤然放慢,笔力内收,墨色枯淡,空间感被极度放大,巨大的“寂”字像墨一样在纸上晕染开来,压得人喘不过气。
从“鸟能歌舞花能言”到“酒醒人散山寂寂”,这书法上的强烈对比,把诗歌情绪的陡转直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比直接读诗还要震撼。
最后收束在“惟有落蕊黏空樽”。繁华落尽,只剩这一点点凄凉的余韵。赵孟頫写这句时,笔触一定是细腻、缓慢而带着无限怅惘的。“惟有”二字,写得轻、写得淡,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确认感。
“落蕊”二字,“落”字的草字头,他可能会用极细极淡的笔触,甚至断断续续,像飘零的花瓣;“蕊”字结构复杂,但在赵孟頫笔下,绝不会写得密不透风,而是留足气息流动的空间,笔画纤细,墨色浅淡,强调其脆弱易逝。
最关键的是“黏空樽”。“黏”字怎么写?这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拖沓、粘滞、挥之不去的意味。赵孟頫写这个“黏”字,用墨可能会稍润一点,但绝不是饱满,而是带点拖泥带水的感觉,笔锋在纸上运行时有细微的迟滞感,尤其是右边的“占”部,那一点或短横,会显得特别有分量,像是落花沾在杯壁那种微妙的附着感。
“空樽”二字,“空”字宝盖头下的“工”,笔画肯定轻、虚、疏,强调其内里一无所有;“樽”字的“木”旁稳扎,但“尊”部结构会处理得相对疏朗,尤其里面部分,墨色淡雅,清晰地指向那个曾经盛满欢愉、如今空空如也的酒杯。末笔收束,必然是含蓄内敛的,带着无尽的余味。
看赵孟頫写这四句,就像看他导演一场纸上戏剧。他不仅仅是在“写”字,更是在用笔的提按顿挫、墨的浓淡枯湿、线的疾徐疏密、形的聚散开合,来精准地“演奏”诗歌的每一个音符和情绪转折。
从仙使降临的忙乱轻盈,到万物欢腾的灵动雀跃,再到盛宴散场的巨大死寂,最后归于杯底残蕊的凄凉粘稠。他笔下流淌出的,是看得见的仙乐、摸得着的欢愉、压得人窒息的寂静和挥之不去的怅惘。
那“黏”在“空樽”上的,何止是几片“落蕊”,分明是赵孟頫用笔墨凝结住的,繁华过后的那一缕清冷魂灵。这就是他的本事,让冰冷的墨痕有了温度,让静止的线条有了呼吸,让千年前的诗意,穿透纸背,直抵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