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
的文献学价值*
赵 嘉 梁健康
内容提要:《爱日精庐藏书志》是清代藏书家张金吾所编的一部藏书目,该书的最早版本为张金吾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排印的《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卷本(以下称“四卷本”);常见版本为道光七年(1827)行世的《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续志》四卷本(因《续志》与四卷本在著录内容上无重合,故以下称“三十六卷本”)。四卷本较之三十六卷本在收书数量、体例形制上属于早期形态,但后者同时也删去了前者所保留的信息、改变了目录在体例上的特征。通过对四卷本所保留的信息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张金吾的藏书来源及其编写《爱日精庐藏书志》的最初设想有所了解。
关键词:《爱日精庐藏书志》 藏书来源 目录体制 张金吾 私家藏书
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较为罕见,前辈学人对此关注不多,柳向春先生在整理本《爱日精庐藏书志》的《整理前言》谈及四卷本“现今海内公藏,仅存国家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两部而已。”[1]今所据四卷本即为国家图书馆藏本[2]。
四卷本
一、著录藏书来源
《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卷本经、史、子、集每部各一卷,共著录古籍383部;《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续志》四卷本同样采用了四部分类法,共著录古籍801部[3]。除个别书籍仅见于四卷本外,三十六卷本中包含了四卷本所著录的书籍,但是同时也将大部分四卷本所著录的书籍来源信息删去。
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藏书来源梳理
张金吾在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中,于每部书籍下,以小字注明藏书来源,笔者依据不同的来源,将其分为得自书坊、书贾,得自藏书家(含亲友),其先已有藏书以及其他四类。同时,又结合张金吾《言旧录》及同一时期友人黄丕烈的题跋,将诸来源整理如下:
(一)得自书坊、书贾 共168部
(二)得自藏书家(含亲友) 共135部
“同里”指张金吾所居住的琴川,即常熟;“同郡”指江苏地区。由上表可知,张金吾与藏书家好友(含亲友)的书籍交流十分密切,彼此间传录、赠送以及买卖是当时藏书家之间扩充藏书的方式,特别是建立在交谊基础上的传录,是对书坊购书的重要补充。
(三)其先已有藏书 共31部
此类为张金吾在编写《爱日精庐藏书志》时,选自其先已有藏书的部分。
旧藏,共有23部,其中2部信息来源在三十六卷本中有所保留,其余均被删去。
先君子手抄本,张光基,字南有,一字心萱。张金吾祖父张仁济的长子。
共有7部,来源信息在三十六卷本中均被保存;
八世祖端岩公刊本,共1部,亦于三十六卷本(“刊本”非来源信息,属于其先已有藏书);
(四)其他 共49部
以下三类更接近于版本形态,并未直接说明来自何人。
从道藏本传录,共有1部,三十六卷本保留。
文澜阁传抄本,共有46部,其中2部未被三十六卷本收录,其余被三十六卷本保留。
天一阁传抄本,共有2部,三十六卷本保留。
以上四类,合计383部。
总之,通过以上对张金吾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著录藏书来源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对一位生活在清代中期江苏地区藏书名家的聚书途径有一定的了解,即购买和传录是当时藏书家收藏图书的主要方式,书商所从事的古籍交易在当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传录的方式在藏书家扩充藏书规模时也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这种传录主要出现在同是藏书家的亲友之间。江苏地区又是当时经济和文化非常繁盛的地区,所以张金吾的聚书特点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二、著录藏书来源的价值
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了藏书的来源,对于研究书籍的递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为以下研究提供帮助:
(一)对顾之逵藏书流散的补充
顾之逵和黄丕烈、周锡瓒、袁廷梼四位藏书家都生活在苏州地区,被称为“藏书四友”,但顾氏是四位藏书家事迹最为稀缺的。刘鹏先生在《顾之逵生平及书事述略》一文中对顾氏事迹和藏书有一定的研究,依据顾氏题跋、黄丕烈、顾千里、钮玉树诸家题识日记及部分藏书目录,已考得顾氏藏书百余种,在文中列举国家图书馆所藏顾氏藏书十余种。另撰有《重辑小读书堆善本书志(经部)》一文,收录顾氏藏经部书21种[18]。
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中著录源自顾之逵藏书25部,与刘鹏先生已公布的顾氏藏书相较,相同的有3部,其余22部未提及,今将未提及者条列于下,或为顾氏藏书研究提供参考:
(1)周易注十卷 毛氏影写宋相台岳氏本;(2)经典释文残本一卷 宋刊本[19];(3)叙古千文一卷 旧抄本;(4)补后汉书年表十卷 影宋抄本;(5)吴越春秋十卷 影宋抄本;(6)直斋书录解题残本四卷 旧抄本;(7)旧闻证误残本二卷 宋刊本;(8)宝祐四年会天历一卷 影宋抄本;(9)近事会元五卷 旧抄本;(10)玉堂嘉话八卷 旧抄本;(11)东皋子集三卷 旧抄本、脉望馆藏书[20];(12)杼山集十卷 旧抄本;(13)欧阳行周集十卷 旧抄本;(14)李元宾文集五卷 旧抄本;(15)元(玄)英先生诗集十卷 丛书堂抄本、汲古阁藏书;(16)禅月集二十五卷 旧抄本、雁里草堂藏书[21];(17)祖龙学文集十六卷 旧抄本;(18)谢幼槃文集十卷 旧抄本;(19)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三十卷附无住词一卷 宋刊本[22];(20)翠微南征录十一卷 旧抄本、汲古阁藏书;(21)闻过斋集八卷 旧抄、淡(澹)生堂藏书;(22)东山词一卷 宋刊本、汲古阁藏书[23]。
因顾之逵、张金吾二位藏书家都有不常在藏书上钤印、题跋的习惯,所以使得通过书籍上的钤印、题跋来判断递藏源流变得较为困难。如以上所列书目中的残宋本《经典释文》,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6710),该书无顾之逵、张金吾钤印或题跋,但是《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了这部宋刻本,可知此书曾经张金吾收藏[24];而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又进一步著录了此本是购自顾之逵,因此在递藏线索上补充了顾、张二人[25]。
《重辑小读书堆善本书志(经部)》一文中著录了顾之逵所藏清通志堂刻本《经典释文》三十卷(索书号2135),书中有顾之逵校语,并录惠栋、段玉裁、臧镛堂校,是顾氏所藏另一本。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顾之逵去世的时间是嘉庆二年(1797)。据黄跋,知顾氏小读书堆藏书的散出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26],而张金吾四卷本的问世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说明张氏购得顾氏藏书很早,数量也很多[27]。
(二)对黄丕烈旧藏的补充
黄丕烈通常会在其藏书上钤盖印记、撰写题跋,但亦有例外,因此增加了黄丕烈旧藏古籍研究的难度。前辈学者中如丁延峰先生《求古居藏宋刻本存佚考录》,依据黄氏所编《百宋一廛书录》《百宋一廛赋注》《求古居宋本书目》及其他资料,统计出黄丕烈旧藏宋本至少在二百四十种以上,现存黄藏宋本实有一百六十七种[28]。
我们在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中,根据张金吾对来源于黄丕烈的藏书著录,发现了宋刻一部、元刻一部、明刻一部,均为黄氏旧藏,前人对此留意不多。
1.宋本《史记》残本三十卷
《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卷本、三十六卷本均收录此本,版本著录为宋蜀大字本,每页十八行,行十六字,注二十字。四卷本著录来源信息“得之郡城黄氏”。
勾稽黄丕烈所编的三部宋板书目,可知其先后收藏有三部“蜀大字本”《史记》,分别是列传五卷残本[29],一百三十卷全本(有抄配)[30]和廿四册残本[31]。售与张金吾者当为廿四册残本。
此本自黄丕烈、张金吾之后,递藏线索并不明显,较早记录此书由张氏爱日精庐散出的是钱泰吉,其在《曝书杂记》中抄录了钱天树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眉间所作的批注,名曰《家梦庐翁所见旧本书》,其中著录了这部《史记》:
《史记》。残本,蜀大字本,此不全本三十卷,今藏小重山馆胡氏。[32]
钱天树所批的《爱日精庐藏书志》应该不是四卷本,否则当知晓此书为黄丕烈旧藏。
此书后归郁松年,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一著录此本,为“史纪集解宋蜀刻大字本。上海郁氏藏。”[33]其后解题文字中称此书“共二十九卷”,复核其所列存卷数目,实际上是漏了卷三十四(《世家》四)。
再后归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卷二著录《史记一百三十卷》:
宋刻蜀大字本。曾藏黄氏士礼居,即顾广圻《百宋一廛赋》所云字大悦目者。惜卷数仅及半而弱。历藏吴宽、文征明、钱维城、韩世能、当湖胡氏、泰峰郁氏诸家。[34]
《持静斋书目》所记录之本今藏上海图书馆,著录为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存三十卷,清单学传、徐渭仁跋、清莫友芝题识、杨守敬、康有为跋(索书号758030-46)[35]。
据书中诸家题跋及钤印,知此本曾经张蓉镜、当湖胡惠孚[36]、泰峰郁氏等人收藏,当与钱天树所记《史记》为同一本,存三十卷。
尾崎康先生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一书中也提到此本,同时也注意到了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了此本,但在梳理此书递藏源流时,未提及黄丕烈、张金吾、丁日昌[37]。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对此本来源的著录,将黄丕烈旧藏与此书后来的递藏线索加以连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元本《白虎通德论》十卷
《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卷本、三十六卷本均收录此本,為元大德刊本,区别在于四卷本作“天籁阁藏书”,三十六卷本作“项氏万卷堂藏书”,究竟为项氏兄弟项元汴、项笃寿谁人藏书,原书未见,不得而知。
四卷本著录来源信息“得之郡城黄氏”,同时还写有“后附黄荛圃先生跋”,但无论是四卷本还是三十六卷本,都没有抄录黄氏题跋,三十六卷本将与黄丕烈有关的信息全部删去。
张金吾所藏的这部黄丕烈旧藏元大德十卷本《白虎通德论》今不知所踪,但在黄丕烈的题跋以及他人著述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这部书的线索:
今藏国家图书馆的元小字本《白虎通》二卷(索书号06889,收入《中华再造善本》),黄丕烈在题跋中提到了与小字本不同的另一部元大德刻本:
余思《白虎通》宋本流传绝少,最古以大德刻本为先。余得两本凑合,尚有缺叶,然已矜为罕觏。今又得此小字本,可称双璧。[38]
这说明黄丕烈所藏元大德本是由两本拼凑而来,并且尚不完整。
又,徐乃昌在《积学斋藏书记》中的《缩写元大德本风俗通十卷》一条下抄录了黄廷鉴的一篇跋,该跋也提到了黄丕烈所藏的元大德本《白虎通》:
余向知《白虎》、《风俗》二通有元人合刊大字本,嗣于嘉庆初元得见吴门士礼居所藏,而《风俗》已失,心耿耿者四十余年。[39]
又,铁琴铜剑楼旧藏有元大德本《白虎通德论》一部,《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收录有此本首卷卷端书影,丁祖荫所撰《识语》书中有项氏子长、项氏万卷堂藏书印,并称此本曾经张金吾爱日精庐收藏,但书影图片模糊,印章无法辨认[40]。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收录有此书首卷卷端,藏印为“项氏子长”“万卷堂印”,为项笃寿藏书(索书号6890)[41]。但此本没有黄丕烈题跋,不知是否即是张氏《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著录之本。
3.明刊本《石门先生文集》七卷
《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卷本、三十六卷本均收录此本,为明刊本,四卷本著录来源信息“得之郡城黄氏”,同时还写有“后附黄荛圃先生跋”。但无论是四卷本还是三十六卷本,都没有抄录黄氏题跋,三十六卷本将与黄丕烈有关的信息全部删去。
黄丕烈所藏七卷本明刊《石门先生文集》今不知所踪,但是我们在《荛圃藏书题识续录》中找到了黄丕烈题在旧钞本《石门集》的题跋,谈到了其所藏的七卷本:
于案头见有旧钞本《梁石门集》,阅之,有序无目,不分卷,因忆余家向有旧刻本,无序有目,却分卷为七,似不及余本。[42]
黄丕烈所跋旧钞本《石门集》,不分卷,今藏湖南图书馆(△435/2),曾为叶启勋、叶启发收藏,见于《拾经楼䌷书录》《华鄂堂读书小识》[43]。
由旧钞本《石门集》中黄氏跋文可知,其另藏有七卷旧刻本一部,与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著录者当即一本,惜张金吾未抄录黄丕烈题跋。
三十六卷本
三、四卷本到三十六卷本的目录体制变化
前辈学者对于《爱日精庐藏书志》在目录体制上的特点已有论述[44],但当时论者未见四卷本,而该书目由四卷本到三十六卷本在目录体制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理解张金吾编写思想的变化至关重要。
(一)由自撰解题到附入原书序跋
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有黄廷鉴所作序,提到了张金吾编写该书目的背景和参考体例:
今夏曝书之暇,取凡宋元旧刻暨新旧抄帙罕见之本凡三百八十种,计一万二千卷……为《藏书志》四卷,其传本久绝佚而复出者,仿公武、直斋之例,略为解题,意在存佚继绝,初不欲示人也。
黄廷鉴在序文中提到的“公武”“直斋”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可以看出,在黄氏眼中,四卷本的《爱日精庐藏书志》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在体例上是相同的。
同样,张金吾在四卷本的序中(三十六卷本称之为“旧序”),也有类似的说明:
然自《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外,惟《读书敏求记》略述源流,故储藏家每艳称之。……若有明及时贤著述,时代既近、搜罗较易,故亦从略,其前此逸在名山、未登柱史,为世所不经见者,则间附数语以识流别,名之曰《爱日精庐藏书志》。
此处“间附数语以识流别”与上文黄氏序提到的“略为解题”,具有相似之处,即内容由编者所作,而不是抄录书籍的序跋,这也是四卷本和三十六卷本在在体制上非常明显的区别,四卷本中没有抄录书籍的序跋。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黄丕烈《续颜氏家训》(宋残本)的题跋中也找到了类似的观点:
书之源流,具详主人所著《藏书志》中。
黄丕烈卒于1825年,在其生前所见只有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本问世在1827年)。这篇解题文字在四卷本和三十六卷本中几乎没有差别,后者主要是改动了四卷本解题文句的顺序,删去一处征引书目,并未抄录序跋。可见黄氏所谓“书之源流”与张金吾“间附数语以识流别”是呼应的,都是作者撰写的解题文字。
由以上可知,解题内容是否为编者所作是四卷本与三十六卷本的主要区别之一,《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读书敏求记》也都具有这一特点。之后的三十六卷本加入了大量对书籍序跋的引用。张金吾在三十六卷本的《新序》和《例言》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新序:
六七年来,增益颇多,乃重加编次,附入原书序跋,厘为三十六卷,仍其旧名曰《爱日精庐藏书志》。
例言:
自来书目无载序跋者,有之,自马氏《经籍考》始,是编略仿其体。……余则备载全文,俾一书原委,燦然可考。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张金吾在三十六卷本的《新序》和《例言》提到附录原书序跋,但已不再提及《读书敏求记》,也说明其认识发生了变化。
(二)对《四库全书总目》体制上的改变
张金吾将《四库全书总目》奉为经典,高度崇敬,在其《爱日精庐藏书志》中再三致意,具体在实践中便是在体例上的借鉴。这种借鉴,在四卷本和三十六卷本中也有所变化。
1.由著录书籍来源到删去
著录藏书来源是张金吾借鉴《四库全书总目》最为明显的一个体现。《总目》在著录书籍时,会在书名下著录书籍来源,如“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浙江巡抚采进本”等。《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卷本也在书名之下著录书籍的来源信息,当是借鉴了《总目》的这一做法。
著录藏书来源的做法在传统目录中较为少见。此前,这一信息往往多是出现见在目录的解题或者题跋中,但将其作为著录项贯彻在目录中,在清代私家藏书目录中,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可谓罕有其匹[45],也正是因为四卷本中著录了书籍的来源信息,才为我们今日研究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的递藏源流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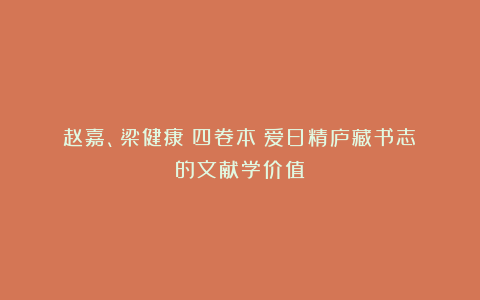
三十六卷本虽仍然部分保留了四卷本中的书籍来源信息,共83部,较之四卷本383部少了300部,在数量比例上已经不能被看作是整体特征,因此可以看成是一种在目录体制上的前后变化,变化的结果是原来作为著录项之一的书籍来源信息变为了非必要项。
这种变化的原因尚无明确依据,但是可以从三十六卷对书籍来源信息的取舍加以推测。三十六卷本将四卷本中购自书坊书贾的来源信息全部删去,是删除最为彻底的,说明张金吾对于著录反映与古籍交易相关信息的取舍发生了变化,最终决定不予保留。而其余来源信息则多呈现出一种部分删去部分保留的状态,取舍标准也并不明晰,或许与张金吾所编书稿即未统一,前后不一致有关系。
2.解题形式由概括变为引用
概括一书内容或者构成一直是传统目录中较为常见的形式,《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四库全书总目》都是这种形式,张金吾在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在采用这种形式的同时,还会将《总目》中的解题概括后使用,此时的《爱日精庐藏书志》与《总目》为代表的目录在体制上是相同的。
三十六卷《爱日精庐藏书志》在解题形式上发生了变化,我们归纳总结出以下三种类型,加以比较说明。
①填充型
此类在四卷本中由概括一书序跋构成情况,变为将原书序跋直接依次抄录,区别在于变整体概括为直观抄录,后者详于序跋文字而无整体概括。四卷本的特征符合藏书家最初编写书目时简洁明了的特点,此类变化在三十六卷本中较为常见。
四卷本:
《易变体义》十二卷 文澜阁抄本
宋都洁撰,前有赣川曾几、范阳张九成两序及自序、进书劄子。
三十六卷本:
《易变体义》十二卷 文澜阁抄本
宋都洁撰。
夫《易》如天地,……赣川曾几序。(内容略)
张九成序。(内容略)
又《登封进书劄子》(内容略)
②改概括书中序跋为直接抄录型
四卷本:
《周易经义》三卷 得之同里李松门遵古堂书坊
元涂溍生撰,溍生字自昭,宜黄人,《江西通志》称其邃于《易》,著有《易义矜世》。……未审即此书否?后附郡城吴枚庵翌凤先生跋。
以上引文即概括自吴枚庵跋,三十六卷本删去了这些概括之语,改为直接抄录吴氏题跋全文。
③改近《四库总目》体为简略型
四卷本:
《读四书丛说》六卷 元刊本 得之四美堂书坊
元许谦撰。按,《元史》本传载谦《四书丛说》二十卷,《经义考》云未见。伏读《四库全书总目》云,《四书丛说》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缺其半,《论语》则已全佚,盖世已久不见全书矣。是编系元椠初印本,凡《论语》上下两卷,《中庸》《孟子》各二卷,缺《大学》一卷、《论语》中一卷。
三十六卷本:
《读四书丛说》残本 六卷 元刊本
元东阳许谦撰。
是本系元椠初印本。凡《论语》上下两卷,《中庸》《孟子》各二卷,缺《大学》一卷、《论语》中一卷。
《读四书丛说》是《四库》未收之书,见于《四库总目》,理应按照张氏在三十六卷本《例言》所言“未经采入《四库》者,仿晁、陈两家例,略附解题,以识流别。”而三十六卷本却删去了起到“以识流别”作用的部分解题。与之类似的情况是,三十六卷本多将四卷本解题中的作者生平爵里删去,与《四库总目》对作者的介绍也明显不同。
这些修改变化,使得四卷本由原来较为接近《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总目》的目录体制变为以抄录书中序跋为主,近《文献通考·经籍考》《经义考》一类的体制了。
由以上《爱日精庐藏书志》从四卷本到三十六卷本的目录体制变化,说明了作为一部产生于《四库全书总目》《天禄琳琅书目》之后的私家藏书目录,张金吾由最初四卷本选择近《四库总目》式的体例,变为三十六卷本的加大抄录题跋,减少主观概括,近《文献通考·经籍考》《经义考》的体例。解题由主观概括向抄录客观序跋转变,而书中的序跋往往又和一书之版本联系紧密。《爱日精庐藏书志》虽然并没有像之后一些私家藏书目录带有更多更明显的版本特征(如记录行款、钤印等),但这种变化是张金吾编写私家藏书实践时,对已有传统目录在体质上的一种选择和尝试,是一种介于书籍内容和版本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并不纯粹。后来陆心源在《皕宋楼藏书志》的《例言》中明确其书目在体制上仿照的是《爱日精庐藏书志》,也说明《爱日精庐藏书志》在当时一些藏书家眼中,与此前目录是不同的。
*本文为河北省教育厅2024年省级研究生示范课程“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KCJSX2024007)的阶段性成果。
[1](清)张金吾撰、柳向春整理,《爱日精庐藏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页。
[2]按,此本见于“中华古籍资源库”,著录为清嘉庆25年(1820)张氏爱日精庐活字印本(善本书号15069),此本中有张乃熊“菦圃收藏”藏书印。
[3]按,四卷本著录古籍数量为笔者统计,四十卷本数量统计来自石祥《著录行款:版本学典范的学术史考察》,《国学研究·第四十七卷》,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313-338页。
[4](清)黄丕烈撰,屠友祥校注,《荛圃藏书题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跋,第630页。
[5]《新雕孙真人千金方》跋,《荛圃藏书题识》,第266页。
[6]《玄珠密语》跋,《荛圃藏书题识》,第268页。
[7]《韩山人诗集》跋,《荛圃藏书题识》,第762页。
[8]《爱日精庐藏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8页。
[9]按,顾之逵字安道,来自刘鹏先生《清代藏书史论稿》中《顾之逵生平及书事述略》一文,作者指出钱大昕、段玉裁在文中称顾之逵为顾安道。刘鹏撰,《清代藏书史论稿》,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108页。
[10](清)瞿镛编纂,《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06页。
[11]《爱日精庐藏书志》,第490页。
[12]张金吾撰,《言旧录》,二十八岁条下。(清)张金吾撰,《言旧录》,南林刘氏嘉业堂刊本,1913年。
[13]《言旧录》,六岁条下。
[14]《言旧录》,十五岁条下。
[15]《言旧录》,六岁条下。
[16]《言旧录》,三十七岁条下。
[17]《言旧录》,四十岁条下。
[18]《清代藏书史论稿》,第173页。
[19]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6710),曾经铁琴铜剑楼收藏。
[20]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3541),曾经铁琴铜剑楼收藏。
[21]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3568),曾经铁琴铜剑楼收藏。
[22]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6651),著录为元刊本,被收入《中华再造善本》。
[23]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7178),存卷上一卷,被收入《中华再造善本》。
[24]《爱日精庐藏书志》,第88页。
[25]按,《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著录此本,在介绍递藏源流时未提及顾之逵、张金吾,又将书中撰写题跋的臧镛堂当作此书的递藏者之一,其实臧镛堂所作题跋已言是书借自顾之逵,可知臧氏并非递藏者。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册,第1045页。
[26]《清代藏书史论稿》,第58页。
[27]《洛阳伽蓝记》跋“(嘉庆二十四年)钱唐何君梦华邀余陪琴川陈、张二君。陈字子准,张字月霄,皆今日好购古书之友,谈及顾氏小读书堆书,渠两家所收颇夥。”《荛圃藏书题跋》,第184页。
[28]丁延峰撰,《古籍文献从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97页。
[29]黄丕烈撰,《百宋一廛书录·史记》,余鸣鸿、占旭东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982页。
[30]顾广圻撰、黄丕烈注,《百宋一廛赋注》,清嘉庆十年(1805)黄氏士礼居刊本,第五叶,顾广圻赋文“良史实录,藉用识蜀。乃本古以惬心,复字大以悦目。”下有黄丕烈注“蜀大字本《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每半叶九行,每行大十六字,小廿字。所缺旧钞补足。”
[31]黄丕烈撰,《求古居宋本书目》,清嘉庆十七年(1812)黄氏求古居抄本,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5493),第二叶,“蜀本大字史记集解残本廿四册”。
[32](清)钱泰吉撰,冯先思整理,《曝书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0页。
[33](清)莫友芝撰,邱丽玟、李淑燕点校,《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34](清)丁日昌撰,路子强、王雅新整理,《持静斋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35]按,《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四册,第3-16页,提供了书中的钤印及题跋;《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第109页,提供了题跋的释文。《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陈先行、郭立暄撰,《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
[36]按,关于小重山馆主人胡氏的姓名及生卒,学界尚未明确。自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将小重山馆主人记录为胡惠墉后,许多相关资料皆承此说。但一些学者则认为胡惠墉误,当为胡惠孚,如林申清先生在《书影研究》一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9.4)依据《静嘉堂宋本书影》找到了小重山馆主人胡惠孚的名字印章。我们检阅《静嘉堂宋本书影》中的《纂图互注礼记》,确如林氏所言(《日藏珍稀中文古籍书影丛刊》第四册,第261页)。
又,关于胡氏的生卒,尾崎康先生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提到胡氏(胡惠墉)生卒为1821-1851。《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收录有宋本《毛诗要义》一部,其中有钱天树题识“壬辰仲春,篴江婿不惜重值,购得宋椠《毛诗要义》。”(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胡氏字篴江,壬辰年是1832年,按尾崎康先生所记胡氏生年,当时胡氏只有11岁,似与常理不符,恐生年有误。
[37](日)尾崎康著,《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40页。
[38]《荛圃藏书题跋》,第340页。
[39]徐乃昌撰,柳向春、南江涛整理,《积学斋藏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50页。
[40]瞿启甲编,《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41]《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9册,第3716页。
[42]王欣夫,《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卷四》,第326页。《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43]按,黄丕烈以及叶氏兄弟著录此本时均作“不分卷”,此本被收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11917,则作“七卷”,不知何据。
[44]按,前辈学者如昌彼得、潘美月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56-63页)、黄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22页)、严佐之先生在《“开聚书之门径”,“标读书之脉络”:论“藏书志”目录体制结构——以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78辑,第255-282页),均有独到深刻的见解。
[45]按,清代藏书家的目录中,如《善本书室藏书志》也在个别书名下注明该书为未某家旧藏,但是首先在数量上不似四卷本《爱日精庐藏书志》之多;其次是某家旧藏未必是书籍的直接来源。
赵嘉,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