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人生映晚霞(一)
开篇的话:我的老家在原淮阴县北吴集,在渔沟镇北边有20里路,整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都姓包。据说我们是宋朝包拯的后代,在我们包家庄流传着一个说法:因为先辈包拯在世时,儿子总跟他对着干,他想让儿子往东,儿子偏往西。包拯临死前想葬在木棺里,知道儿子会反着来,就故意说要石头棺材。结果儿子觉得一辈子没听爹的话,最后一次总该满足老人的心愿,就真用了石头棺材。石头棺材永久不烂,就压住了后人的福气,所以包姓做不了大官,出不了人才,发不了大才,这个魔咒像块石头,压在包家人的心头。
父 亲
我家有九口人,父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也是整个生产队的主心骨。他 1950 年参军,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度过了五年青春。作为侦察班长,他两次立三等功,两次立四等功,那些军功章被他小心地放在一个红色绒布带拉链的皮夹里,藏在床头的木箱底。我记事起就常常偷偷翻出来看,四枚军功章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闪着微弱的光,旁边那本红皮面的复员证上,年轻的父亲穿着军装,眼神锐利如鹰。
“爸,你在朝鲜打仗的时候,是不是像电影里那样?” 我不止一次这样问他。
父亲总是摆摆手:“小孩子懂什么。” 但在夏夜乘凉时,他偶尔会给我们讲起在雪地里潜伏的夜晚,讲起如何摸到敌人阵地前抓俘虏,讲起战友们冻得失去知觉还紧握着枪。那些故事里没有电影里的轰轰烈烈,更多的是刺骨的寒冷、无尽的饥饿和对家乡的思念。
1955 年,部队要派父亲去四川步校学习,留在部队工作。他看着复员证上“文盲”两个字,摇了摇头。“我大字不识一个,在部队能当侦察兵,靠的是腿快眼尖,到了学校还不成了睁眼瞎子?”这时候,他更想念苏北平原的黄土地,想念家乡后荡的一草一木。于是,他背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成了一名普通农民,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
1964年的冬天,苏北平原被一层薄薄的白雪覆盖,后荡大队第11 生产队的茅草屋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我,包家老三,不,其实是老四,降生在这个贫寒却热闹的家庭。母亲抱着我,看着床边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轻轻叹了口气:“又是个小子。”父亲从外面进来,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刚从生产队的场院回来,身上还带着麦秸秆的气息。“好,好,多子多福。” 他说着,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粗糙的手掌带着常年劳作的温度。
父母加上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就是九口人的大家庭。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家里的排行只算男孩,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所以对外我一直是“老三”。姐妹们似乎被默认排除在排行之外,就像她们在生产队的劳动工分总比男人少一截一样。
我们家的茅草屋在村子东边,泥土糊的墙,麦秸秆盖的顶,冬天漏风,夏天闷热,屋檐低得父亲进门得小心翼翼地低头。我家十间草房像串起来的窝棚,东头两间是灶屋,中间是三间堂屋,西头两间猪圈,南头两间前屋,堆着农具和过冬的山芋干,还兼做吃饭的餐厅。墙缝里塞着旧报纸,上面印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被风吹得哗哗响,字边角卷起来,像要飞。
我那时还不懂这些,只知道每天醒来,耳边都是家人的咳嗽声、说话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还有窗外生产队的哨子声 —— 那是一天劳动开始的集结号。
社 场
后荡坐落在一望无垠的苏北平原上,像一片叶子落在绿色的绒毯上。西边五里地是跃进河,据说1958 年大跃进时,全公社的劳力齐上阵,用铁锹和扁担挖出了这条河。父亲说,那时候没有机械,全靠人力,冬天冻土硬得像石头,夏天蚊子能把人抬走,又吃不饱饭,不少人累倒在河工上。村民们私下里都叫它 “眼泪河”,河水深处,藏着太多人的血和泪。
东边的淮沭河则是另一番景象,河水常年清澈,能看到水底的水草和游动的鱼虾。大人们说,这条河通着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都从这里过。我常常跑到河边,看白帆点点,听纤夫的号子在水面上荡开,想象着远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村子中间的社场,是全村的心脏地带,也是全村政治经济中心。三十亩地大的场子,春天晒种子,夏天堆麦垛,秋天扬谷粒,冬天卧着雪,像块被太阳晒得发亮的牛皮,那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大场东边有十几间爬头房子,像一排趴在地上的老牛。靠东的六七间是仓库,里面堆满了粮食,用芦材编的结子圈起来,一个个有一人多高。保管粮食的是两个老头,每人一把钥匙,开锁时必须两人同时在场。粮食堆最上面,用生石灰盖着“公平”两个大字的印,那是防止有人偷粮食。
我小时候最盼着分粮食的日子。生产队十天分一次粮,每人十斤,堆在大场上像一座座小雪山。傍晚收工后,各家各户推着独轮车,提着麻袋来领粮。会计用木锨把粮食分成一堆堆,嘴里喊着:“老包家七口,70斤!”“包二爷家三口,30斤!” 我们小孩就跟在大人后面,数着自家的粮食堆,心里盘算着能吃几顿饱饭。分山芋、黄豆、花生也是这样,看着堆成小山的收成,再苦的日子也有了盼头。
大场北边的六七间房子是磨面房,里面有台粉碎机,专磨玉米,开动起来“轰隆隆”响,几里外都能听见。还有一台小钢磨,磨出来的小麦面脱掉麸皮,蒸出的馒头白白的,却有一股麦香。最让我着迷的是那台榨油机,榨菜籽油和花生油时,整个屋子都飘着香味,老远的村民都推着粮食来这里加工,磨面房门口总是排着长队。
大场最西边是饲养场,养着七八头黄牛。这些牛是生产队的宝贝,耕地、打场、拖板车都离不开它们。两个饲养员把牛伺候得比自家孩子还上心,夏天给牛棚搭凉棚,冬天铺上厚厚的干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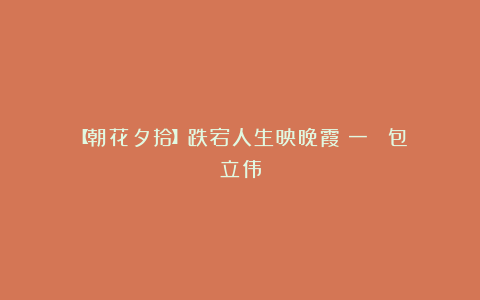
我和小伙伴们夏天最常干的活就是割牛草。放学或放暑假时,我们挎着篮子,拿着镰刀,到田间沟坡去找最嫩的青草。傍晚把牛草提到饲养场,饲养员用杆秤称了,记上工分。我力气小,一天最多能割20斤草,换三分工分,相当于大人半天的工分。但看着记工本上的数字,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觉得自己也能为家里挣钱了。
冬天没有青草,饲养员就用铡刀把花生藤、黄豆梗、麦草切碎了喂牛,还要烧热水给牛喝。父亲常说:“牛是农民的命根子,不能亏待。” 那时候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就算老得走不动了,也不能随便杀,得公社兽医站批准才行。
饲养场旁边有五六间猪圈,生产队养着两头老母猪和二十多头小猪。养猪的是二爷,个子不到一米六,是个光棍,跟着弟弟过。二爷家以前是地主,他父母勤劳,攒点钱就买地,结果刚解放就被划成了地主成分。但村里人都说二爷家人好,以前常接济穷人,所以成分虽然不好,倒也没受太多罪,只是孩子们受了影响。
二爷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老大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后来转业到山东济南,娶了个山东媳妇定居在那里。老三,我们叫三爷,学习特别好,在淮阴中学读高中,因为成分问题没能上大学。后来父亲举荐他,担保他没问题,才让他在后荡学校当了民办教师。
三爷教初中语文,课讲得特别好,县里都有名。他常顶着烈日或寒风周日去学生家家访,义务给学生补课,还常常自己掏钱给困难学生交学费。村里人都说:“三先(生)是文曲星下凡,就是命不好。”
我那时还小,只知道三爷每次见了我,都会摸摸我的头说:“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 没想到多年后,这句话成了我求学路上的动力。
童 趣
七八岁的时候,我开始帮家里干活。夏天放暑假,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放猪。家里养了一头老母猪,带着十几只小猪,我每天上午下午都要跟着二爷去放猪。
放猪的地方可多了,收割后的山芋地、花生地、麦田里,总能找到些遗漏的山芋、花生和麦粒。小猪们拱着土,哼哧哼哧地找吃的,老母猪则慢悠悠地跟在后面,时不时抬头看看我,好像在说:“别走远了。”
沟坡上的青草也是猪的美食,蒲公英、灰灰菜、马齿苋…… 这些野菜我都叫得上名字,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心里门儿清。有时候猪吃得高兴,跑到别人家的地里,我就得赶紧追过去,一边喊一边用树枝赶,生怕被看青人发现罚工分。
后来家里又养了水牛,放牛就成了我的新任务。比起放猪,放牛要轻松快乐得多。我可以骑在牛背上,哼着不成调的小曲,看天上的云卷云舒,听路边的鸟叫虫鸣。水牛很温顺,慢慢悠悠地走着,我晃着腿,感觉自己像个大将军。
有时候牛吃草,我就和小伙伴们在草地上打滚、摔跤,或者比赛爬树。累了就躺在树荫下,看牛尾巴甩来甩去赶苍蝇,闻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心里说不出的惬意。
除了放猪放牛,我还放过鸭子。一百多只鸭子,白花花一片,跟在我身后,“嘎嘎” 地叫着,穿梭在稻田和沟渠之间。鸭子很淘气,总爱乱跑,我得时刻盯着,用长竹竿把它们赶在一起。有时候鸭子下蛋,我捡起来揣在怀里,热乎乎的,跑回家交给母亲,能得到一句夸奖。
割猪菜是每天必做的活。我和小二兔、小翠华是固定搭档。小二兔整天光着屁股,挺着个大肚子,像个小弥勒佛。小翠华是个文静的女孩,总是安安静静地割菜,不多说话。
我们三个每人挎着一个篮子,比赛谁割得快、割得多。割满篮子后,就玩个小游戏:把镰刀抛向天空,落地时如果刀刃朝上,就能赢一把猪菜;刀刃朝下,就输一把。每天输赢不多,但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笑声在田埂上回荡。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苦,但快乐来得很简单。一根麦秸秆能吹出调子,一块泥巴能捏出各种造型,几个石子能玩半天。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玩具,但大自然给了我们最丰富的礼物。
春天,我们到田埂上挖荠菜,回家让母亲做成荠菜团子,那是难得的美味。夏天,在树荫下捉知了,用面筋粘蜻蜓。秋天,跟着大人去地里拾稻穗,偶尔能找到几穗饱满的,偷偷剥去皮塞进嘴里嚼,清香在舌尖散开。冬天,就在雪地里滚雪球,堆雪人,冻得小手通红也不回家。
有一次,我们在三虫家墙外看到一棵大枣树,树上结满了半红的枣子,看得我们直流口水。但枣树在院子里,我们不敢进去,就在墙外打转。小卫军眼珠一转,想出个办法:用芦柴梢子圈成三角形的扣子,站在墙外,把扣子套在枣树枝上,用力一拉,枣子就掉了下来。我们一边捡枣子,一边往嘴里塞,甜丝丝的汁水在嘴里蔓延。小二兔吃得太急,枣核卡在喉咙里,吓得我们赶紧拍他的背,好不容易才咳出来。虽然有点惊险,但那天的枣子,是我吃过最甜的。